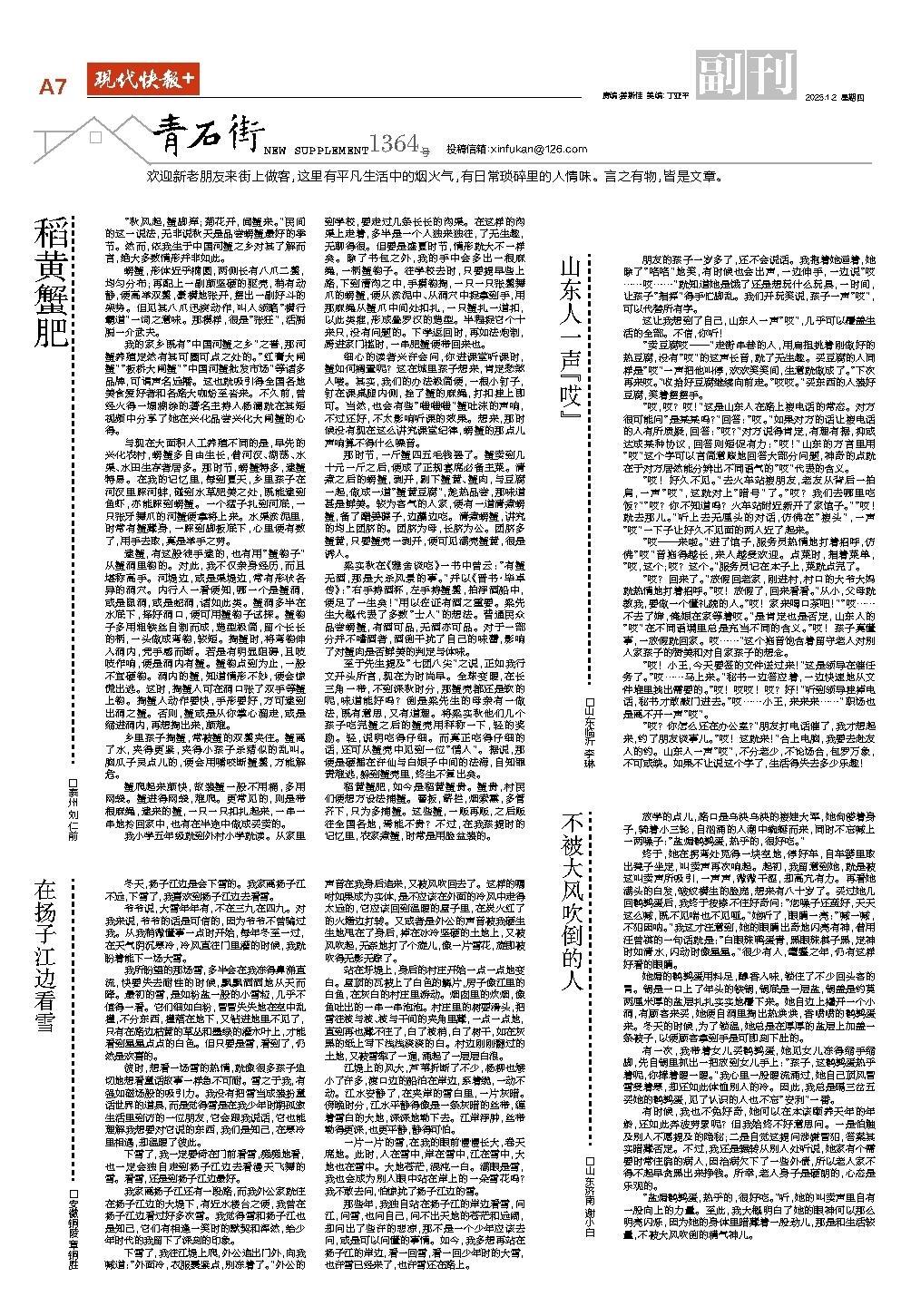□泰州 刘仁前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民间的这一说法,无非说秋天是品尝螃蟹最好的季节。然而,依我生于中国河蟹之乡对其了解而言,绝大多数情形并非如此。
螃蟹,形体近乎椭圆,两侧长有八爪二螯,均匀分布;再配上一副颇坚硬的躯壳,稍有动静,便高举双螯,豪横地张开,摆出一副好斗的架势。但见其八爪迅疾动作,叫人领略“横行霸道”一词之意味。那模样,很是“张狂”,活脱脱一介武夫。
我的家乡既有“中国河蟹之乡”之誉,那河蟹养殖定然有其可圈可点之处的。“红膏大闸蟹”“板桥大闸蟹”“中国河蟹批发市场”等诸多品牌,可谓声名远播。这也就吸引得全国各地美食爱好者和各路大咖纷至沓来。不久前,曾经火得一塌糊涂的著名主持人杨澜就在其短视频中分享了她在兴化品尝兴化大闸蟹的心得。
与现在大面积人工养殖不同的是,早先的兴化农村,螃蟹多自由生长,借河汊、湖荡、水渠、水田生存者居多。那时节,螃蟹特多,逮蟹特易。在我的记忆里,每到夏天,乡里孩子在河汊里踩河蚌,碰到水草肥美之处,既能逮到鱼虾,亦能踩到螃蟹。一个猛子扎到河底,一只张牙舞爪的河蟹便拿将上来。水渠淤泥里,时常有蟹藏身,一踩到脚板底下,心里便有数了,用手去取,真是举手之劳。
逮蟹,有这般徒手逮的,也有用“蟹钩子”从蟹洞里钩的。对此,我不仅亲身经历,而且堪称高手。河堤边,或是渠堤边,常有形状各异的洞穴。内行人一看便知,哪一个是蟹洞,或是鼠洞,或是蛇洞,诸如此类。蟹洞多半在水底下,择好洞口,便可用蟹钩子试探。蟹钩子多用粗铁丝自制而成,造型极简,留个长长的柄,一头做成弯钩,较短。掏蟹时,将弯钩伸入洞内,凭手感而断。若是有明显阻碍,且吱吱作响,便是洞内有蟹。蟹钩点到为止,一般不宜硬钩。洞内的蟹,知道情形不妙,便会惊慌出逃。这时,掏蟹人可在洞口张了双手等蟹上钩。掏蟹人动作要快,手形要好,方可逮到出洞之蟹。否则,蟹或是从你掌心溜走,或是缩进洞内,再想掏出来,颇难。
乡里孩子掏蟹,常被蟹的双螯夹住。蟹离了水,夹得更紧,夹得小孩子杀猪似的乱叫。脑瓜子灵点儿的,便会用嘴咬断蟹螯,方能解危。
蟹爬起来颇快,故装蟹一般不用桶,多用网袋。蟹进得网袋,难爬。更常见的,则是带根麻绳,逮来的蟹,一只一只扣扎起来,一串一串地拎回家中,也有在半途中做成买卖的。
我小学五年级就到外村小学就读。从家里到学校,要走过几条长长的沟渠。在这样的沟渠上走着,多半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了无生趣,无聊得很。但要是盛夏时节,情形就大不一样矣。除了书包之外,我的手中会多出一根麻绳,一柄蟹钩子。往学校去时,只要提早些上路,下到漕沟之中,手摸钩掏,一只一只张螯舞爪的螃蟹,便从淤泥中、从洞穴中捉拿到手,用那麻绳从蟹爪中间处扣扎,一只蟹扎一道扣,以此类推,形成叠罗汉的造型。半程捉它个十来只,没有问题的。下学返回时,再如法炮制,跨进家门槛时,一串肥蟹便带回来也。
细心的读者兴许会问,你进课堂听课时,蟹如何搁置呢?这在城里孩子想来,肯定愁煞人喽。其实,我们的办法极简便,一根小钉子,钉在课桌腿内侧,拴了蟹的麻绳,打扣挂上即可。当然,也会有些“嗤嗤嗤”蟹吐沫的声响,不过还好,不太影响听课的效果。想来,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讲究课堂纪律,螃蟹的那点儿声响算不得什么噪音。
那时节,一斤蟹四五毛钱罢了。蟹卖到几十元一斤之后,便成了正规宴席必备主菜。清煮之后的螃蟹,剥开,剔下蟹黄、蟹肉,与豆腐一起,做成一道“蟹黄豆腐”,趁热品尝,那味道甚是鲜美。较为客气的人家,便有一道清煮螃蟹,备了醋姜碟子,边蘸边吃。清煮螃蟹,讲究的均上团脐的。团脐为母,长脐为公。团脐多蟹黄,只要蟹壳一剥开,便可见满壳蟹黄,很是诱人。
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一书中曾云:“有蟹无酒,那是大杀风景的事。”并以《晋书·毕卓传》:“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用以佐证有酒之重要。梁先生大概代表了多数“士人”的想法。普通民众品尝螃蟹,有酒可品,无酒亦可品。对于一部分并不嗜酒者,酒倒干扰了自己的味蕾,影响了对蟹肉是否鲜美的判定与体味。
至于先生提及“七团八尖”之说,正如我行文开头所言,现在为时尚早。全球变暖,在长三角一带,不到深秋时分,那蟹壳都还是软的呢,味道能好吗?倒是梁先生的母亲有一做法,既有意思,又有道理。将梁实秋他们几个孩子吃完蟹之后的蟹壳用秤称一下,轻的奖励。轻,说明吃得仔细。而真正吃得仔细的话,还可从蟹壳中见到一位“僧人”。据说,那便是硬插在许仙与白娘子中间的法海,自知罪责难逃,躲到蟹壳里,终生不复出矣。
稻黄蟹肥,如今是稻黄蟹贵。蟹贵,村民们便想方设法捕蟹。罾扳,簖拦,烟索熏,多管齐下,只为多捕蟹。这些蟹,一贩再贩,之后贩往全国各地,焉能不贵?不过,在我孩提时的记忆里,农家煮蟹,时常是用脸盆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