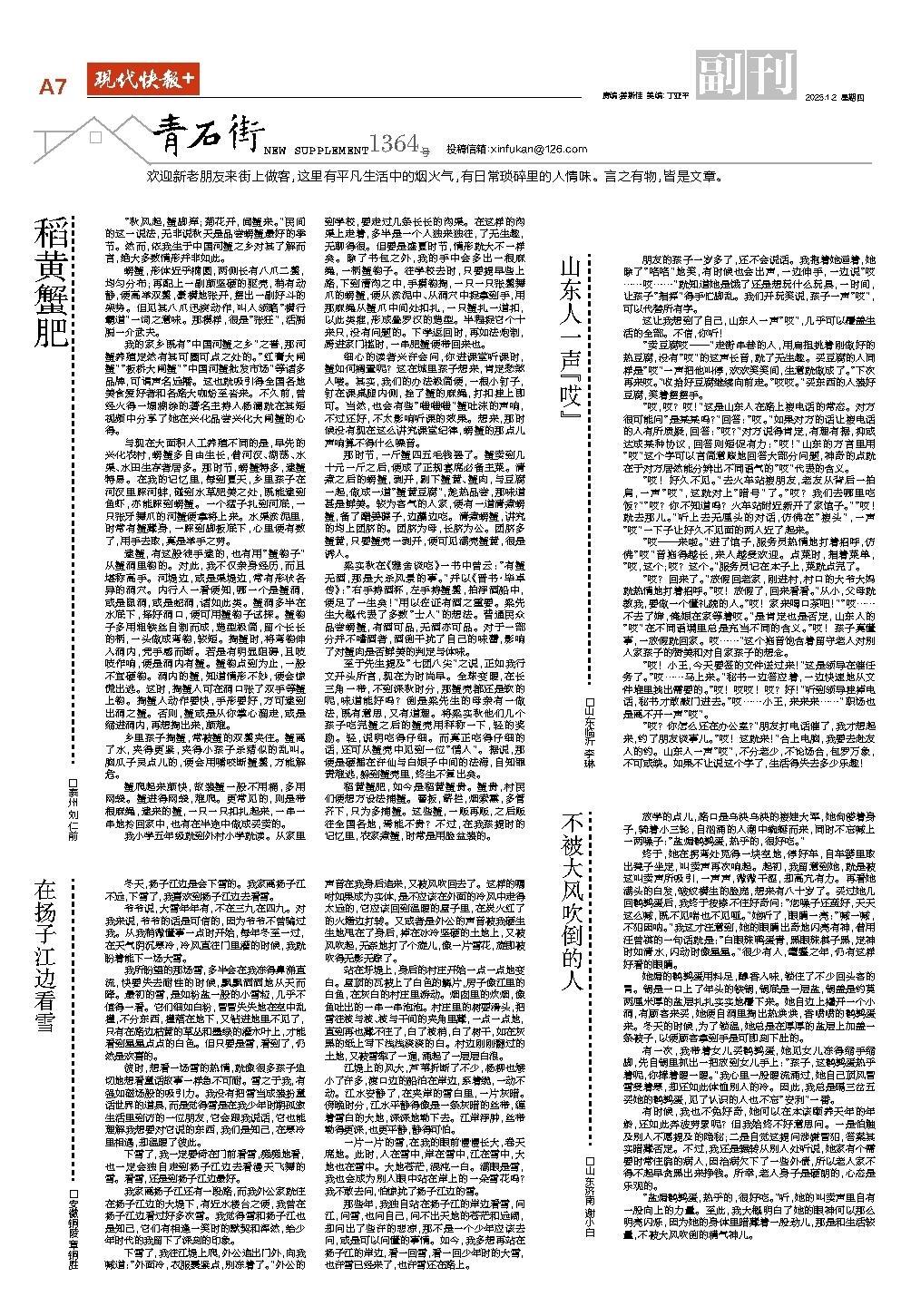□安徽铜陵 章铜胜
冬天,扬子江边是会下雪的。我家离扬子江不远,下雪了,我喜欢到扬子江边去看雪。
爷爷说,大雪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对我来说,爷爷的话是可信的,因为爷爷不曾骗过我。从我稍微懂事一点时开始,每年冬至一过,在天气阴沉寒冷,冷风直往门里灌的时候,我就盼着能下一场大雪。
我所盼望的那场雪,多半会在我冻得鼻涕直流,快要失去耐性的时候,飘飘洒洒地从天而降。最初的雪,是如粉盐一般的小雪粒,几乎不值得一看。它们细如白粉,冒冒失失地在空中乱撞,不分东西,撞落在地下,又钻进地里不见了,只有在路边枯黄的草丛和墨绿的灌木叶上,才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白色。但只要是雪,看到了,仍然是欢喜的。
彼时,想看一场雪的热情,就像很多孩子迫切地想看童话故事一样急不可耐。雪之于我,有强如磁场般的吸引力。我没有把雪当成装扮童话世界的道具,而是觉得雪是在我少年时期孤寂生活里到访的一位朋友,它会跟我说话,它也能理解我想要对它说的东西,我们是知己,在寒冷里相遇,却温暖了彼此。
下雪了,我一定要倚在门前看雪,痴痴地看,也一定会独自走到扬子江边去看漫天飞舞的雪。看雪,还是到扬子江边最好。
我家离扬子江还有一段路,而我外公家就住在扬子江边的大堤下,有近水楼台之便,我曾在扬子江边看过好多次雪。我觉得雪和扬子江也是知己,它们有相逢一笑时的默契和浑然,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雪了,我往江堤上爬,外公追出门外,向我喊道:“外面冷,衣服裹紧点,别冻着了。”外公的声音在我身后追来,又被风吹回去了。这样的嘱咐如果成为实体,是不应该在外面的冷风中走得太远的,它应该回到温暖的屋子里,在炭火红了的火塘边打转。又或者是外公的声音被我硬生生地甩在了身后,掉在冰冷坚硬的土地上,又被风吹起,无奈地打了个旋儿,像一片雪花,旋即被吹得无影无踪了。
站在圩堤上,身后的村庄开始一点一点地变白。屋顶的瓦披上了白色的鳞片,房子像江里的白鱼,在灰白的村庄里游动。烟囱里的炊烟,像鱼吐出的一串一串泡泡。村庄里的树耍滑头,把雪往枝与枝、枝与干间的夹角里藏,一点一点地,直到再也藏不住了,白了枝梢,白了树干,如在灰黑的纸上写下浅浅淡淡的白。村边刚刚翻过的土地,又被雪犁了一遍,涌起了一层层白浪。
江堤上的风大,芦苇折断了不少,杨柳也矮小了许多,渡口边的船泊在岸边,系着缆,一动不动。江水安静了,在夹岸的雪白里,一片灰暗。傍晚时分,江水平静得像是一条灰暗的丝带,缠着雪白的大地,深深地勒下去。江岸浮肿,丝带勒得更深,也更平静,静得可怕。
一片一片的雪,在我的眼前慢慢长大,卷天席地。此时,人在雪中,岸在雪中,江在雪中,大地也在雪中。大地苍茫,混沌一白。满眼是雪,我也会成为别人眼中站在岸上的一朵雪花吗?我不敢去问,怕惊扰了扬子江边的雪。
那些年,我独自站在扬子江的岸边看雪,问江,问雪,也问自己,问不出天地的苍茫和远阔,却问出了些许的悲凉,那不是一个少年应该去问,或是可以问懂的事情。如今,我多想再站在扬子江的岸边,看一回雪,看一回少年时的大雪,也许雪已经来了,也许雪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