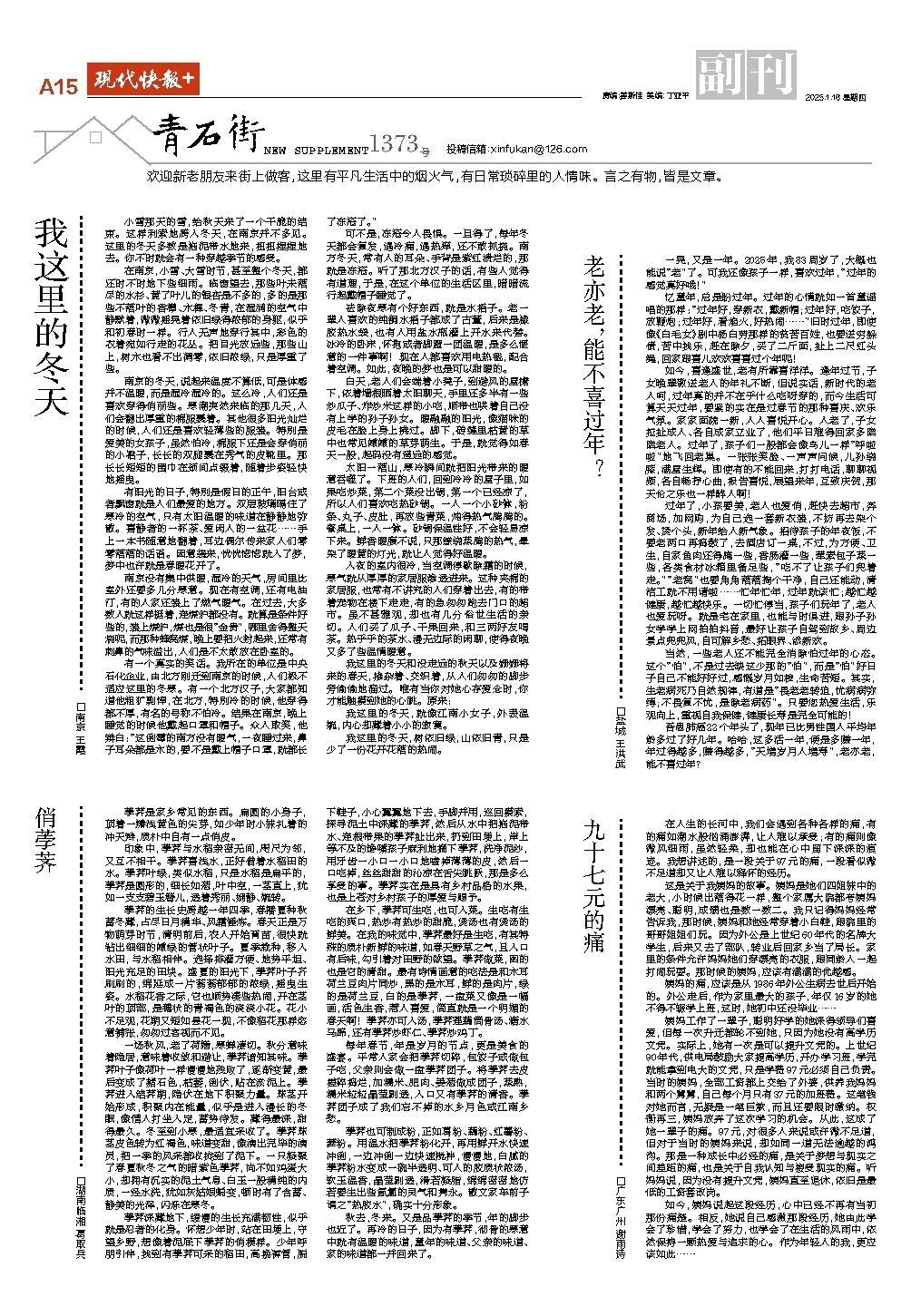□南京 王霞
小雪那天的雪,给秋天来了一个干脆的结束。这样利索地跨入冬天,在南京并不多见。这里的冬天多数是拖泥带水地来,扭扭捏捏地去。你不时就会有一种穿越季节的感受。
在南京,小雪、大雪时节,甚至整个冬天,都还时不时地下些细雨。临窗望去,那些叶未落尽的水杉、黄了叶儿的银杏是不多的,多的是那些不落叶的香樟、木樨、冬青,在湿润的空气中静默着,微微摇晃着依旧绿得浓郁的身躯,似乎和初春时一样。行人无声地穿行其中,彩色的衣着宛如行走的花丛。把目光放远些,那些山上,树木也看不出凋零,依旧浓绿,只是厚重了些。
南京的冬天,说起来温度不算低,可是体感并不温暖,而是湿冷湿冷的。这么冷,人们还是喜欢穿得俏丽些。寒潮突然来临的那几天,人们会翻出厚重的棉服裹着。其他很多阳光灿烂的时候,人们还是喜欢轻薄些的服装。特别是爱美的女孩子,虽然怕冷,棉服下还是会穿俏丽的小裙子,长长的双腿裹在秀气的皮靴里。那长长短短的围巾在颈间点缀着,随着步姿轻快地摇曳。
有阳光的日子,特别是假日的正午,阳台或者飘窗就是人们最爱的地方。双层玻璃隔住了寒冷的空气,只有太阳温暖的味道在静静地弥散。喜静者的一杯茶、爱闲人的一盆花……手上一本书随意地翻着,耳边偶尔传来家人们零零落落的话语。困意袭来,恍恍惚惚就入了梦,梦中也许就是春暖花开了。
南京没有集中供暖,湿冷的天气,房间里比室外还要多几分寒意。现在有空调,还有电油汀,有的人家还装上了燃气暖气。在过去,大多数人就这样挺着,连煤炉都没有。就算是条件好些的,装上煤炉,煤也是很“金贵”,哪里舍得整天烧呢,而那种蜂窝煤,晚上要把火封起来,还常有刺鼻的气味溢出,人们是不太敢放在卧室的。
有一个真实的笑话。我所在的单位是中央石化企业,由北方刚迁到南京的时候,人们极不适应这里的冬寒。有一个北方汉子,大家都知道他粗犷剽悍,在北方,特别冷的时候,他穿得都不厚,有名的号称不怕冷。结果在南京,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戴起口罩和帽子。众人取笑,他辩白:“这倒霉的南方没有暖气,一夜睡过来,鼻子耳朵都是木的,要不是戴上帽子口罩,就都长了冻疮了。”
可不是,冻疮令人畏惧。一旦得了,每年冬天都会复发,遇冷痛,遇热痒,还不敢抓挠。南方冬天,常有人的耳朵、手背是紫红溃烂的,那就是冻疮。听了那北方汉子的话,有些人觉得有道理,于是,在这个单位的生活区里,暗暗流行起戴帽子睡觉了。
祛除夜寒有个好东西,就是水捂子。老一辈人喜欢的纯铜水捂子都成了古董,后来是橡胶热水袋,也有人用盐水瓶灌上开水来代替。冰冷的卧床,怀抱或者脚蹬一团温暖,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啊!现在人都喜欢用电热毯,配合着空调。如此,夜晚的梦也是可以甜暖的。
白天,老人们会端着小凳子,到避风的屋檐下,依着墙根晒着太阳聊天,手里还多半有一些炒瓜子、炸炒米这样的小吃,顺带也哄着自己没有上学的孙子孙女。暖融融的阳光,像猫咪的皮毛在脸上身上拂过。脚下,砖缝里枯黄的草中也常见嫩嫩的草芽萌生。于是,就觉得如春天一般,起码没有遥远的感觉。
太阳一落山,寒冷瞬间就把阳光带来的暖意吞噬了。下班的人们,回到冷冷的屋子里,如果吃炒菜,第二个菜没出锅,第一个已经凉了,所以人们喜欢吃热砂锅。一人一个小砂钵,粉条、丸子、皮肚,再放些青菜,炖得热气腾腾的。餐桌上,一人一钵。砂锅保温性好,不会轻易凉下来。鲜香暖腹不说,只那缭绕蒸腾的热气,晕染了暖黄的灯光,就让人觉得好温暖。
入夜的室内很冷,当空调停歇除霜的时候,寒气就从厚厚的家居服渗透进来。这种夹棉的家居服,也常有不讲究的人们穿着出去,有的带着宠物在楼下走走,有的急匆匆跑去门口的超市。虽不甚雅观,却也有几分俗世生活的亲切。人们买了瓜子、干果回来,和三两好友喝茶。热乎乎的茶水、漫无边际的闲聊,使得夜晚又多了些温情暖意。
我这里的冬天和没走远的秋天以及姗姗将来的春天,掺杂着、交织着,从人们匆匆的脚步旁偷偷地溜过。唯有当你对她心存爱念时,你才能触摸到她的心跳。原来:
我这里的冬天,就像江南小女子,外表温婉,内心却藏着小小的寂寞。
我这里的冬天,树依旧绿,山依旧青,只是少了一份花开花落的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