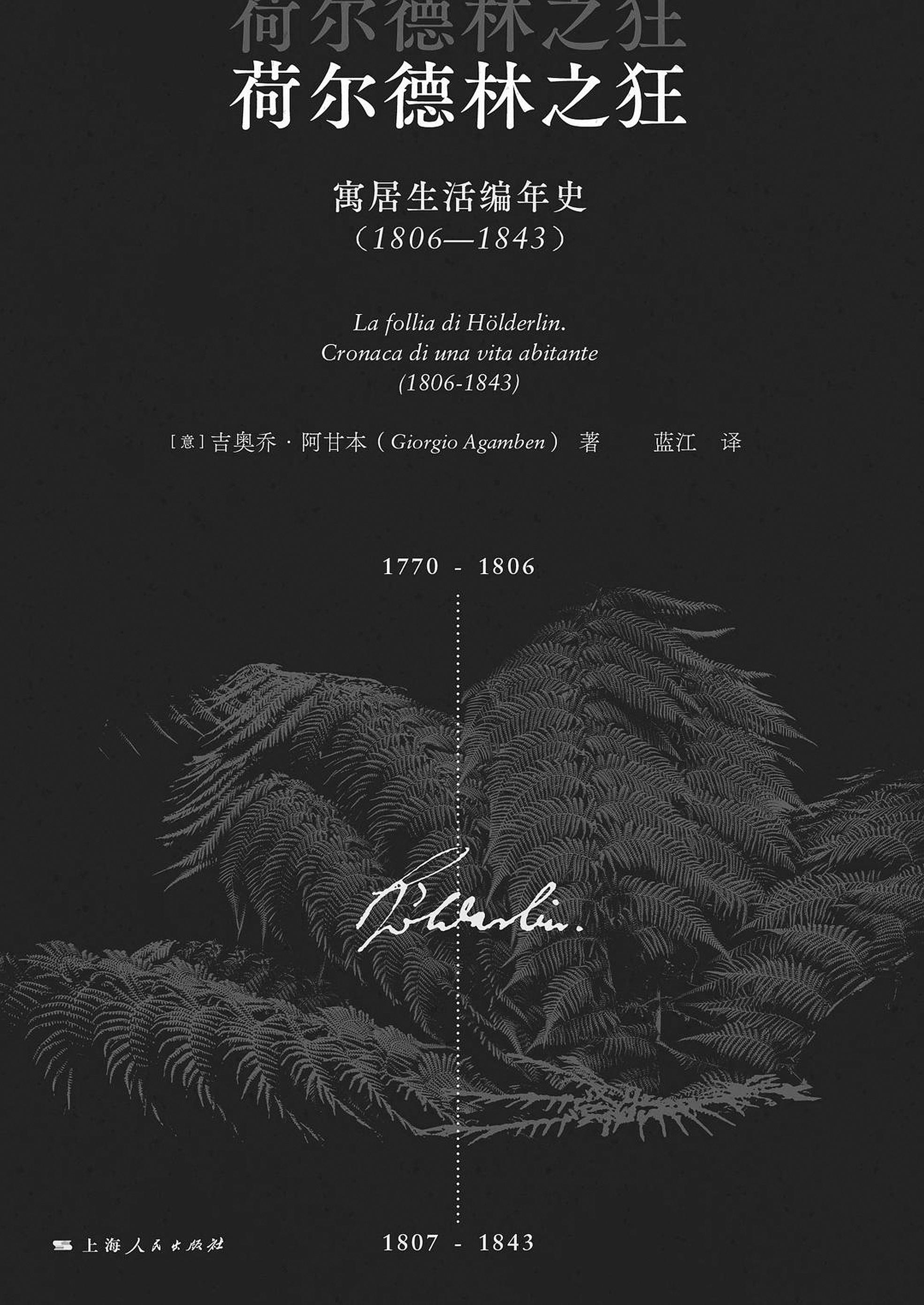□李北园
“人,诗意地栖居。”这句话在中国广为人知,因其高度吻合中国文化中的诗性传统,常被误认为是国产俗语。又因它最早是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著作被转译到中国,版权又常被归入海德格尔(1889—1976)名下。实际上,“人,诗意地栖居。”源于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的诗学思想。
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的“相遇”或者“重逢”,是在他离开弗莱堡大学之后。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曾执掌纳粹治下的弗莱堡大学,以纳粹官员的身份担任校长,虽然时长仅一年,但这成为他终生无法抹去的黑历史。在执掌弗莱堡之前,海德格尔注重对“此在在世”的生存状态的分析,以“此在”为基础对“存在”进行了本体论的解释。辞职之后,他开始注重于对存在本身性质的解释,直接面对存在的真理,对存在的意义进行追问,在哲学研究中开始引入诗歌和艺术。
1935年11月13日,海德格尔在弗莱堡艺术科学协会作题为《艺术作品的本源》的演讲。1936年4月2日,在罗马作题为《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的演讲,第一次以荷尔德林为背景。此后直到去世,荷尔德林都是海德格尔用来阐释自己哲学思想的重要入口。著名的《……人,诗意地栖居……》一文,便是海德格尔1951年10月6日在比勒欧作的荷尔德林诗歌主题演讲讲稿。在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在柔媚的湛蓝中》的诗句,从诗意与栖居的关系入手,来探讨人之生存。当人本真地作诗的时候,诗意便发生了,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来度量自身。这种度量一旦发生,人就能根据诗意之本质来作诗。而这种诗意一旦发生,人就能诗性地栖居在大地上。那样的情景,海德格尔则引用荷尔德林的诗作《风景》来描绘:
“当一个人的居住生活走向远方,
远处,葡萄园的季节熠熠生辉,
夏日空旷的田野也尽收眼底,
浮现了森林和它们幽暗的面容。
大自然完成了岁月的形象,
当时光飞逝,一页页翻过时,大自然仍在徘徊,
这是纯粹的完美,是上天的光辉,
人也是如此,就像树冠上盛开的花朵。”
荷尔德林是德国古典浪漫派诗人,诗人中年时因情场失意身心交瘁,产生精神分裂,但他的诗歌创作并未就此停止。他的作品书写优美的自然景色,同时又注重主观感情的抒发,流露出忧郁、孤独的气质。遗憾的是,诗人在他生前以及19世纪未被重视,到20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海德格尔便是荷尔德林诗学思想的重要传播者。与海德格尔有师生之谊的意大利哲学家、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则关注荷尔德林失去理智的后半生,以“狂”为切入点,进行“居住”与“自我”的哲学探讨。
在阿甘本撰著的《荷尔德林之狂:寓居生活编年史(1806—1843)》中,荷尔德林的一生被整齐地分为两部分:从1770年到1806年的前36年,以及从1807年到1843年的后36年。诗人的前半生在相对广阔的世界里四处游荡,但在后半生,他却完全与世隔绝,寄居在木匠恩斯特·齐默尔的家里。写作、沉思与接待访客,成为荷尔德林幽居期间的日常,而从访客们的描述之中,人们得以了解这位伟大诗人后半生的状况。虽然访客们坚持要详细描述一系列或多或少无关紧要的事件和习惯,但荷尔德林坚持认为自己身上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这里啥事都没有发生!”访客们留下来的记录,也成为阿甘本撰著《荷尔德林之狂》的重要资料来源。
阿甘本采用编年史的形式来展示荷尔德林后半生的生活,他交代自己的用心:“我选择将荷尔德林疯狂岁月的编年史与同时期欧洲历史的编年史并列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编年史是否比历史更真实,以及真实到什么程度,读者可以自行决定。无论如何,编年史的真实性最终将取决于它与历史上的编年史之间的张力,这让我们永远无法对编年史进行归档。”
作为荷尔德林寓居生活编年史参照系的“欧洲历史的编年史”,在阿甘本看来,是有着严重缺憾的,因为在那个体系里,伟大的荷尔德林被排除在外,“至少在1826年路德维希·乌兰特和古斯塔夫·施瓦布编辑的诗集出版之前是如此”。乌兰特和施瓦布都是德国诗人,也是荷尔德林首部诗集的编辑出版者。但据说,对这两位朋友的帮助,荷尔德林并不领情,他认为自己有能力独自完成编辑出版工作。
荷尔德林的不满,也被阿甘本写进了《荷尔德林之狂》,他尽最大的可能呈现诗人后半生原生态的诗意栖居生活,让诗人自我隔绝和精神状态背后的深刻哲学意涵直接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