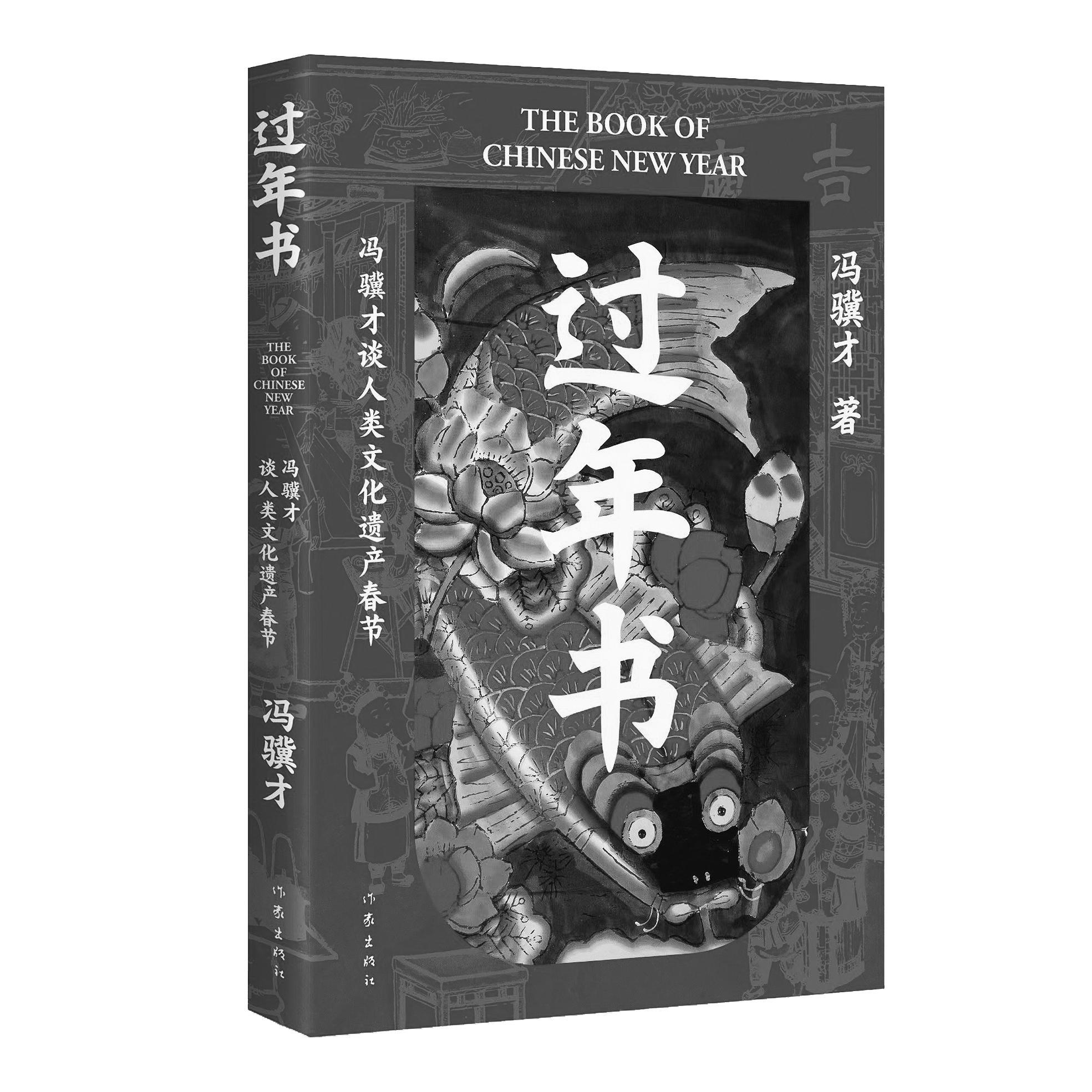儿时最快乐的日子是过年。
不同的人生境遇有不同的过年的滋味。穷苦的人在过年中自寻安慰,幸运的人过年享受幸福。然而,不管贫富,一般人儿时的年总还能无忧无虑,因为生活的愁苦都被大人藏在自己身上了。
天津这里的年是从厨房的灶龛摆上糖瓜就开始了,尽管离着大年三十还有二十多天,已经能够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很大的快乐即将开始。虽然大人在给灶王摆供时特意留给了我两个小糖瓜,我还是更喜欢趁大人们不注意时,从灶王爷身前的碟子里偷一个糖瓜,尝一尝“偷吃禁果”的快乐。偷吃禁果是一种人性。
接下来,便是好戏一样样开始。
大人们用被单和旧报纸蒙盖屋中所有的家具,用头巾或一块布蒙住自己的脑袋,将鸡毛掸子或扫帚绑在竹竿前端,在屋顶上划来划去,清除边边角角的蜘蛛网和灰尘;跟着把所有窗子都擦得几乎看不见玻璃,好像伸手就能摸到窗外的景物。身居租界地的五大道的住户大多是四处迁来的移民,各地的风俗不同,有的地方不贴门神,吊钱只是天津本地盛行的年俗,所以五大道人家很少用门神吊钱。然而,家家户户的屋内却都贴上花花绿绿的年画。我小时候家里已经不贴杨柳青木版印制的年画了,都贴石印或胶印的年画。新式年画颜色更多,形象更立体;我最喜欢三国故事的年画,比如《三英战吕布》《草船借箭》《辕门射戟》等等。这喜好肯定与姥姥紧密相关。
最叫我兴奋的烟花爆竹,也是每个男孩子的最爱。由于鞭炮只能过年时放,一年只这几天,便爱之尤切。逢到年根,家里就从老城娘娘宫前的鞭炮市用三轮车拉来满满一车花炮,搬进一楼那间小小的茶室里,叫我的心儿激动得怦怦跳。在各种诱人的鞭炮和烟花中,最刺激人的是三种:一种是“足数万头”的钢鞭,长长的一包立在那儿,快和我一样高,响起来必须捂耳朵;还有一种名叫“八仙过海”的烟花盒子,只要点起来,各种烟花一连十多分钟;一会儿窜花,一会儿打灯,一会儿喷火,花样翻新,连绵不绝,叫人不肯眨眼;再一种是大金人,黄泥做的老寿星,很重很重,外边刷一道金,里边装满火药,头顶是药捻子,点着后,从老寿星光溜溜的头顶向上“呲花”,愈呲愈高,最高可以呲过楼顶,要上天了!
每到过年,娘娘宫有一条街是“鞭炮市”,红红的摆满烟花爆竹,像站满大兵,现在居然搬到我家里来!然而,大人们却把这小茶室的门锁得严严;我认为是防我,其实是不准任何人进去。那时男人们大多吸烟,怕把火带进去。
这些花炮是在大年三十夜里放的。但每年大人都会给我一些特别的恩惠,几挂小鞭,黄烟带炮、地老鼠、呲花之类,允许我在院里放一放。我太淘皮,总要想些“坏点子”,弄出一些恶作剧,比如把点着的几头鞭扔到鸡窝里,或者拴在猫尾巴上,有一年就把家中的老虎猫吓跑了再也没回来。长大后,我一直为我儿时有过虐猫的劣迹感到耻辱。
对于孩子们,过年还有一件平时连想也不敢想的美事,就是无论怎么喊怎么叫怎么闹,大人也不管。不会训斥你,更不会打你。过年是神仙当家的特殊的日子,连父亲平日的一脸正经也给夺走了。过年只准笑、不准哭,不能吓唬孩子,更不能打孩子,所以这几天可以放开手脚地胡闹。我的奶妈对我说:“你要闹过头了,小心过了年跟你算总账!”果然,一年的初二,我在客厅耍一把木头做的“青龙偃月刀”,耍过了劲儿,啪地把一个贵重的百蝶瓶打碎。父亲脸色都青了,但他居然忍下来没说我一句。可等过了年,赶到我淘皮惹祸的当口,把我狠打一顿,我感到了有几下是与百蝶瓶有关。
过年虽然放纵孩子开心,大人们对自己却管得很严。无论谁都不准耷拉脸蛋子,人人满脸堆笑,嘴上总挂着各种吉祥话,碰到与丧气的字同音的话必须绕开说;白颜色的东西不能放在表面,窗户上只能贴红窗花;不能扫地;尤其三十晚上,所有屋里的灯全要开着,一直开到初一天亮。有时忘了关,初一白天还亮着。
年夜饭必定要最丰盛,餐桌上一定要摆上宁波老家传统的“冯家鸭”,还有年糕汤、雪菜黄鱼、苔条花生,但都没让我流下口水,整整一天我都焦急地等着饭后那场爆竹烟花的“盛宴”。可是放花炮要等到子午交时,从下午到午夜是我一年中感觉最慢的时间,一次我悄悄去拨快壁炉上座钟的表针。大人们笑道:拨到十二点也没用,太阳还在天上呢!
燃放花炮是天津本地最疯狂的一项年俗。天津这里是码头,码头上争强好胜,无论人和事都是硬碰硬,天津人放炮要相互比拼,看谁放的炮大,谁放得多,谁放得胆大。这一较劲,鞭炮就疯了。五大道上的人家虽然是外地移民,但非官即商,官商都讲究排场,闹得愈大愈牛,而且官商都有钱,这一来五大道的花炮放得反而比老城那边还凶。
临近午夜时,随着外边的鞭炮声愈来愈响,大人们开始把花炮从茶室搬到后院,那场面有点像大战将临。我兴奋地跟着那些搬运花炮的大人从楼里跑进跑出,完全不管外边寒风刺骨。急得我的奶妈使劲把我往屋里拽,等到把长长的鞭炮在竹竿上拴牢,烟火盒子和大金人都搬上墙头,我和全家都趴在餐厅和客厅的窗台上,关了屋里的灯,一片比梦还灿烂的烟花世界呈现在眼前。我和姐姐妹妹们所有欢叫和惊叫都淹没在震耳欲聋的鞭炮的炸裂声中了。我现在还记得一家人被闪动的火光照亮的每一张带表情的脸。母亲似乎更关心我们脸上的表情。更叫我激动的是,我家的鞭炮声已经淹没在整个城市鞭炮惊天动地的轰响中。一个“年”的概念不知怎么深深嵌入我的心里,便是——普天同庆。我不知什么时候记住这个词儿,什么时候懂得其中的含义,反正现在明白了年的真正的理想。不能往下再说了,再说就离开童年和五大道了。
年年夜里,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入睡的。反正一定是困得不行,用火柴棍儿也支不住眼皮时,便歪在哪儿,叫奶妈把我背回屋,脱了衣服盖上被,呼呼大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一准一个红通通发亮的大苹果放在枕边。这是母亲放的。母亲年年夜里都会到我们兄弟姐妹屋里转一圈,每人枕边放一个大苹果,预示来年平平安安。
■前言后记
近年来,我特别想编一本书,即《过年书》。因为我写了太多的关于年的文字,小说散文也好,随笔杂文也好。我是从农耕时代过来的人,对年的情怀和记忆太深。年是中国生活和文化中太陈太浓太烈太醇的一缸老酒,而且没有一个中国人没尝过。
也许为此,在上世纪社会开放、生活改弦更张,加上西风东渐,固有的传统便渐渐松散,年味发生淡化,我因而忧患,生活不能不知不觉失掉了这么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失却了年的风俗,那就不仅仅是一顿年夜饭,而是几千年创造的各个地域千差万别灿烂缤纷的年文化,这里边还包裹着我们民族对团圆、慈孝、和谐、平安和幸福执着的精神追求。于是,我开始关切、思索、思辨、探究年的内涵、性质、意义、不可缺失的道理,写成文章,或向公众讲述;进而对一些重要的年俗如花会、窗花、年画等进行田野抢救;在各种与年相关的社会话题上发表意见,如春晚、春运、短信拜年、鞭炮等。我的本意是保护好和传承好传统的年文化。
另外还要做一件事,是为加强年的本身而努力。一是向国家建议除夕放假;除夕是年最重要的日子,不放假,就无法过好年;这个建议被政府采纳了。二是建议将春节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与历史经典。一旦被国际公认,列入世遗,将极大提高国人的文化自信,同时春节将成为全世界尊重与喜爱的节日。
为此,我写了许多文章、建议、提案,做了许多演讲,通过媒体表达出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与意见。近四十年来,写年、说年、谈年、论年,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于是,我很想把它们汇编一起,看看年的当代兴衰与走向,也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力。
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春节申遗成功——闯到我们的生活。多年的梦想成为现实!春节成为人类的文化瑰宝,一方面当之无愧,一方面喜出望外。
由衷地祝愿,春节在中国和世界的现代文明中散发出更璀璨的光彩。让文明更文明。
内容简介
春节申遗成功后,冯骥才第一时间编著了《过年书》。该书分为“年的感怀”“年的沉思”“年的艺术”“年的思辨”“年的话语”五个部分,收录了他有关年的《守岁》《花脸》《春节八事》等五十余篇关于春节的文章和访谈,并配以三十余张彩图,从春节回忆、春节习俗、对春节相关非遗的抢救,到对春节的思考和展望,全面阐述了春节的文化内涵,是了解春节的入门读物,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春节的绝佳读本。
作者简介
冯骥才
1942年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宁波,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冯骥才是新时期崛起的第一批作家,也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尤以“文化反思”系列小说著称,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二百余种,代表作有《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一百个人的十年》《俗世奇人》《单筒望远镜》《艺术家们》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西、阿拉伯等二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译本六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