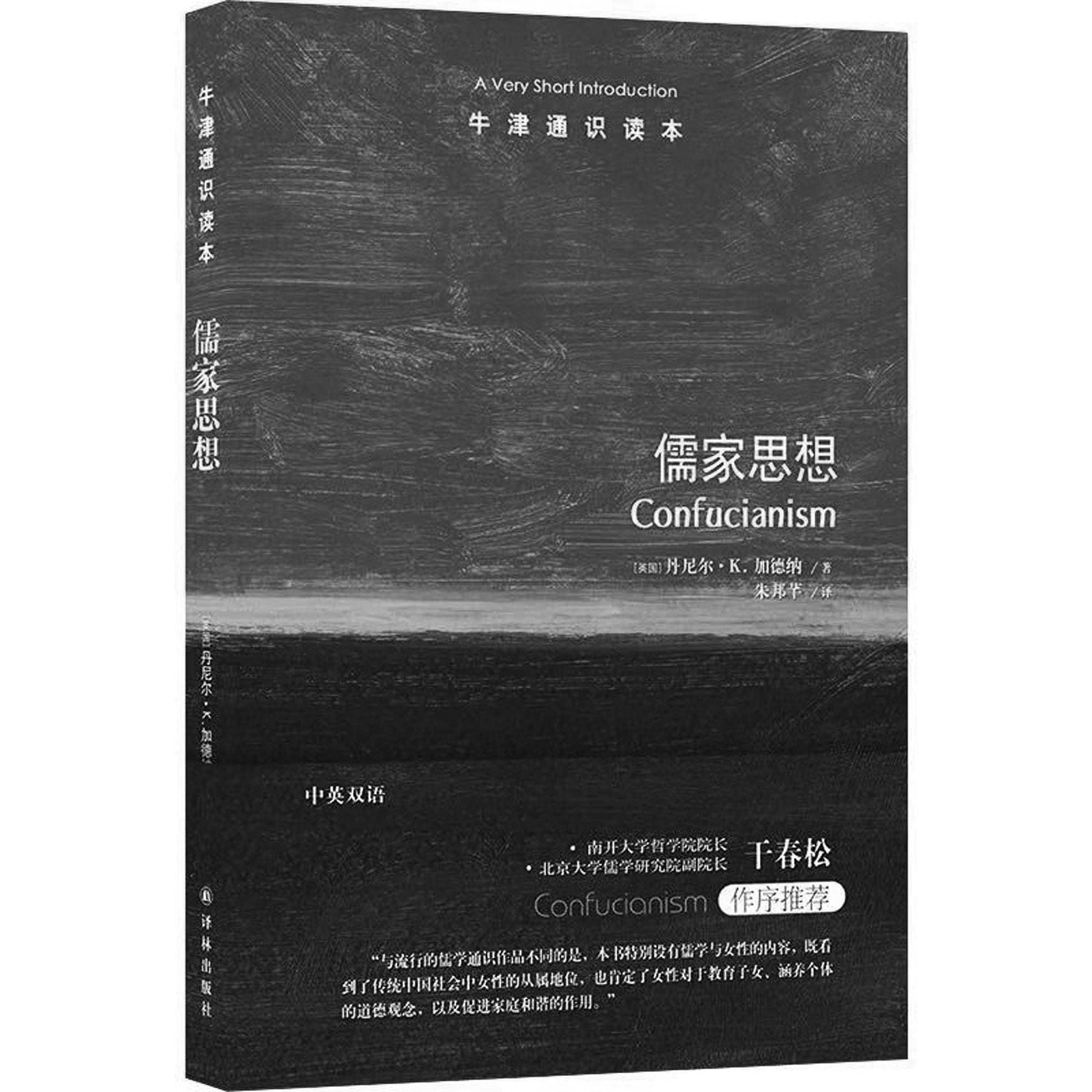《论语》并没有为道德君子提供一个简洁明晰的定义,却连篇累牍地讨论了道德君子的各种特质。最重要的是,道德君子是仁者。在儒家的理想中,仁是最高的美德,这种美德涵盖了包括诚信、正义、慈悲、礼仪、智慧,以及孝顺在内的一切。没有一种翻译能够精确描述这个词的全部意义。它被译成了五花八门的benevolence(仁爱)、humanity(仁慈)、humanness(人性),如此等等;我在本书中把它翻译成true goodness(真善),希望这种译法能够传达“仁”在孔子教诲中包罗万象、至高无上的地位。仁不是与世隔绝,与其他人断绝往来培养不出这种品质。仁只能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对待他人的方式中。正是在具体的行为中,作为美德的仁才得以实现。例如,孝子向其父鞠躬,就“施行”了他的孝心。因此,仁与礼仪密切相关,因为孔子认为,仁主要通过践礼才被赋予了有意义的表达。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发现孔子在《论语》中的大部分教导都在讨论恰当的礼仪。孔子认为,在道德上高人一筹,就是对礼仪有敏锐的认知。
虽说仁的概念在孔子的学说中至关重要,他却从未就他所谓的至德做出大致的解释或定义。这让弟子们倍感挫败,在《论语》中,他们自始至终都在用如下的问题烦扰他:“仁是什么?”“某某人是仁者吗?”“某某人的行为是仁行吗?”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似乎取决于提问之人以及所论及之人。仁可以是“爱人”(《论语 ·颜渊第十二之二二》),是“克己复礼”(《论语 ·颜渊第十二之一》),是“恭、宽、信、敏、惠”(《论语 ·阳货第十七之六》),是“有勇”(《论语 ·宪问第十四之四》),是“不忧”(《论语 ·子罕第九之二九》),或是“刚毅”(《论语 ·子路第十三之二七》)。孔子向弟子们所作的解释不过是仁的概况或部分面向。他也知道他们很沮丧,渴望他能更加开诚布公,就说道:“朋友们,我知道你们认为我有什么瞒着没教。但我对你们没什么可隐瞒的。”(《论语 ·述而第七之二三》)看来,仁似乎无法被完全表达,充分定义,它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性质。像他的追随者们一样,我们倒是可以从《论语》中梳理出对这个基本道德品质的更加深刻的理解。该文本中的一些段落尤其发人深省。子贡问:“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生去做的呢?”孔子说:“应该是恕吧:自己不乐意的,就不要强加于人。”(《论语 ·卫灵公第十五之二四》)仁就是感同身受的境界。在与他人打交道时,我们应该以自己乐于接受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为了判断他人的感受,我们需要易地而处,体会一下自己的感受。这就是孔子的同理心。将自己的这些同理感受成功地延伸至他人,使得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能够真正达到感同身受之时,就实现了仁:“我们老师的道,就是忠于自己,宽恕他人,没别的。”(《论语 ·里仁第四之十五》)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或特定场合,感同身受或许不难。孔子认为,其困难在于我们与各式各样的人交往时,整天都保持着共情的感受与做法,这些人包括关切的学生、悲伤的友人、哭闹的孩子、病弱的邻居、咄咄逼人的乞丐、心烦意乱的同事、筋疲力尽的配偶,不一而足。如果一整天可以称作挑战的话,那么整周或整月就更是难上加难。这或许解释了孔子何以拒绝称任何人为仁者,他自己也不例外(《论语 ·述而第七之三四》)。一个人共情的感受和做法消失的那一刻,他的仁也随之而去。颜回比大多数人都能保持仁,但就连他的成功也是有限的。孔子说:“颜回能做到心中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余弟子能一天做到一次,或者一个月做到一次就不错了。”(《论语 ·雍也第六之七》)如此说来,有必要认识到,仁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达成的一种内心状态;它是一种涉及身心的持续行为,需要始终保持警惕。正因为此,孔子的另一个著名的弟子曾子才会说:“读书人必须博大坚毅,因为他们重任在肩,征途漫长。将仁爱作为自己的负担,不也沉甸吗?到死方休,不也漫长吗?”(《论语 ·泰伯第八之七》)。在儒家的传统中,作为君子和仁者,需要终身的承诺,至死方休。中文“仁”字的词源本身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仁”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人”,另一部分是“二”,表明一个人只有与他人交往方可成就“仁”,即真正的善。在儒家传统中,仁并不是一种可以孤立培养并表达的品质。儒家思想中没有为“上帝的竞技者”这种闪米特传统留有立足之处,那位竞技者坐在叙利亚沙漠里40英尺高的石柱上,当着上帝的面为自己扬善除恶。在孔子看来,仁是人际关系,是只有与其他人交往才会实现的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