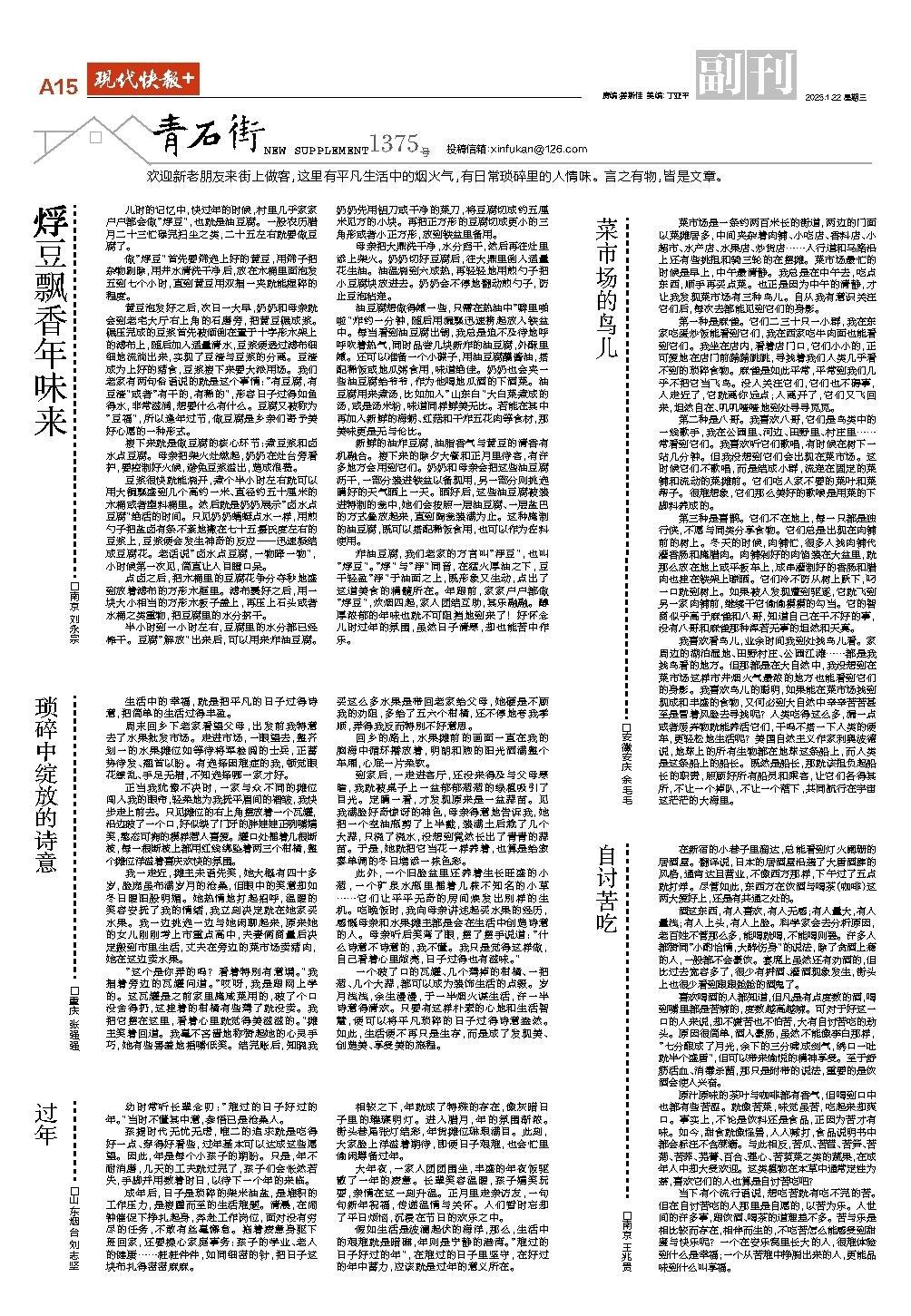□南京 刘永宗
儿时的记忆中,快过年的时候,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烰豆”,也就是油豆腐。一般农历腊月二十三忙碌完扫尘之类,二十五左右就要做豆腐了。
做“烰豆”首先要筛选上好的黄豆,用筛子把杂物剔除,用井水清洗干净后,放在木桶里面泡发五到七个小时,直到黄豆用双指一夹就能捏碎的程度。
黄豆泡发好之后,次日一大早,奶奶和母亲就会到老宅大厅右上角的石磨旁,把黄豆碾成浆。碾压完成的豆浆首先被倾倒在置于十字形木架上的滤布上,随后加入适量清水,豆浆便透过滤布细细地流淌出来,实现了豆渣与豆浆的分离。豆渣成为上好的猪食,豆浆接下来要大派用场。我们老家有两句俗语说的就是这个事情:“有豆腐,有豆渣”或者“有干的,有稀的”,形容日子过得如鱼得水,非常滋润,想要什么有什么。豆腐又被称为“豆福”,所以逢年过节,做豆腐是乡亲们寄予美好心愿的一种形式。
接下来就是做豆腐的核心环节:煮豆浆和卤水点豆腐。母亲把柴火灶燃起,奶奶在灶台旁看护,要控制好火候,避免豆浆溢出,造成浪费。
豆浆很快就能烧开,煮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用大铜瓢盛到几个高约一米、直径约五十厘米的木桶或者塑料桶里。然后就是奶奶展示“卤水点豆腐”绝活的时间。只见奶奶蜻蜓点水一样,用煎勺子把盐卤有条不紊地撒在七十五摄氏度左右的豆浆上,豆浆便会发生神奇的反应——迅速凝结成豆腐花。老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小时候第一次见,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点卤之后,把木桶里的豆腐花争分夺秒地盛到放着滤布的方形木框里。滤布裹好之后,用一块大小相当的方形木板子盖上,再压上石头或者水桶之类重物,把豆腐里的水分挤干。
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豆腐里的水分都已经榨干。豆腐“解放”出来后,可以用来炸油豆腐。奶奶先用铝刀或干净的菜刀,将豆腐切成约五厘米见方的小块。再把正方形的豆腐切成更小的三角形或者小正方形,放到铁盆里备用。
母亲把大鼎洗干净,水分舀干,然后再往灶里添上柴火。奶奶切好豆腐后,往大鼎里倒入适量花生油。油温烧到六成热,再轻轻地用煎勺子把小豆腐块放进去。奶奶会不停地翻动煎勺子,防止豆泡粘连。
油豆腐想做得嫩一些,只需在热油中“噼里啪啦”炸约一分钟,随后用漏瓢迅速捞起放入铁盆中。每当看到油豆腐出锅,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呼呼吹着热气,同时品尝几块新炸的油豆腐,外酥里嫩。还可以准备一个小碟子,用油豆腐蘸酱油,搭配稀饭或地瓜粥食用,味道绝佳。奶奶也会夹一些油豆腐给爷爷,作为他喝地瓜酒的下酒菜。油豆腐用来煮汤,比如加入“山东白”大白菜煮成的汤,或是汤米粉,味道同样鲜美无比。若能在其中再加入新鲜的海蛎、红菇和干炸五花肉等食材,那美味更是无与伦比。
新鲜的油炸豆腐,油脂香气与黄豆的清香有机融合。接下来的除夕大餐和正月里待客,有许多地方会用到它们。奶奶和母亲会把这些油豆腐沥干,一部分装进铁盆以备现用,另一部分则挑选晴好的天气晒上一天。晒好后,这些油豆腐被装进特制的瓮中,她们会按照一层油豆腐、一层盐巴的方式叠放起来,直到陶瓮装满为止。这种腌制的油豆腐,既可以搭配稀饭食用,也可以作为佐料使用。
炸油豆腐,我们老家的方言叫“浮豆”,也叫“烰豆”。“烰”与“浮”同音,在猛火厚油之下,豆干轻盈“浮”于油面之上,既形象又生动,点出了这道美食的精髓所在。年跟前,家家户户都做“烰豆”,炊烟四起,家人团结互助,其乐融融。醇厚浓郁的年味也就不可阻挡地到来了!好怀念儿时过年的氛围,虽然日子清寒,却也能苦中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