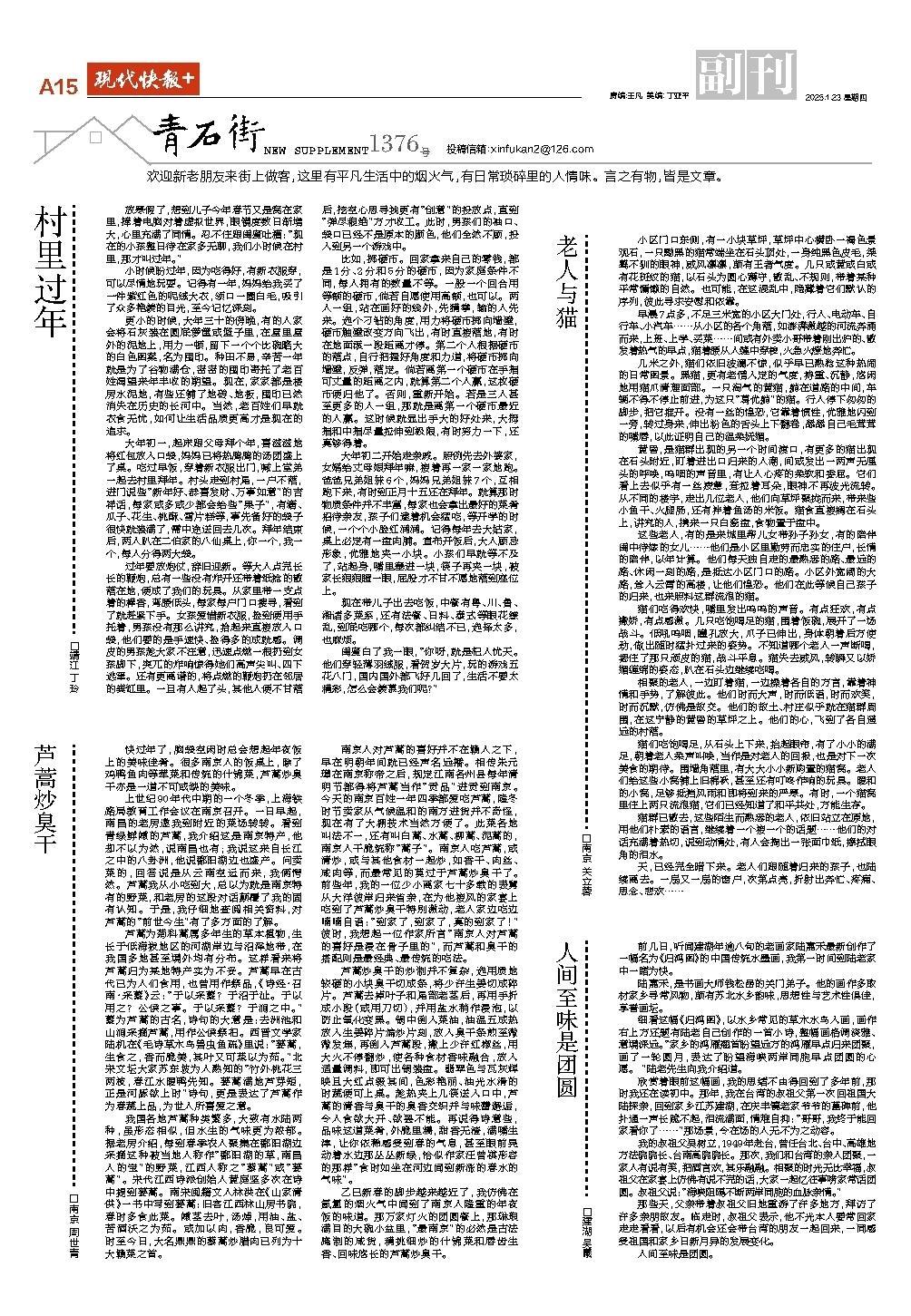□南京 周世青
快过年了,脑袋空闲时总会想起年夜饭上的美味佳肴。很多南京人的饭桌上,除了鸡鸭鱼肉等荤菜和传统的什锦菜,芦蒿炒臭干亦是一道不可或缺的美味。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季,上海铁路局教育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一日早起,南昌的老房邀我到附近的菜场转转。看到青绿鲜嫩的芦蒿,我介绍这是南京特产,他却不以为然,说南昌也有;我说这来自长江之中的八卦洲,他说鄱阳湖边也盛产。问卖菜的,回答说是从云南空运而来,我俩愕然。芦蒿我从小吃到大,总以为就是南京特有的野菜,和老房的这段对话颠覆了我的固有认知。于是,我仔细地查阅相关资料,对芦蒿的“前世今生”有了多方面的了解。
芦蒿为菊科蒿属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生长于低海拔地区的河湖岸边与沼泽地带,在我国多地甚至境外均有分布。这样看来将芦蒿归为某地特产实为不妥。芦蒿早在古代已为人们食用,也曾用作祭品,《诗经·召南·采蘩》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蘩为芦蒿的古名,诗句的大意是:去洲池和山涧采摘芦蒿,用作公侯祭祀。西晋文学家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里说:“蒌蒿,生食之,香而脆美,其叶又可蒸以为茹。”北宋文坛大家苏东坡为人熟知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诗句,更是表达了芦蒿作为春蔬上品,为世人所喜爱之意。
我国各地芦蒿种类繁多,大致有水陆两种,虽形态相似,但水生的气味更为浓郁。据老房介绍,每到春季农人聚集在鄱阳湖边采摘这种被当地人称作“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的野菜,江西人称之“藜蒿”或“蒌蒿”。宋代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多次在诗中提到蒌蒿。南宋闽籍文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一书中写到蒌蒿:旧客江西林山房书院,春时多食此菜。嫩茎去叶,汤焯,用油、盐、苦酒沃之为茹。或加以肉,香脆,良可爱。时至今日,大名鼎鼎的藜蒿炒腊肉已列为十大赣菜之首。
南京人对芦蒿的喜好并不在赣人之下,早在明朝年间就已经声名远播。相传朱元璋在南京称帝之后,规定江南各州县每年清明节都得将芦蒿当作“贡品”进贡到南京。今天的南京百姓一年四季都爱吃芦蒿,隆冬时节卖家从气候温和的南方进货并不奇怪,现在有了大棚技术当然方便了。此菜各地叫法不一,还有叫白蒿、水蒿、柳蒿、泥蒿的,南京人干脆统称“蒿子”。南京人吃芦蒿,或清炒,或与其他食材一起炒,如香干、肉丝、咸肉等,而最常见的莫过于芦蒿炒臭干了。前些年,我的一位少小离家七十多载的表舅从大洋彼岸归来省亲,在为他接风的家宴上吃到了芦蒿炒臭干特别激动,老人家边吃边喃喃自语:“到家了,到家了,真的到家了!”彼时,我想起一位作家所言“南京人对芦蒿的喜好是浸在骨子里的”,而芦蒿和臭干的搭配则是最经典、最传统的吃法。
芦蒿炒臭干的炒制并不复杂,选用质地较硬的小块臭干切成条,将少许生姜切成碎片。芦蒿去掉叶子和尾部老茎后,再用手折成小段(或用刀切),并用盐水稍作浸泡,以防止氧化变黑。锅中倒入菜油,油温五成热放入生姜碎片煸炒片刻,放入臭干条煎至微微发焦,再倒入芦蒿段,撒上少许红椒丝,用大火不停翻炒,使各种食材香味融合,放入适量调料,即可出锅装盘。翡翠色与瓦灰辉映且大红点缀其间,色彩艳丽、油光水滑的时蔬便可上桌。趁热夹上几筷送入口中,芦蒿的清香与臭干的臭香交织并与味蕾邂逅,令人食欲大开、欲罢不能。再说得诗意些,品味这道菜肴,外脆里糯,甜香无渣,满嘴生津,让你依稀感受到春的气息,甚至眼前晃动着水边那丛丛新绿,恰似作家汪曾祺形容的那样“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
乙巳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我仿佛在氤氲的烟火气中闻到了南京人隆重的年夜饭的味道。那万家灯火的团圆餐上,那琳琅满目的大碗小盆里,“最南京”的必然是古法腌制的咸货,精挑细炒的什锦菜和唇齿生香、回味悠长的芦蒿炒臭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