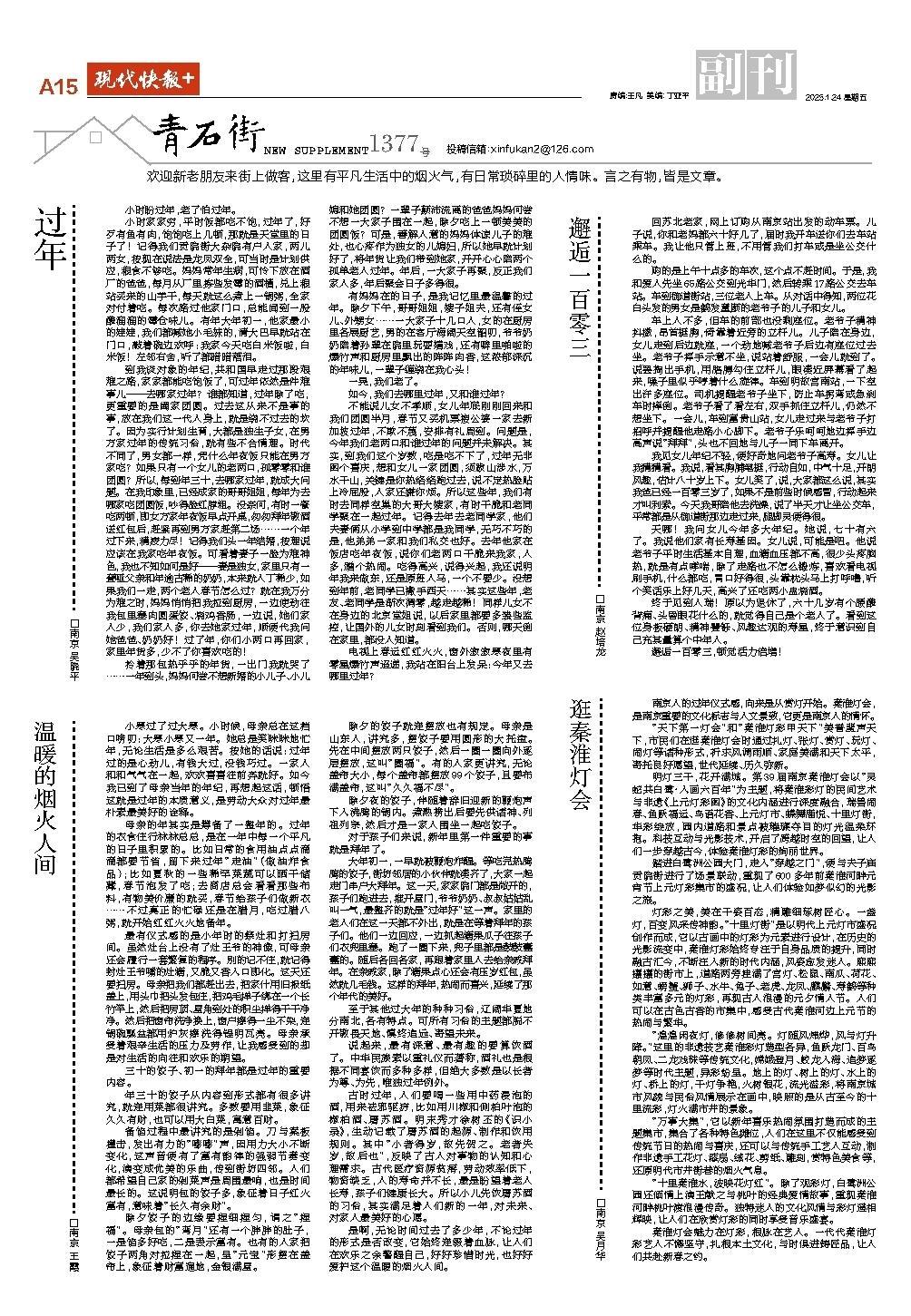□南京 吴晓平
小时盼过年,老了怕过年。
小时家家穷,平时饭都吃不饱,过年了,好歹有鱼有肉,饱饱吃上几顿,那就是天堂里的日子了!记得我们贡院街大杂院有户人家,两儿两女,按现在说法是龙凤双全,可当时是计划供应,粮食不够吃。妈妈常年生病,可怜下放在酒厂的爸爸,每月从厂里拣些发霉的酒糟,兑上粮站买来的山芋干,每天就这么煮上一锅粥,全家对付着吃。每次路过他家门口,总能闻到一股酸溜溜的霉仓味儿。有年大年初一,他家最小的娃娃,我们都喊她小毛妹的,清大巴早就站在门口,敲着碗边欢呼:我家今天吃白米饭啦,白米饭!左邻右舍,听了都暗暗落泪。
到我谈对象的年纪,共和国早走过那段艰难之路,家家都能吃饱饭了,可过年依然是件难事儿——去哪家过年?谁都知道,过年除了吃,更重要的是阖家团圆。过去这从来不是事的事,放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就是绕不过去的坎了。因为实行计划生育,大都是独生子女,在男方家过年的传统习俗,就有些不合情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凭什么年夜饭只能在男方家吃?如果只有一个女儿的老两口,孤零零和谁团圆?所以,每到年三十,去哪家过年,就成大问题。在我印象里,已经成家的哥哥姐姐,每年为去哪家吃团圆饭,吵得脸红脖粗。没奈何,有时一餐吃两顿,即女方家年夜饭早点开桌,匆匆拜年敬酒送红包后,赶紧再到男方家赶第二场……一个年过下来,精疲力尽!记得我们头一年结婚,按理说应该在我家吃年夜饭。可看着妻子一脸为难神色,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妻是独女,家里只有一聋哑父亲和年逾古稀的奶奶,本来就人丁稀少,如果我们一走,两个老人春节怎么过?就在我万分为难之时,妈妈悄悄把我拉到厨房,一边使劲往我包里塞肉圆蛋饺、烧鸡香肠,一边说,她们家人少,我们家人多,你去她家过年,顺便代我问她爸爸、奶奶好!过了年,你们小两口再回家,家里年货多,少不了你喜欢吃的!
拎着那包热乎乎的年货,一出门我就哭了……一年到头,妈妈何尝不想新婚的小儿子、小儿媳和她团圆?一辈子颠沛流离的爸爸妈妈何尝不想一大家子围在一起,除夕吃上一顿美美的团圆饭?可是,善解人意的妈妈体谅儿子的难处,也心疼作为独女的儿媳妇,所以她早就计划好了,将年货让我们带到她家,开开心心陪两个孤单老人过年。年后,一大家子再聚,反正我们家人多,年后聚会日子多得很。
有妈妈在的日子,是我记忆里最温馨的过年。除夕下午,哥哥姐姐,嫂子姐夫,还有侄女儿、外甥女……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女的在厨房里各展厨艺,男的在客厅海阔天空韶叨,爷爷奶奶陪着孙辈在院里玩耍嬉戏,还有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和厨房里飘出的阵阵肉香,这浓郁深沉的年味儿,一辈子缠绕在我心头!
一晃,我们老了。
如今,我们去哪里过年,又和谁过年?
不能说儿女不孝顺,女儿年底刚刚回来和我们团圆半月,春节又买机票接公婆一家去新加坡过年,不欺不蔑,安排有礼周到。问题是,今年我们老两口和谁过年的问题并未解决。其实,到我们这个岁数,吃是吃不下了,过年无非图个喜庆,想和女儿一家团圆,须跋山涉水,万水千山,关键是你热络络跑过去,说不定热脸贴上冷屁股,人家还嫌你烦。所以这些年,我们有时去同样空巢的大哥大嫂家,有时干脆和老同学聚在一起过年。记得去年去老同学家,他们夫妻俩从小学到中学都是我同学,无巧不巧的是,他弟弟一家和我们私交也好。去年他家在饭店吃年夜饭,说你们老两口干脆来我家,人多,蹭个热闹。吃得高兴,说得兴起,我还说明年我来做东,还是原班人马,一个不要少。没想到年前,老同学已撒手西天……其实这些年,老友、老同学是渐次凋零,越走越稀!同样儿女不在身边的北京堂姐说,以后家里都要多装些监控,让国外的儿女时刻看到我们。否则,哪天倒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电视上春运红红火火,窗外寂寂寒夜里有零星爆竹声迢递,我站在阳台上发呆:今年又去哪里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