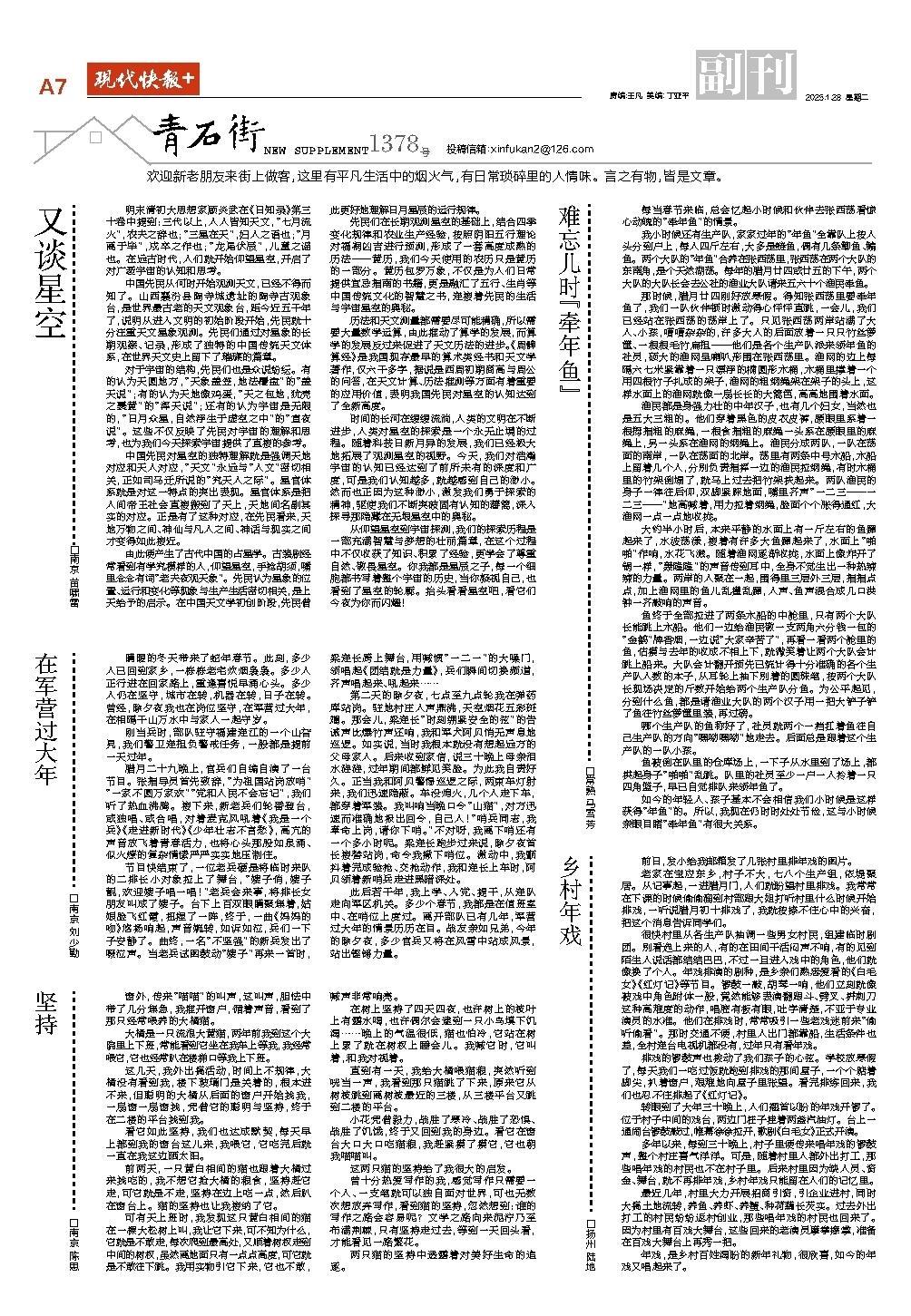□南京 苗啸雷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第三十卷中提到: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开始仰望星空,开启了对广袤宇宙的认知和思考。
中国先民从何时开始观测天文,已经不得而知了。山西襄汾县陶寺城遗址的陶寺古观象台,是世界最古老的天文观象台,距今近五千年了,说明从进入文明的初始阶段开始,先民就十分注重天文星象观测。先民们通过对星象的长期观察、记录,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天文体系,在世界天文史上留下了璀璨的篇章。
对于宇宙的结构,先民们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天圆地方,“天象盖笠,地法覆盘”的“盖天说”;有的认为天地像鸡蛋,“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的“浑天说”;还有的认为宇宙是无限的,“日月众星,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的“宣夜说”。这些不仅反映了先民对宇宙的理解和思考,也为我们今天探索宇宙提供了直接的参考。
中国先民对星空的独特理解就是强调天地对应和天人对应,“天文”永远与“人文”密切相关,正如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星官体系就是对这一特点的突出表现。星官体系是把人间帝王社会直接搬到了天上,天地间名副其实的对应。正是有了这种对应,在先民看来,天地万物之间、神仙与凡人之间、神话与现实之间才变得如此接近。
由此便产生了古代中国的占星学。古装剧经常看到有学究模样的人,仰望星空,手捻胡须,嘴里念念有词“老夫夜观天象”。先民认为星象的位置、运行和变化等现象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上天给予的启示。在中国天文学初创阶段,先民借此更好地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
先民们在长期观测星空的基础上,结合四季变化规律和农业生产经验,按照阴阳五行理论对福祸凶吉进行预测,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历法——黄历,我们今天使用的农历只是黄历的一部分。黄历包罗万象,不仅是为人们日常提供宜忌指南的书籍,更是融汇了五行、生肖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之书,连接着先民的生活与宇宙星空的奥秘。
历法和天文测量都需要尽可能精确,所以需要大量数学运算,由此推动了算学的发展,而算学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天文历法的进步。《周髀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算术类经书和天文学著作,仅六千多字,据说是西周初期商高与周公的问答,在天文计算、历法推测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表明我国先民对星空的认知达到了全新高度。
时间的长河在缓缓流淌,人类的文明在不断进步,人类对星空的探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已经极大地拓展了观测星空的视野。今天,我们对浩瀚宇宙的认知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可是我们认知越多,就越感到自己的渺小。然而也正因为这种渺小,激发我们勇于探索的精神,驱使我们不断突破固有认知的藩篱,深入探寻那隐藏在无垠星空中的奥秘。
从仰望星空到宇宙探测,我们的探索历程是一部充满智慧与梦想的壮丽篇章,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收获了知识、积累了经验,更学会了尊重自然、敬畏星空。你我都是星辰之子,每一个细胞都书写着整个宇宙的历史,当你凝视自己,也看到了星空的轮廓。抬头看看星空吧,看它们今夜为你而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