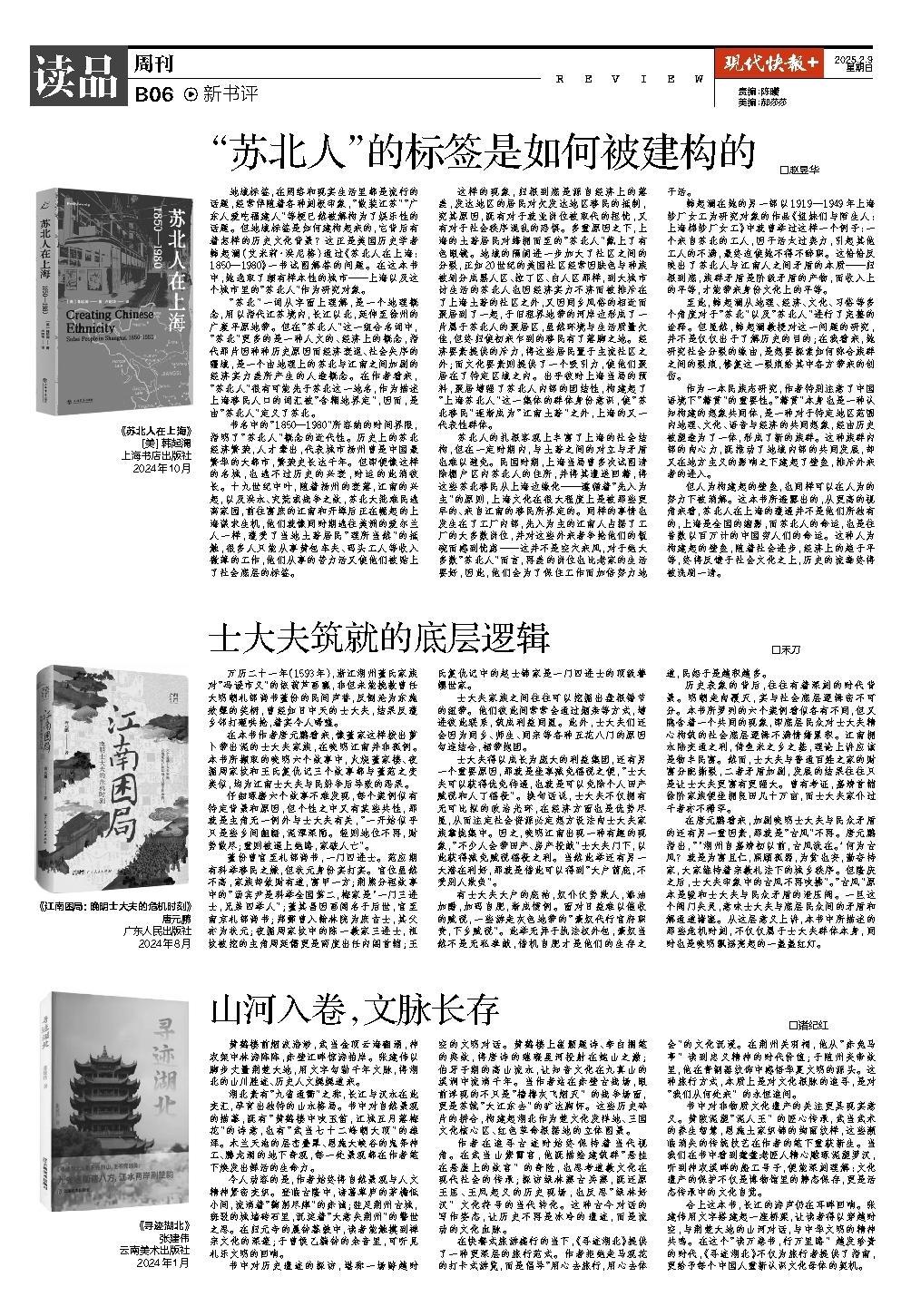□禾刀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浙江湖州董氏家族对“冯谖市义”的依葫芦画瓢,非但未能挽救曾任大明朝礼部尚书董份的民间声誉,反倒沦为东施效颦的笑柄,曾经如日中天的士大夫,结果反遭乡邻打砸哄抢,着实令人唏嘘。
在本书作者唐元鹏看来,像董家这样拨出萝卜带出泥的士大夫家族,在晚明江南并非孤例。本书所撷取的晚明六个故事中,火烧董家楼、夜掘周家坟和王氏复仇记三个故事都与董范之变类似,均为江南士大夫与民纷争后导致的恶果。
仔细琢磨六个故事不难发现,每个案例似有特定背景和原因,但个性之中又有某些共性,那就是主角无一例外与士大夫有关,“一开始似乎只是些乡间龃龉,泥潭深陷。轻则地位不再,财势散尽;重则被逼上绝路,家破人亡”。
董份曾官至礼部尚书,一门四进士。范应期有科举移民之嫌,但状元身份实打实。官位虽然不高,家族却敛财有道,富甲一方;荆熊分袒故事中的“汤宾尹是科举全国第二,梅家是‘一门三进士,兄弟四举人”;董其昌因画闻名于后世,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郑鄤曾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其父亦为状元;夜掘周家坟中的陈一教家三进士,祖坟被挖的主角周延儒更是两度出任内阁首辅;王氏复仇记中的赵士锦家是一门四进士的顶级簪缨世家。
士大夫家族之间往往可以挖掘出盘根错节的纽带。他们彼此间常常会通过姻亲等方式,增进彼此联系,筑成利益同盟。此外,士大夫们还会因为同乡、师生、同宗等各种五花八门的原因勾连结合,裙带抱团。
士大夫得以成长为庞大的利益集团,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坐享减免徭税之便,“士大夫可以获得优免待遇,也就是可以免除个人田产赋税和人丁徭役”。换句话说,士大夫不仅拥有无可比拟的政治光环,在经济方面也是优势尽显,从而注定社会资源必定想方设法向士大夫家族靠拢集中。因之,晚明江南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不少人会带田产、房产投献”士大夫门下,以此获得减免赋税徭役之利。当然此举还有另一大潜在利好,那就是借此可以得到“大户荫庇,不受别人欺负”。
有士大夫大户的庇祐,奴仆仗势欺人,添油加醋,加码自肥,渐成惯例。面对日益难以催收的赋税,一些游走灰色地带的“豪奴代行官府职责,下乡赋税”。此举无异于执法权外包,豪奴当然不是无私奉献,借机自肥才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民怨于是越积越多。
历史表象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明朝走向覆灭,实与社会底层逻辑密不可分。本书所罗列的六个案例看似各有不同,但又隐含着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底层民众对士大夫精心构筑的社会底层逻辑不满情绪累积。江南拥水陆交通之利,倚鱼米之乡之基,理论上讲应该是物丰民富。然而,士大夫与普通百姓之家的财富分配撕裂,二者矛盾加剧,发展的结果往往只是让士大夫更富有更强大。曾有考证,嘉靖首辅徐阶家族便坐拥良田几十万亩,而士大夫家仆过千者亦不稀罕。
在唐元鹏看来,加剧晚明士大夫与民众矛盾的还有另一重因素,那就是“古风”不再。唐元鹏指出,“‘湖州自嘉靖初以前,古风犹在。’何为古风?就是为富且仁,照顾孤弱,为贫也安,勤奋持家,大家维持着宗教礼法下的城乡秩序。但隆庆之后,士大夫印象中的古风不再吹拂”。“古风”原本是缓和士大夫与民众矛盾的泄压阀。一旦这个阀门失灵,意味士大夫与底层民众间的矛盾和解通道堵塞。从这层意义上讲,本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危机时刻,不仅仅属于士大夫群体本身,同时也是晚明飘摇亮起的一盏盏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