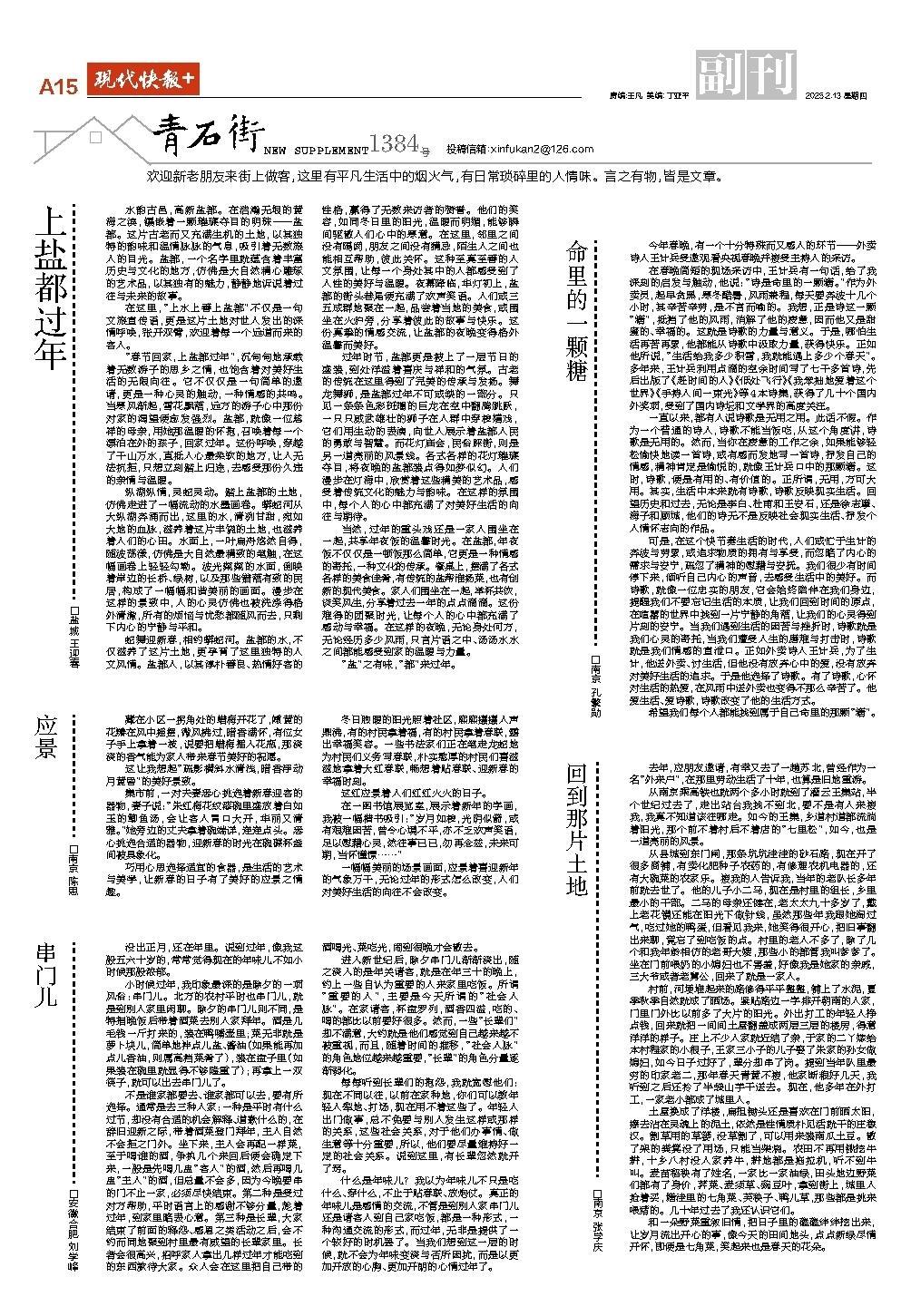□南京 张学庆
去年,应朋友邀请,有幸又去了一趟苏北,曾经作为一名“外来户”,在那里劳动生活了十年,也算是旧地重游。
从南京乘高铁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灌云王集站,半个世纪过去了,走出站台我找不到北,要不是有人来接我,我真不知道该往哪走。如今的王集,乡道村道都流淌着阳光,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七里松”,如今,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县城到东门闸,那条坑坑洼洼的砂石路,现在开了很多商铺,有卖化肥种子农药的,有修理农机电器的,还有大碗菜的农家乐。接我的人告诉我,当年的老队长多年前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小二马,现在是村里的组长,乡里最小的干部。二马的母亲还健在,老太太九十多岁了,戴上老花镜还能在阳光下做针线,虽然那些年我跟她淘过气,吃过她的鸭蛋,但看见我来,她笑得很开心,把旧事翻出来聊,竟忘了到吃饭的点。村里的老人不多了,除了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老哥大嫂,那些小的都管我叫爹爹了。坐在门前喂奶的小媳妇也不害羞,好像我是她家的亲戚,三大爷或者老舅公,回来了就是一家人。
村前,河埂堆起来的路修得平平整整,铺上了水泥,夏季秋季自然就成了晒场。紧贴路边一字排开朝南的人家,门里门外比以前多了大片的阳光。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挣点钱,回来就把一间间土屋翻盖成两层三层的楼房,得意洋洋的样子。庄上不少人家就近结了亲,于家的二丫嫁给本村程家的小根子,王家三小子的儿子娶了朱家的孙女做媳妇,如今日子过好了,辈分却串了岗。提到当年队里最穷的印家老二,那年春天青黄不接,他家断粮好几天,我听到之后还拎了半袋山芋干送去。现在,他多年在外打工,一家老小都成了城里人。
土屋换成了洋楼,扁担锄头还是喜欢在门前晒太阳,擦去沾在灵魂上的泥土,依然是性情质朴见活就干的庄稼汉。割草用的草篓,没草割了,可以用来装南瓜土豆。散了架的粪箕没了用场,只能当柴烧。农田不再用锹挖牛耕,十乡八村没人家养牛,耕地都是拖拉机,听不到牛叫。麦苗稻秧有了姓名,一家比一家油绿,田头地边野菜们都有了身价,荠菜、麦须草、豌豆叶,拿到街上,城里人抢着买,塘洼里的七角菜、芙秧子、鸭儿草,那些都是挑来喂猪的。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认识它们。
和一朵野菜重叙旧情,把日子里的磕磕绊绊挖出来,让岁月流出开心的事,像今天的田间地头,点点新绿尽情开怀,即便是七角菜,笑起来也是春天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