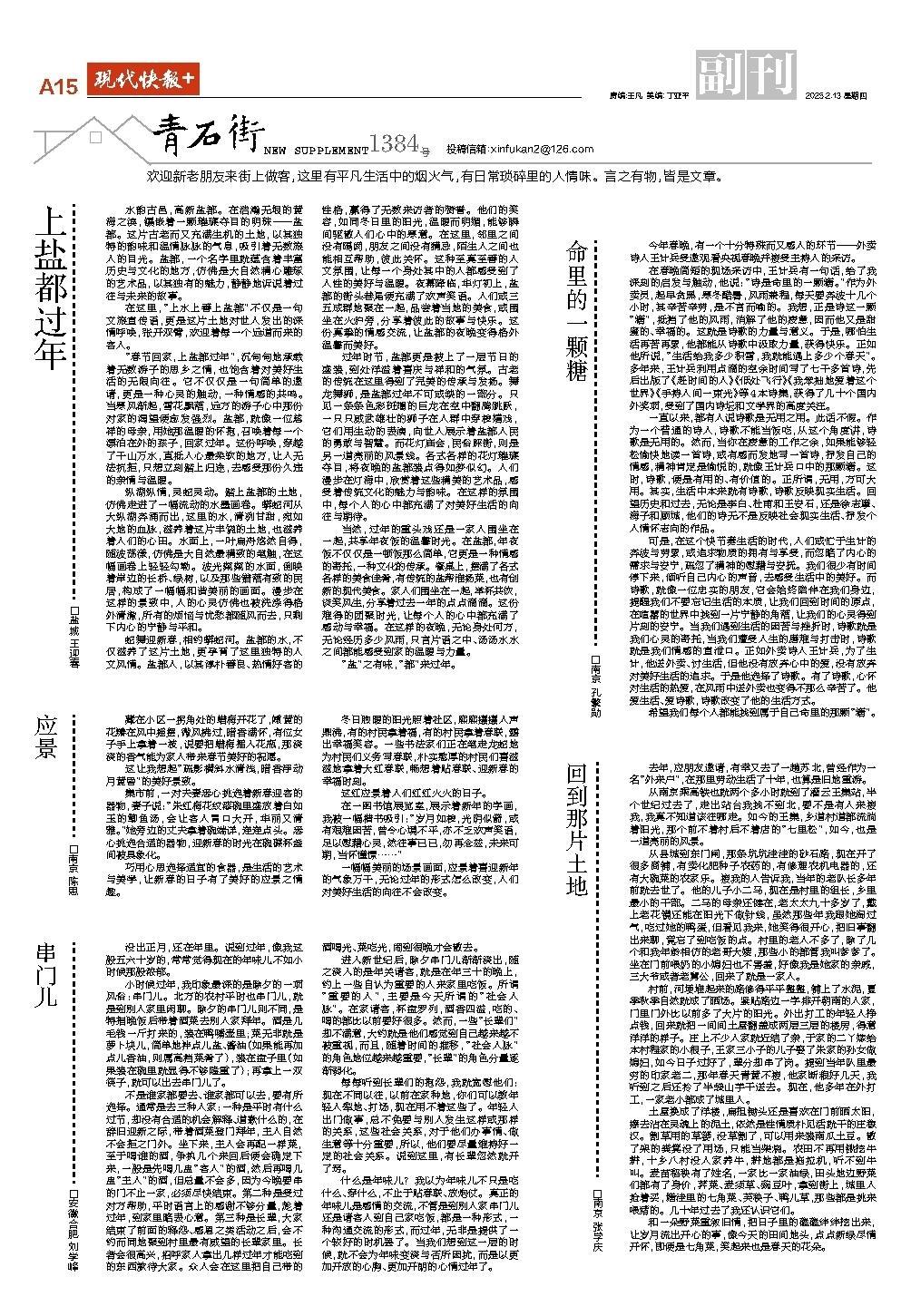□安徽合肥 刘学峰
没出正月,还在年里。说到过年,像我这般五六十岁的,常常觉得现在的年味儿不如小时候那般浓郁。
小时候过年,我印象最深的是除夕的一项风俗:串门儿。北方的农村平时也串门儿,就是到别人家里闲聊。除夕的串门儿则不同,是特指晚饭后带着酒菜去别人家拜年。酒是几毛钱一斤打来的,装在鸭嘴壶里;菜无非就是萝卜块儿,简单地拌点儿盐、酱油(如果能再加点儿香油,则属高档菜肴了),装在盘子里(如果装在碗里就显得不够隆重了);再拿上一双筷子,就可以出去串门儿了。
不是谁家都要去、谁家都可以去,要有所选择。通常是去三种人家:一种是平时有什么过节,却没有合适的机会解释、道歉什么的,在辞旧迎新之际,带着酒菜登门拜年,主人自然不会拒之门外。坐下来,主人会再配一样菜,至于喝谁的酒,争执几个来回后便会确定下来,一般是先喝几盅“客人”的酒,然后再喝几盅“主人”的酒,但总量不会多,因为今晚要串的门不止一家,必须尽快结束。第二种是受过对方帮助,平时语言上的感谢不够分量,趁着过年,到家里略表心意。第三种是长辈,大家结束了前面的释怨、感恩之类活动之后,会不约而同地聚到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辈家里。长者会很高兴,招呼家人拿出几样过年才能吃到的东西款待大家。众人会在这里把自己带的酒喝光、菜吃光,闹到很晚才会散去。
进入新世纪后,除夕串门儿渐渐淡出,随之淡入的是年关请客,就是在年三十的晚上,约上一些自认为重要的人来家里吃饭。所谓“重要的人”,主要是今天所谓的“社会人脉”。在家请客,杯盘罗列,酒香四溢,吃的、喝的都比以前要好很多。然而,一些“长辈们”却不满意,大约就是他们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不被重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人脉”的角色地位越来越重要,“长辈”的角色分量逐渐弱化。
每每听到长辈们的抱怨,我就宽慰他们:现在不同以往,以前在家种地,你们可以教年轻人犁地、打场,现在用不着这些了。年轻人出门做事,总不免要与别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对于他们办事情、做生意等十分重要,所以,他们要尽量维持好一定的社会关系。说到这里,有长辈忽然就开了窍。
什么是年味儿?我以为年味儿不只是吃什么、穿什么,不止于贴春联、放炮仗。真正的年味儿是感情的交流,不管是到别人家串门儿还是请客人到自己家吃饭,都是一种形式,一种沟通交流的形式,而过年,无非是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时机罢了。当我们想到这一层的时候,就不会为年味变淡与否所困扰,而是以更加开放的心胸、更加开朗的心情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