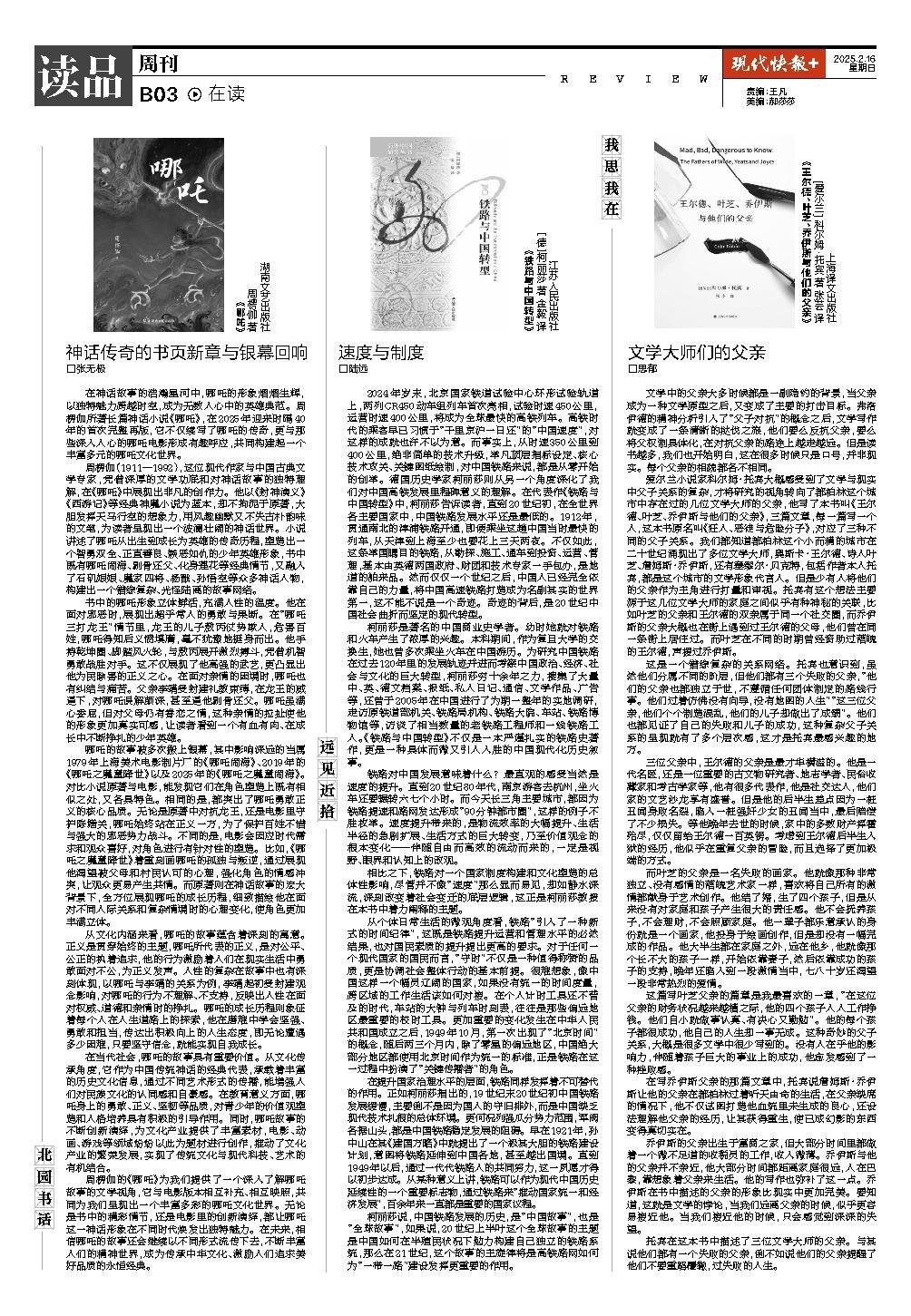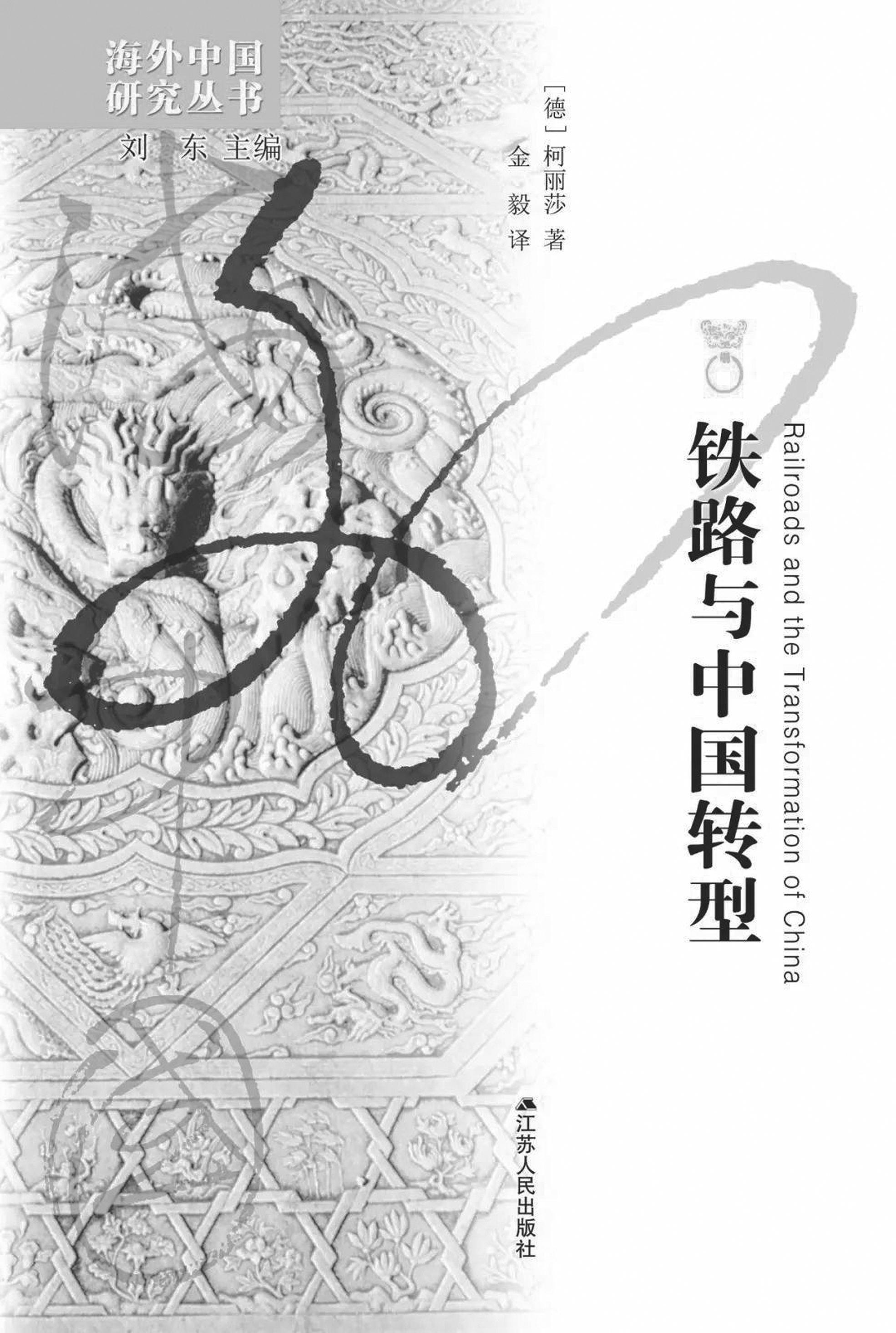□陆远
2024年岁末,北京国家铁道试验中心环形试验轨道上,两列CR450动车组列车首次亮相,试验时速450公里,运营时速400公里,将成为全球最快的高铁列车。高铁时代的乘客早已习惯于“千里京沪一日还”的“中国速度”,对这样的成就也许不以为意。而事实上,从时速350公里到400公里,绝非简单的技术升级,举凡顶层指标设定、核心技术攻关、关键图纸绘制,对中国铁路来说,都是从零开始的创举。德国历史学家柯丽莎则从另一个角度深化了我们对中国高铁发展里程碑意义的理解。在代表作《铁路与中国转型》中,柯丽莎告诉读者,直到20世纪初,在全世界各主要国家中,中国铁路发展水平还是最低的。1912年,贯通南北的津浦铁路开通,即便乘坐这趟中国当时最快的列车,从天津到上海至少也要花上三天两夜。不仅如此,这条举国瞩目的铁路,从勘探、施工、通车到投资、运营、管理,基本由英德两国政府、财团和技术专家一手包办,是地道的舶来品。然而仅仅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人已经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将中国高速铁路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奇迹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社会曲折而坚定的现代转型。
柯丽莎是著名的中国商业史学者。幼时她就对铁路和火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科期间,作为复旦大学的交换生,她也曾多次乘坐火车在中国游历。为研究中国铁路在过去120年里的发展轨迹并进而考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巨大转型,柯丽莎穷十余年之力,搜集了大量中、英、德文档案、报纸、私人日记、通信、文学作品、广告等,还曾于2005年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整年的实地调研,走访原铁道部机关、铁路局机构、铁路大院、车站、铁路博物馆等,访谈了相当数量的老铁路工程师和一线铁路工人。《铁路与中国转型》不仅是一本严谨扎实的铁路史著作,更是一种具体而微又引人入胜的中国现代化历史叙事。
铁路对中国发展意味着什么?最直观的感受当然是速度的提升。直到20世纪80年代,南京游客去杭州,坐火车还要辗转六七个小时。而今天长三角主要城市,都因为铁路提速和路网发达形成“90分钟都市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速度提升带来的,是物流效率的大幅提升、生活半径的急剧扩展、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乃至价值观念的根本变化——伴随自由而高效的流动而来的,一定是视野、眼界和认知上的改观。
相比之下,铁路对一个国家制度构建和文化塑造的总体性影响,尽管并不像“速度”那么显而易见,却如静水深流,深刻改变着社会变迁的底层逻辑,这正是柯丽莎教授在本书中着力阐释的主题。
从个体日常生活的微观角度看,铁路“引入了一种新式的时间纪律”,这既是铁路提升运营和管理水平的必然结果,也对国民素质的提升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而言,“守时”不仅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品质,更是协调社会整体行动的基本前提。很难想象,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果没有统一的时间度量,跨区域的工作生活该如何对接。在个人计时工具还不普及的时代,车站的大钟与列车时刻表,往往是那些偏远地区最重要的校时工具。更加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49年10月,第一次出现了“北京时间”的概念,随后两三个月内,除了零星的偏远地区,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使用北京时间作为统一的标准,正是铁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传播者”的角色。
在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层面,铁路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柯丽莎指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铁路发展缓慢,主要倒不是因为国人的守旧排外,而是中国缺乏现代技术扎根的总体环境。更何况列强瓜分势力范围,军阀各据山头,都是中国铁路稳定发展的阻碍。早在1921年,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铁路建设计划,意图将铁路延伸到中国各地,甚至越出国境。直到1949年以后,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共同努力,这一夙愿才得以初步达成。从某种意义上讲,铁路可以作为现代中国历史延续性的一个重要标志物,通过铁路来“推动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百余年来一直都是重要的国家议程。
柯丽莎说,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是“中国故事”,也是“全球故事”,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这个全球故事的主题是中国如何在半殖民状况下勉力构建自己独立的铁路系统,那么在21世纪,这个故事的主旋律将是高铁路网如何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