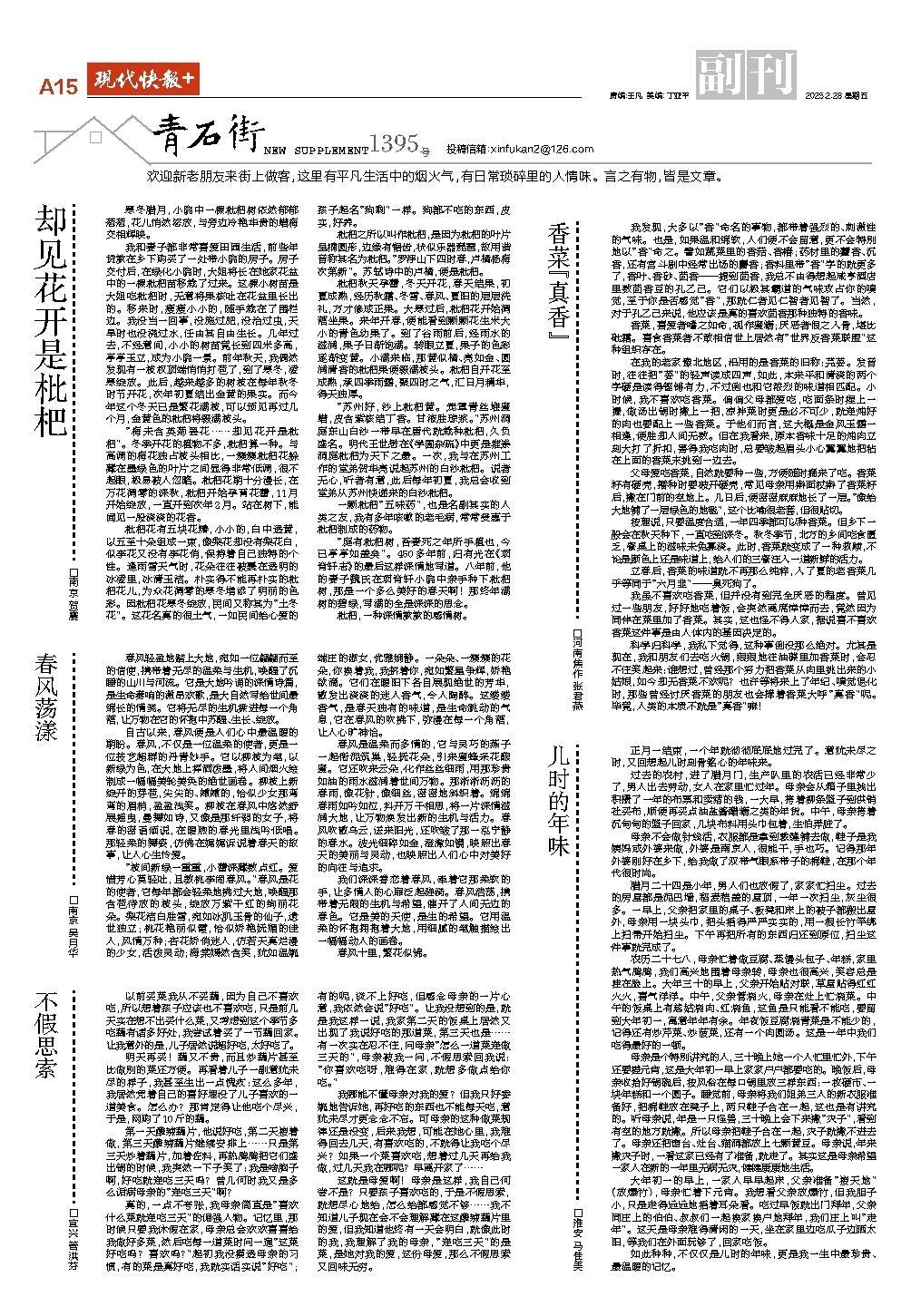□淮安 马佳美
正月一结束,一个年就彻彻底底地过完了。意犹未尽之时,又回想起儿时刻骨铭心的年味来。
过去的农村,进了腊月门,生产队里的农活已经非常少了,男人出去劳动,女人在家里忙过年。母亲会从箱子里找出积攒了一年的布票和卖猪的钱,一大早,挎着柳条篮子到供销社买布,顺便再买点油盐酱醋糖之类的年货。中午,母亲挎着沉甸甸的篮子回家,几块布料用头巾包着,生怕弄脏了。
母亲不会做针线活,衣服都是拿到裁缝铺去做,鞋子是我姨妈或外婆来做,外婆是南京人,很能干,手也巧。记得那年外婆刚好在乡下,给我做了双带气眼系带子的棉鞋,在那个年代很时尚。
腊月二十四是小年,男人们也放假了,家家忙扫尘。过去的房屋都是泥巴墙,稻麦秸盖的屋顶,一年一次扫尘,灰尘很多。一早上,父亲把家里的桌子、板凳和床上的被子都搬出屋外,母亲用一块头巾,把头捂得严严实实的,用一根长竹竿绑上扫帚开始扫尘。下午再把所有的东西归还到原位,扫尘这件事就完成了。
农历二十七八,母亲忙着做豆腐、蒸馒头包子、年糕,家里热气腾腾,我们高兴地围着母亲转,母亲也很高兴,笑容总是挂在脸上。大年三十的早上,父亲开始贴对联,草屋贴得红红火火,喜气洋洋。中午,父亲管烧火,母亲在灶上忙烧菜。中午的饭桌上有慈姑烧肉、红烧鱼,这鱼是只能看不能吃,要留到大年初一,寓意年年有余。年夜饭豆腐烧青菜是不能少的,记得还有炒芹菜、炒菠菜,还有一个肉圆汤。这是一年中我们吃得最好的一顿。
母亲是个特别讲究的人,三十晚上她一个人忙里忙外,下午还要搓元宵,这是大年初一早上家家户户都要吃的。晚饭后,母亲收拾好锅碗后,按风俗在每口锅里放三样东西:一枚硬币、一块年糕和一个圆子。睡觉前,母亲将我们姐弟三人的新衣服准备好,把棉鞋放在凳子上,两只鞋子合在一起,这也是有讲究的。听母亲说,年是一只怪兽,三十晚上会下来撒“灾子”,看到有空的地方就撒。所以母亲把鞋子合在一起,灾子就撒不进去了。母亲还把窗台、灶台、猫洞都放上七颗黄豆。母亲说,年来撒灾子时,一看这家已经有了准备,就走了。其实这是母亲希望一家人在新的一年里无病无灾,健健康康地生活。
大年初一的早上,一家人早早起床,父亲准备“接天地”(放爆竹),母亲忙着下元宵。我想看父亲放爆竹,但我胆子小,只是走得远远地捂着耳朵看。吃过早饭就出门拜年,父亲同庄上的伯伯、叔叔们一起挨家挨户地拜年,我们庄上叫“走年”。这天是母亲难得清闲的一天,坐在家里边吃瓜子边晒太阳,等我们在外面玩够了,回家吃饭。
如此种种,不仅仅是儿时的年味,更是我一生中最珍贵、最温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