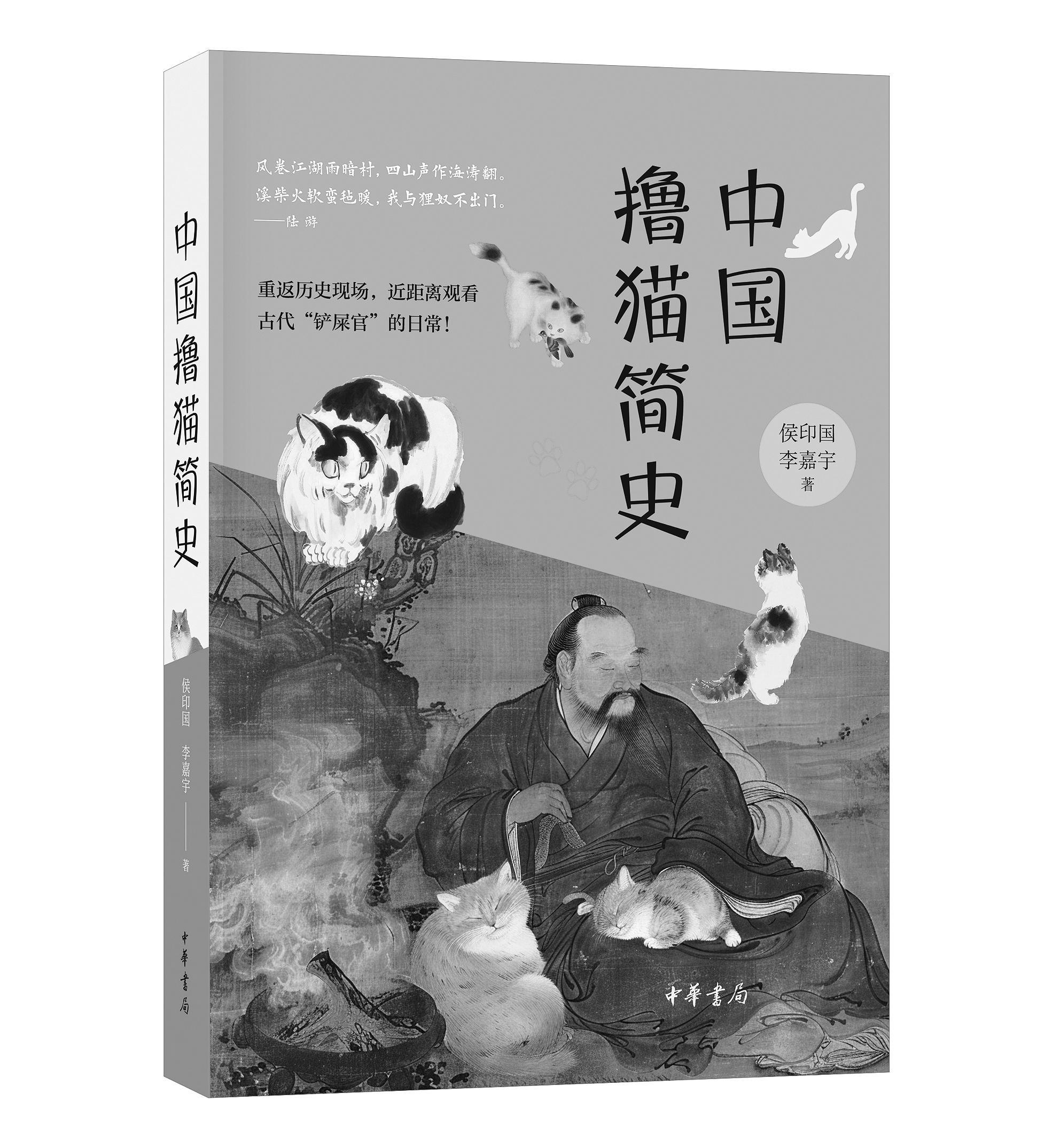内容简介
现如今爱猫人士很多,为了家中可爱的小猫咪没少投入。那么,古代“铲屎官”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呢?《中国撸猫简史》梳理了从先秦两汉到明清,猫是怎样从野外进入到人类社会,进而成为受人喜爱的宠物的历程,以及猫对民间信仰、中国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读者能从中了解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关于猫神、猫妖、猫精怪等扑朔迷离的传说故事;还有现在习以为常的宠物美容,古代也有,当时被称为“改猫犬”;再比如,逗猫棒,这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创造,唐宋时期就有了,其中有一种高端的被称为“红丝标杖”。内容趣味十足,作者又有着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专业背景,这本书可谓既好玩儿又靠谱。
宋人爱猫,猫成为市井百姓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一些关于猫的民俗逐渐形成。这些养猫的民间习俗,大部分在元代定型,并深刻影响后世。六月六日的“浴猫节”便是典型的例子。
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洗澡频率很低。在先秦时期,一年中一些固定的时节会举行含有洗澡沐浴内容的仪式,后来形成了三月三日修禊的传统。在当时,贵族们才正儿八经洗澡,周王的使臣中有个职务叫“宫人”,职责之一就是帮周王洗澡。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青铜器里,有一部分就是用来洗澡的。很多学校作为校训的名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原本就是刻在商汤洗澡盆上的铭文。到了汉代,官员们洗澡稍微频繁了一些,也不过是五天一次。古人把放假叫“休沐”,其实就是放假给官员洗澡。虽然有着“贵妃出浴”之类的经典故事,但唐代官员贵族们洗澡也算不上频繁,普通人洗澡就更加困难了。著名诗人白居易,我们印象中总觉得这位香山居士是神仙一流的人物,但他自己的诗里说自己“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现代人可能很难接受。到了宋代,洗澡就成了日常生活中很寻常的事情了。人们可以在家洗澡,很多人家中都设置有专门洗澡的空间。市井中公共浴室也开始兴起,洗澡逐渐成为一种普通百姓热爱的享受。人们洗澡日常化的时期,也是养猫日常化的时期,给猫洗澡自然也会出现。但在宋代,六月六日浴猫狗的习俗尚未普遍兴起,在南宋晚期《梦粱录》《乾淳岁时记》《武林旧事》等关于南方风俗的书籍中均未提及。
最早关于浴猫节日的记载,是在元代汪汝懋编撰的《山居四要》卷四,在“六月六日”条下记载“本日浴猫狗”。早期浴猫是在南方,但在明代中晚期,已经流传到了北方。在当时的北京,女性在六月六这一天洗头发,把猫猫狗狗都带到河边洗澡,皇家所养的大象也在这天送到城外水边洗浴。给猫狗洗澡的方式非常简单粗暴,和今天宠物店里给猫犬洗澡完全不同,就是直接把猫狗扔到河里。明代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中便如实记录:“六月六日,吴俗悉投猫犬于水中。”
元代开始,“六月六,浴猫狗”便成了民间流传的谚语,一些地区认为这天给猫洗澡,能防虱子,能治癞病。如清代孔尚任《节序同风录》中说“浴猫狗于池,治癞”。但为什么是在六月六日这天给猫狗洗澡呢?实际上明代人已经搞不清楚原因了,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记载,六月六日这天,“郡人舁猫狗浴之河中,致有汨没淤泥踉跄就毙者,其取义竟不可晓也”。杭州人在这天抬着猫狗到河边洗澡,有陷进河边淤泥里爬不出来的。对于这个习俗大家都习以为常,却都不知道其缘由何在,这正可谓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了。清代人自然更是不清楚原因,清代顾禄记录苏州一带民俗的《清嘉录》中收入郭麐的《浴猫犬词》:“六月六,家家猫犬水中浴。不知此语从何来,展转流传竟成俗。流传不实为丹青,孰知物始睹厥形。孰居庄严成坏住,劫前八万四千横竖飞走一一知其名。而况白老鸟龙不同族,何以降日为同生。一笑姑置之,听我为媒词。司马高才号犬子,拓跋英雄称佛狸,乌员锦带纷绮丽,韩卢宋鹊尤魁奇。世上纷纷每生者,李义府与景升儿。金钱犀果洗若属,但有痴骨无妍皮。猫乎犬乎好自爱,洞里云中久相待。伐毛洗髓三千年,会见爬沙登上界。”他也表示不知道这个习俗从何而来。
尽管如此,人们六月六浴猫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清代黄钊的《读白华草堂诗》中就收录了两首关于浴猫的诗,其一是《消夏杂诗其六》:“节到观莲斗玉肌,家家猫狗浴从窥。梦回却忆春明事,正是金河洗象时。”其二是《暑窗即事》:“闲来云母窗间坐,醉向杨妃榻畔眠。一月雨晴存日记,呼龙时候浴猫天。”
明代有个关于浴猫日的知名段子。杨循吉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字君卿,一作君谦,号南峰、雁村居士,好读书,每得意则手舞足蹈,不能自禁,人称“颠主事”。又极喜藏书,闻某人家有异本,必购求缮写。性狷隘好持人短长,以学问穷人。有一年的四月初八,有客人来拜访杨循吉,这天正好是佛教的浴佛节,因此杨循吉以洗浴为由推辞。客人不知道浴佛的事情,误以为是杨循吉过于傲慢,心中很是不满。到了六月六日,杨循吉去回拜这位客人,客人便也用洗浴为理由推辞,借此报复他。杨循吉便在他家墙上题写了一首很有趣的诗:“君昔访我我洗浴,我今访君君洗浴。君访我时四月八,我访君时六月六。”
其实古人关于养猫的习俗还有不少,除了六月六洗猫,元代以来杭州一带还以五月二十日为分龙节,选在这天分猫。各地分龙节的时间不尽相同,比如池州一带,就以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两天为分龙节。
除了这两个节日,宋代以来,人们在喝人口粥时,也要给猫准备一份。人口粥在南宋流行,也叫口数粥,是一种赤豆粥。之所以取名人口粥,意思就是按照家中人口所煮的粥,在算人数时,哪怕刚刚出生的小孩子,都要为他熬一碗粥,甚至家中的猫猫狗狗,也都算人口。当时人们都会在腊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喝这种粥,但当时就已经搞不清楚喝粥的缘由。《梦粱录》里说二十五日吃,不知道是什么典故,是为了祭祀食神。《武林旧事》则说是二十四日吃。宋代将这天称为交年节,是祭祀灶神的日子。灶神承担着上天言好事的职责,所以人们往往用蜜糖涂抹在灶神画像的嘴上,希望他上天之后能够多说好话,《武林旧事》中就认为人口粥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但南宋诗人范成大则描述二十五日吃人口粥,远行没有回家的人口都要准备一份,在晚上全家一起食用,主要是为了避瘟疫。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中说苏州一带二十五日吃人口粥,是为了避瘟气。范成大的诗中还提到苏州“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不管怎么样,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腊月二十五日喝人口粥都是为了平安健康。张侃《田家岁晩》诗云:“粥分口数顾长健,不卖痴呆侬自当。”很多民俗的起源都有种种传说,但最终都归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古代清明节小孩子往往头戴柳圈,据说始于唐中宗,是为了避瘟疫。元代以后很多人家给家中猫儿也会准备一个。明代冯应《月令广义》中说:“今俗清明以柳圈小儿戴之,至于猫狗,亦以柳圈,盖辟疠遗意。”清代朱联芝《瓯中纪俗诗注》中说:“清明日,瓯人小儿及猫犬皆戴以杨柳圈,此亦风俗之偏。”
除了节日之外,元代以来,还有不少和养猫相关的民俗。
古人养蚕,往往也要养猫守护,《蚕书》中说“乡人养蚕,多畜猫以卫之”,当时称之“蚕猫”。
购买小猫有许多讲究,在《大宋猫市》中已经有所解释,后代又出现了《纳猫经》《相猫经》之类的经验总结。民间还有一些相关习俗,比如《医统》中记录有买到小猫后不走失的秘诀:小猫到家后,先喂给一两片猪肝,然后把猫带出家门,用细竹枝轻轻鞭打,驱赶回家后,再喂给两片猪肝。“如此数次,永不走。”
猫到家后,也有“朝喂猫,夜喂狗”的俗语,喂狗要在晚上,喂猫则在白天,古人认为这是“取其力以时也”。明清一些地区在家中为猫留有猫洞,是在“人家房屋窗牗间,开一小穴,只容猫儿出入”,有时在灶台上也设置专门的猫洞,是为了“猫儿畏冷,即入卧焉”。
江淮一带,家里丢了猫,就会祭祀灶神,在祈祷之外,还要用绳子把灶头捆起来。据说这样非常灵应,三两天之内猫就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