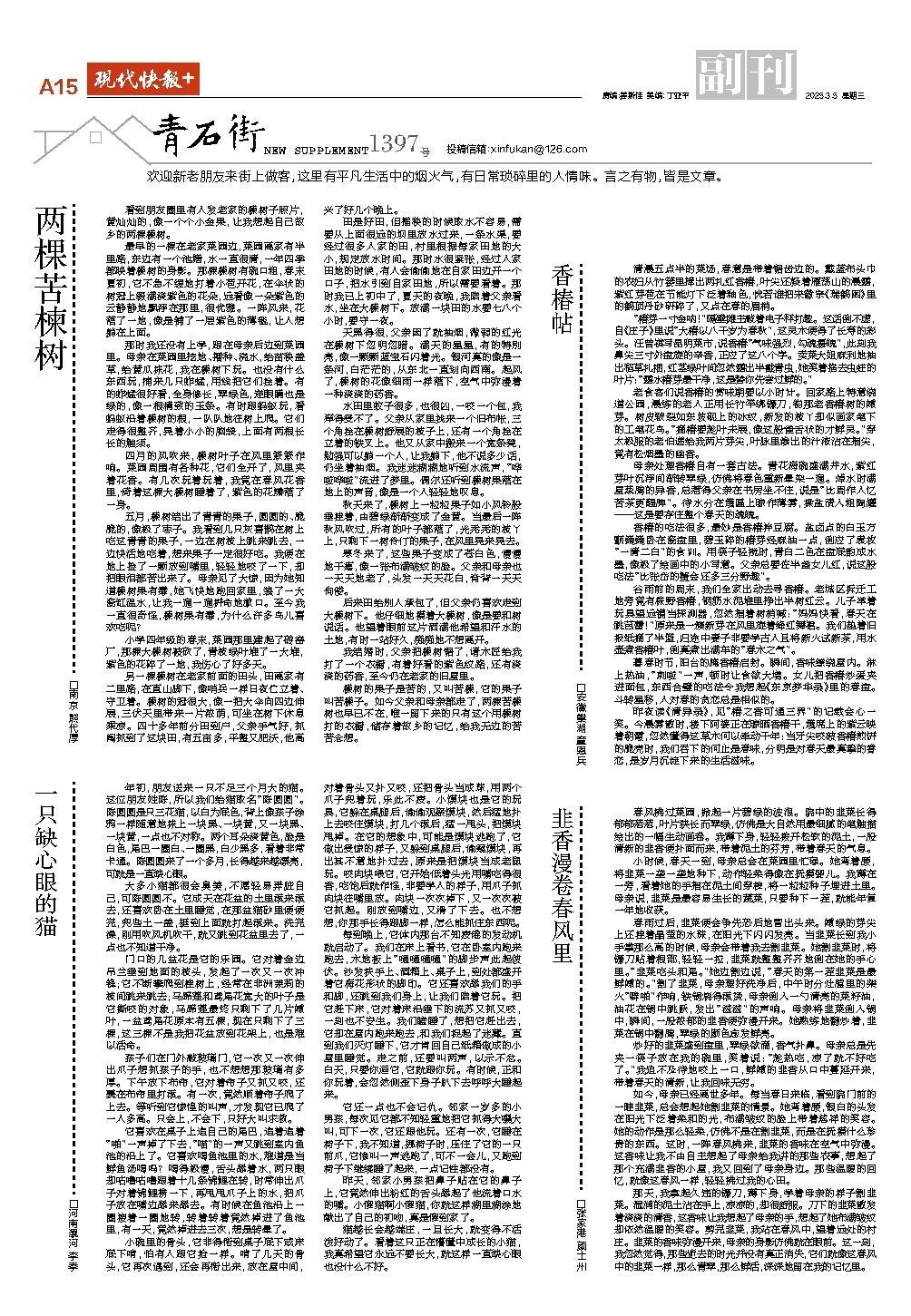□安徽巢湖 童恩兵
清晨五点半的菜场,春意是带着锯齿边的。戴蓝布头巾的农妇从竹篓里捧出两扎红香椿,叶尖还凝着雁荡山的晨露,紫红芽苞在节能灯下泛着釉色,恍若谁把宋徽宗《瑞鹤图》里的鹤顶丹砂研碎了,又点在春的眉梢。
“椿芽一寸金呐!”隔壁摊主敲着电子秤打趣。这话倒不虚,自《庄子》里说“大椿以八千岁为春秋”,这灵木便得了长寿的彩头。汪曾祺写昆明菜市,说香椿“气味强烈,勾魂摄魄”,此刻我鼻尖三寸外盘旋的辛香,正应了这八个字。卖菜大姐麻利地抽出稻草扎捆,红茎绿叶间忽然露出半截青虫,她笑着掐去虫蛀的叶片:“露水椿芽最干净,这是替你先尝过鲜的。”
老食客们说香椿的赏味期要以小时计。回家路上特意绕道公园,晨练的老人正用长竹竿绑镰刀,钩那老香椿树的嫩芽。树皮皲裂如东坡砚上的冰纹,新发的枝丫却似画家笔下的工笔花鸟。“摘椿要趁叶未展,像这般雀舌状的才鲜灵。”穿太极服的老伯递给我两片芽尖,叶脉里渗出的汁液沾在指尖,竟有松烟墨的幽香。
母亲处理香椿自有一套古法。青花海碗盛满井水,紫红芽叶沉浮间渐转翠绿,仿佛将春色重新晕染一遍。焯水时满屋蒸腾的异香,总惹得父亲在书房坐不住,说是“比周作人忆苦茶更醒脾”。待水分在篾匾上晾作薄雾,揉盐渍入粗陶罐——这是要存住整个春天的魂魄。
香椿的吃法很多,最妙是香椿拌豆腐。盐卤点的白玉方颤巍巍卧在瓷盘里,碧玉碎的椿芽经麻油一点,倒应了袁枚“一清二白”的食训。用筷子轻搅时,青白二色在盘底韵成水墨,像极了绘画中的小写意。父亲总要佐半盏女儿红,说这般吃法“比张岱的蟹会还多三分野趣”。
谷雨前的周末,我们全家出动去寻香椿。老城区拆迁工地旁竟有株野香椿,钢筋水泥堆里挣出半树红云。儿子举着玩具望远镜当探测器,忽然指着树梢喊:“妈妈快看,春天在跳芭蕾!”原来是一簇新芽在风里旋着绛红舞裙。我们垫着旧报纸摘了半篮,归途中妻子非要学古人且将新火试新茶,用水壶煮香椿叶,倒真煮出满车的“春木之气”。
暮春时节,阳台的腌香椿启封。瞬间,香味缭绕屋内。淋上热油,“刺啦”一声,顿时让食欲大增。女儿把香椿炒蛋夹进面包,东西合璧的吃法令我想起《东京梦华录》里的春盘。斗转星移,人对春的贪恋总是相似的。
昨夜读《清异录》,见“椿之香可通三界”的记载会心一笑。今晨雾散时,楼下阿婆正在晾晒香椿干,篾席上的紫云映着朝霞,忽然懂得这草木何以牵动千年:当牙尖咬破香椿煎饼的脆壳时,我们吞下的何止是春味,分明是对春天最真挚的眷恋,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生活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