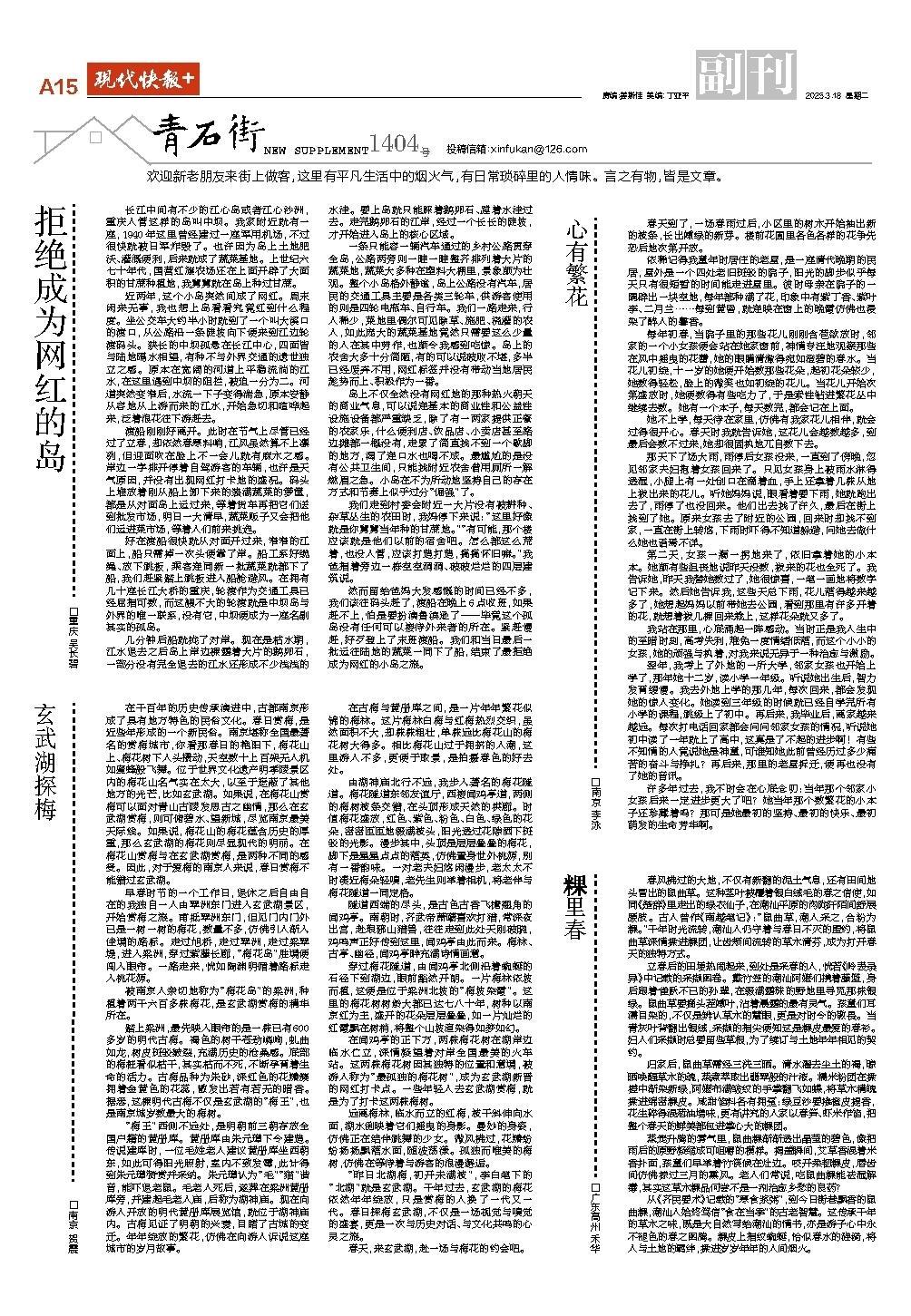□重庆 吴长碧
长江中间有不少的江心岛或者江心沙洲,重庆人管这样的岛叫中坝。我家附近就有一座,1940年这里曾经建过一座军用机场,不过很快就被日军炸毁了。也许因为岛上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后来就成了蔬菜基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营红旗农场还在上面开辟了大面积的甘蔗种植地,我舅舅就在岛上种过甘蔗。
近两年,这个小岛突然间成了网红。周末闲来无事,我也想上岛看看究竟红到什么程度。坐公交车大约半小时就到了一个叫大溪口的渡口,从公路沿一条陡坡向下便来到江边轮渡码头。狭长的中坝孤悬在长江中心,四面皆与陆地隔水相望,有种不与外界交通的遗世独立之感。原本在宽阔的河道上平稳流淌的江水,在这里遇到中坝的阻拦,被迫一分为二。河道突然变窄后,水流一下子变得湍急,原本安静从容地从上游而来的江水,开始急切和喧哗起来,泛着浪花往下游赶去。
渡船刚刚好离开。此时在节气上尽管已经过了立春,却依然春寒料峭,江风虽然算不上凛冽,但迎面吹在脸上不一会儿就有麻木之感。岸边一字排开停着自驾游客的车辆,也许是天气原因,并没有出现网红打卡地的盛况。码头上堆放着刚从船上卸下来的装满蔬菜的箩筐,都是从对面岛上运过来,等着货车再把它们送到批发市场,明日一大清早,蔬菜贩子又会把他们运进菜市场,等着人们前来挑选。
好在渡船很快就从对面开过来,窄窄的江面上,船只需掉一次头便靠了岸。船工系好缆绳、放下跳板,乘客连同新一批蔬菜就都下了船,我们赶紧踏上跳板进入船舱避风。在拥有几十座长江大桥的重庆,轮渡作为交通工具已经屈指可数,而这艘不大的轮渡就是中坝岛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没有它,中坝便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岛。
几分钟后船就拢了对岸。现在是枯水期,江水退去之后岛上岸边裸露着大片的鹅卵石,一部分没有完全退去的江水还形成不少浅浅的水洼。要上岛就只能踩着鹅卵石、蹚着水洼过去。走完鹅卵石的江岸,经过一个长长的陡坡,才开始进入岛上的核心区域。
一条只能容一辆汽车通过的乡村公路贯穿全岛,公路两旁则一畦一畦整齐排列着大片的蔬菜地,蔬菜大多种在塑料大棚里,景象颇为壮观。整个小岛格外静谧,岛上公路没有汽车,居民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各类三轮车,供游客使用的则是四轮电瓶车、自行车。我们一路走来,行人稀少,菜地里偶尔可见除草、施肥、浇灌的农人,如此庞大的蔬菜基地竟然只需要这么少量的人在其中劳作,也颇令我感到吃惊。岛上的农舍大多十分简陋,有的可以说破败不堪,多半已经废弃不用,网红标签并没有带动当地居民趁势而上、积极作为一番。
岛上不仅全然没有网红地的那种热火朝天的商业气息,可以说连基本的商业性和公益性设施设备都严重缺乏,除了有一两家提供正餐的农家乐,什么便利店、饮品店、小卖店甚至路边摊都一概没有,走累了简直找不到一个歇脚的地方,渴了连口水也喝不成。最尴尬的是没有公共卫生间,只能找附近农舍借用厕所一解燃眉之急。小岛在不为所动地坚持自己的存在方式和节奏上似乎过分“倔强”了。
我们走到村委会附近一大片没有被耕种、杂草丛生的农田时,我妈停下来说:“这里好像就是你舅舅当年种的甘蔗地。”“有可能,那个楼应该就是他们以前的宿舍吧。怎么都这么荒着,也没人管,应该打造打造,搞搞怀旧嘛。”我爸指着旁边一栋空空洞洞、破破烂烂的四层建筑说。
然而留给爸妈大发感慨的时间已经不多,我们该往码头赶了,渡船在晚上6点收班,如果赶不上,怕是要扮演鲁滨逊了——毕竟这个孤岛没有任何可以接待外来者的所在。紧赶慢赶,好歹登上了末班渡船。我们和当日最后一批运往陆地的蔬菜一同下了船,结束了最拒绝成为网红的小岛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