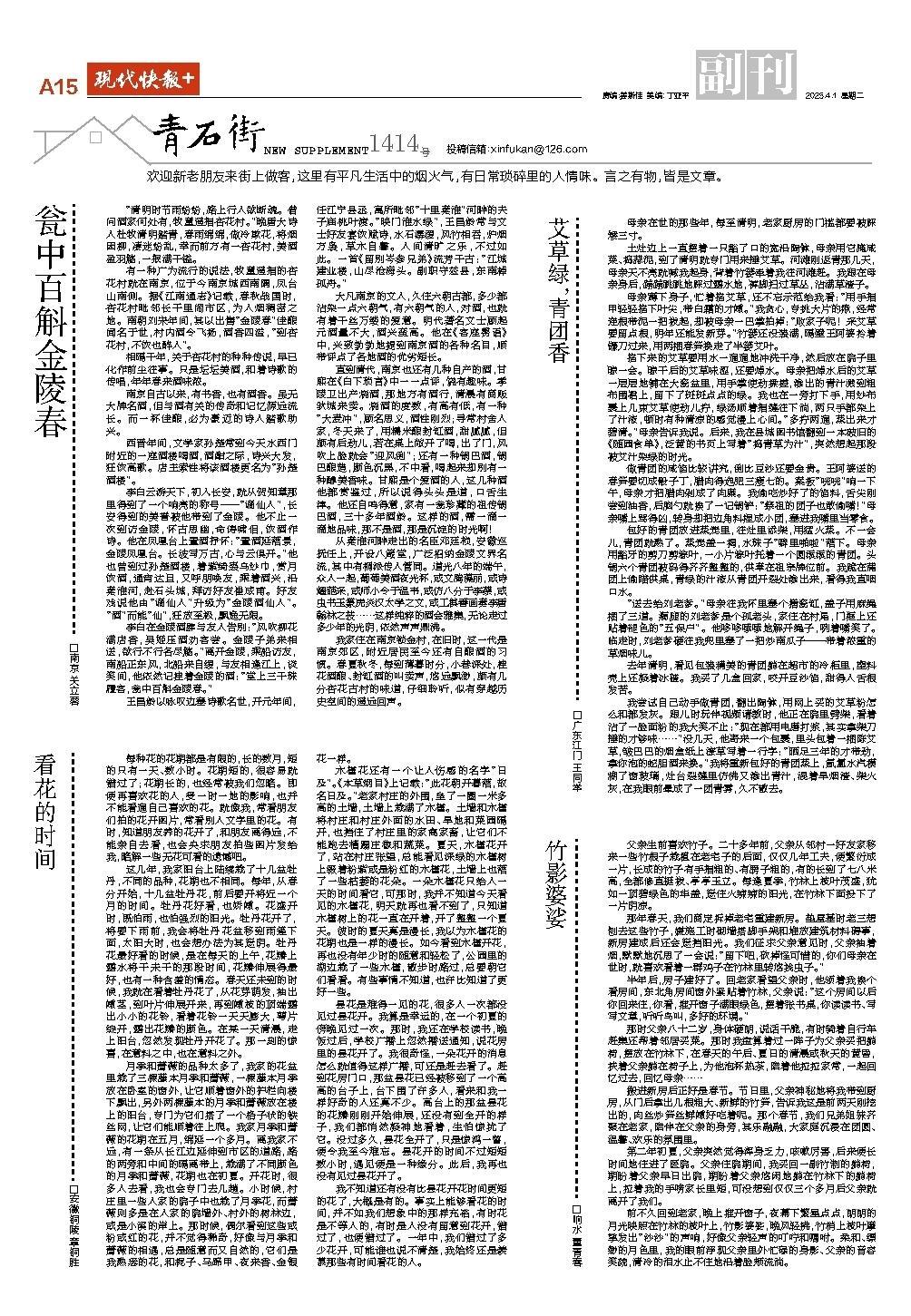□南京 关立蓉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晚唐大诗人杜牧清明踏青,春雨绵绵,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凄迷纷乱,幸而前方有一杏花村,美酒盈羽觞,一抿满千镒。
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说法,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就在南京,位于今南京城西南隅,凤台山南侧。据《江南通志》记载,春秋战国时,杏花村毗邻长干里闹市区,为人烟稠密之地。南朝刘宋年间,其以出售“金陵春”佳酿闻名于世,村内酒令飞扬,酒香四溢,“到杏花村,不饮也醉人”。
相隔千年,关于杏花村的种种传说,早已化作前尘往事。只是坛坛美酒,和着诗歌的传唱,年年春来酒味浓。
南京自古以来,有书香,也有酒香。虽无大牌名酒,但与酒有关的传奇和记忆源远流长。而一杯佳酿,必为豪迈的诗人踏歌助兴。
西晋年间,文学家孙楚常到今天水西门附近的一座酒楼喝酒,酒酣之际,诗兴大发,狂饮高歌。店主索性将该酒楼更名为“孙楚酒楼”。
李白云游天下,初入长安,就从贺知章那里得到了一个响亮的称号——“谪仙人”,长安得到的美誉被他带到了金陵。他不止一次到访金陵,怀古思幽,命俦啸侣,饮酒作诗。他在凤凰台上置酒抒怀:“置酒延落景,金陵凤凰台。长波写万古,心与云俱开。”他也曾到过孙楚酒楼,着紫绮裘乌纱巾,赏月饮酒,通宵达旦,又呼朋唤友,乘着酒兴,沿秦淮河,赴石头城,拜访好友崔成甫。好友戏说他由“谪仙人”升级为“金陵酒仙人”。“酒”而能“仙”,狂放至极,飘逸无限。
李白在金陵酒肆与友人告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离开金陵,乘船访友,南船正东风,北船来自缓,与友相逢江上,谈笑间,他依然记挂着金陵的酒:“堂上三千珠履客,瓮中百斛金陵春。”
王昌龄以咏叹边塞诗歌名世,开元年间,任江宁县丞,寓所毗邻“十里秦淮”河畔的夫子庙桃叶渡。“映门淮水绿”,王昌龄常与文士好友宴饮赋诗,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一首《留别岑参兄弟》流芳千古:“江城建业楼,山尽沧海头。副职守兹县,东南棹孤舟。”
大凡南京的文人,久住六朝古都,多少都沾染一点六朝气,有六朝气的人,对酒,也就有着千丝万缕的爱意。明代著名文士顾起元酒量不大,酒兴蛮高。他在《客座赘语》中,兴致勃勃地提到南京酒的各种名目,顺带评点了各地酒的优劣短长。
直到清代,南京也还有几种自产的酒,甘熙在《白下琐言》中一一点评,饶有趣味。孝陵卫出产烧酒,那地方有酒行,清晨有商贩驮城来卖。烧酒的度数,有高有低,有一种“大麦冲”,顾名思义,酒性刚烈;寻常村舍人家,冬天来了,用糯米酿封缸酒,甜腻腻,但颇有后劲儿,若在桌上敞开了喝,出了门,风吹上脸就会“迎风倒”;还有一种锅巴酒,锅巴酿造,颜色沉黑,不中看,喝起来却别有一种醇美香味。甘熙是个爱酒的人,这几种酒他都赏鉴过,所以说得头头是道,口舌生津。他还自鸣得意,家有一瓮珍藏的祖传锅巴酒,三十多年酒龄。这样的酒,需一滴一滴地品味,那不是酒,那是沉淀的时光啊!
从秦淮河畔走出的名臣邓廷桢,安徽巡抚任上,开设八箴堂,广泛招纳金陵文界名流,其中有桐派传人管同。道光八年的端午,众人一起,葡萄美酒夜光杯,或文腾藻丽,或诗耀葩采,或师小令于温韦,或仿八分于李蔡,或虫书玉篆庑炎汉太学之文,或工棋善画奏李唐翰林之技……这样纯粹的酒会雅集,无论走过多少年的光阴,依然声声鼎沸。
我家住在南京锁金村,在旧时,这一代是南京郊区,附近居民至今还有自酿酒的习惯。春夏秋冬,每到薄暮时分,小巷深处,桂花酒酿、封缸酒的叫卖声,悠远飘渺,颇有几分杏花古村的味道,仔细聆听,似有穿越历史空间的遥远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