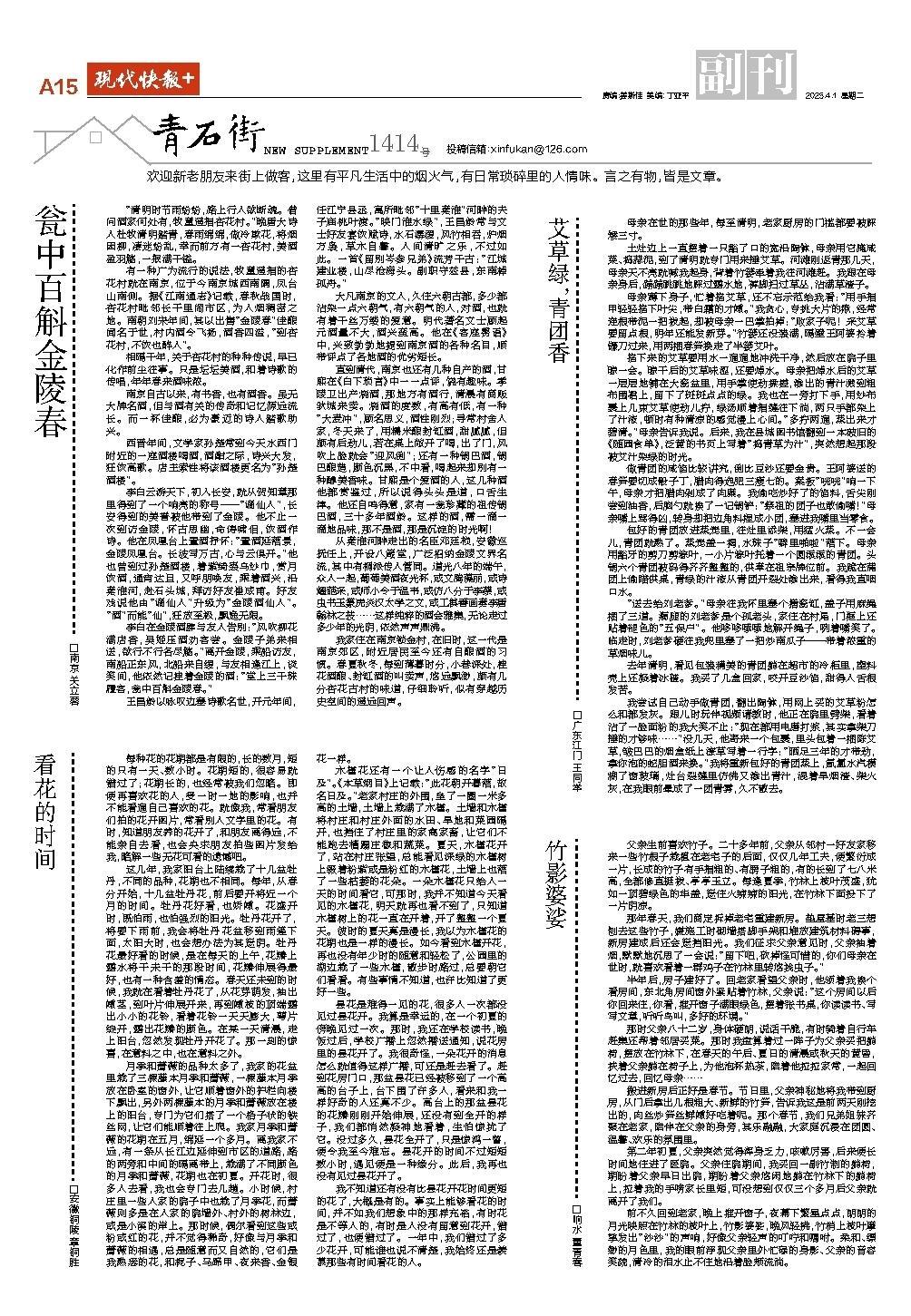□广东江门 王同举
母亲在世的那些年,每至清明,老家厨房的门槛都要被踩矮三寸。
土灶边上一直摆着一只豁了口的宽沿陶钵,母亲用它腌咸菜、捣蒜泥,到了清明就专门用来捶艾草。河滩刚返青那几天,母亲天不亮就喊我起身,背着竹篓牵着我往河滩赶。我跟在母亲身后,蹦蹦跳跳地踩过露水地,裤脚扫过草丛,沾满草渣子。
母亲蹲下身子,忙着掐艾草,还不忘示范给我看:“用手指甲轻轻掐下叶尖,带白霜的才嫩。”我贪心,专挑大片的揪,经常连根带泥一把拔起,却被母亲一巴掌拍掉:“败家子呢!采艾草要留点根,明年还能发新芽。”竹篓还没装满,隔壁王阿婆拎着镰刀过来,用两捆春笋换走了半篓艾叶。
掐下来的艾草要用水一遍遍地冲洗干净,然后放在院子里晾一会。晾干后的艾草味涩,还要焯水。母亲把焯水后的艾草一层层地铺在大瓷盆里,用手掌使劲揉搓,渗出的青汁溅到粗布围裙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绿。我也在一旁打下手,用纱布裹上几束艾草使劲儿拧,绿汤顺着指缝往下淌,两只手都染上了汁液,顿时有种清凉的感觉漫上心间。“多拧两遍,蒸出来才碧清。”母亲告诉我说。后来,我在县城图书馆翻到一本破旧的《随园食单》,泛黄的书页上写着“捣青草为汁”,突然想起那段被艾汁染绿的时光。
做青团的咸馅比较讲究,倒比豆沙还要金贵。王阿婆送的春笋要切成骰子丁,腊肉得选肥三瘦七的。案板“咣咣”响一下午,母亲才把腊肉剁成了肉糜。我偷吃炒好了的馅料,舌尖刚尝到油香,后脑勺就挨了一记锅铲:“祭祖的团子也敢偷嘴!”母亲嘴上骂得凶,转身却把边角料捏成小团,塞进我嘴里当零食。
包好的青团放进蒸笼里,往灶里添柴,用猛火蒸。不一会儿,青团就熟了。蒸笼盖一揭,水珠子“噼里啪啦”落下。母亲用豁牙的剪刀剪粽叶,一小片粽叶托着一个圆滚滚的青团。头锅六个青团被码得齐齐整整的,供奉在祖宗牌位前。我跪在蒲团上偷瞄供桌,青绿的汁液从青团开裂处渗出来,看得我直咽口水。
“送去给刘老爹。”母亲往我怀里塞个搪瓷缸,盖子用麻绳捆了三道。瘸腿的刘老爹是个孤老头,家住在村尾,门框上还贴着褪色的“五保户”。他哆哆嗦嗦地解开绳子,咧着嘴笑了。临走时,刘老爹硬往我兜里塞了一把炒南瓜子——带着浓重的草烟味儿。
去年清明,看见包装精美的青团躺在超市的冷柜里,塑料壳上还凝着冰碴。我买了几盒回家,咬开豆沙馅,甜得人舌根发苦。
我尝试自己动手做青团,翻出陶钵,用网上买的艾草粉怎么和都发灰。跟儿时玩伴视频请教时,他正在院里劈柴,看着沾了一脸面粉的我大笑不止:“现在都用电磨打浆,其实拿柴刀捶的才够味……”没几天,他寄来一个包裹,里头包着一捆陈艾草,皱巴巴的烟盒纸上潦草写着一行字:“晒足三年的才带劲,拿你泡的蛇胆酒来换。”我将重新包好的青团蒸上,氤氲水汽模糊了窗玻璃,灶台裂缝里仿佛又渗出青汁,混着旱烟渣、柴火灰,在我眼前晕成了一团青雾,久不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