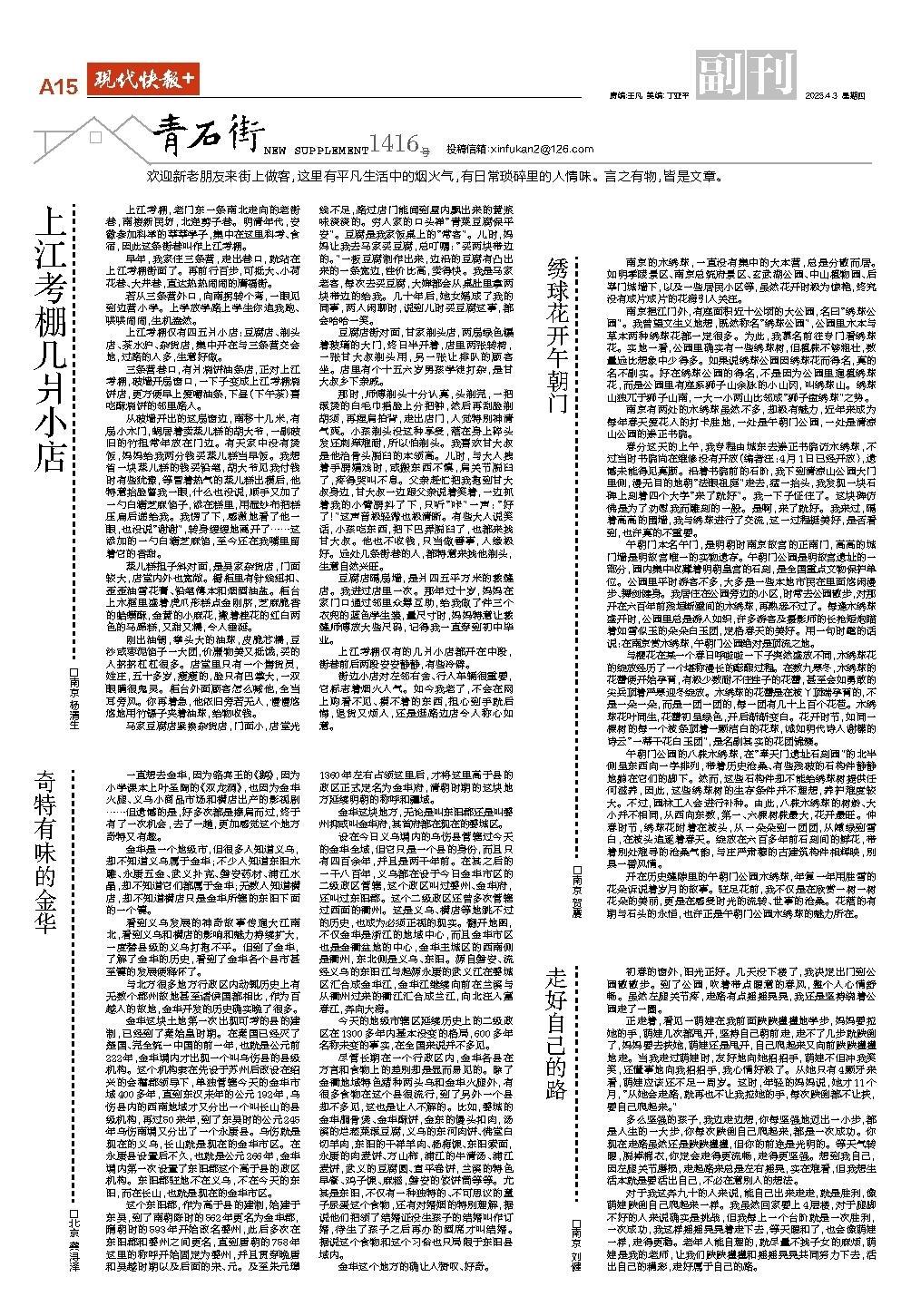□南京 杨清生
上江考棚,老门东一条南北走向的老街巷,南接新民坊,北连剪子巷。明清年代,安徽参加科举的莘莘学子,集中在这里科考、食宿,因此这条街巷叫作上江考棚。
早年,我家住三条营,走出巷口,就站在上江考棚街面了。再前行百步,可抵大、小荷花巷、大井巷,直达热热闹闹的膺福街。
若从三条营外口,向南拐转个弯,一眼见到边营小学。上学放学路上学生你追我跑、哄哄闹闹,生机盎然。
上江考棚仅有四五爿小店:豆腐店、剃头店、茶水炉、杂货店,集中开在与三条营交会地,过路的人多,生意好做。
三条营巷口,有爿烧饼油条店,正对上江考棚,破墙开扇窗口,一下子变成上江考棚烧饼店,更方便早上爱嚼油条,下昼(下午茶)喜吃酥烧饼的邻里路人。
从破墙开出的这扇窗边,南移十几米,有扇小木门,蜗居着卖蒸儿糕的胡大爷,一副破旧的竹担常年放在门边。有天家中没有烫饭,妈妈给我两分钱买蒸儿糕当早饭。我想省一块蒸儿糕的钱买铅笔,胡大爷见我付钱时有些犹豫,等冒着热气的蒸儿糕出模后,他特意抬脸瞥我一眼,什么也没说,顺手又加了一勺白糖芝麻馅子,添在糕里,用湿纱布把糕压扁后递给我。我愣了下,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也没说“谢谢”,转身缓缓地离开了……这添加的一勺白糖芝麻馅,至今还在我嘴里留着它的香甜。
蒸儿糕担子斜对面,是吴家杂货店,门面较大,店堂内外也宽敞。橱柜里有针线纽扣、歪歪油雪花膏、铅笔簿本和烟酒油盐。柜台上木框里盛着虎爪形糕点金刚脐,芝麻脆香的蛤蟆酥,金黄的小麻花,撒着桂花的红白两色的马蹄糕,又甜又糯,令人垂涎。
刚出油锅,拳头大的油球,皮脆芯糯,豆沙或枣泥馅子一大团,价廉物美又抵饿,买的人挤挤杠杠很多。店堂里只有一个售货员,姓庄,五十多岁,瘦瘦的,脸只有巴掌大,一双眼睛很鬼灵。柜台外面顾客怎么喊他,全当耳旁风。你再着急,他依旧旁若无人,慢慢悠悠地用竹镊子夹着油球,给物收钱。
马家豆腐店紧挨杂货店,门面小,店堂光线不足,路过店门能闻到屋内飘出来的黄浆味淡淡的。穷人家的口头禅“青菜豆腐保平安”。豆腐是我家饭桌上的“常客”。儿时,妈妈让我去马家买豆腐,总叮嘱:“买两块带边的。”一板豆腐制作出来,边沿的豆腐有凸出来的一条宽边,性价比高,卖得快。我是马家老客,每次去买豆腐,大婶都会从桌肚里拿两块带边的给我。几十年后,她女婿成了我的同事,两人闲聊时,说到儿时买豆腐这事,都会哈哈一笑。
豆腐店街对面,甘家剃头店,两扇绿色镶着玻璃的大门,终日半开着,店里两张转椅,一张甘大叔剃头用,另一张让排队的顾客坐。店里有个十五六岁男孩学徒打杂,是甘大叔乡下亲戚。
那时,师傅剃头十分认真,头剃完,一把滚烫的白毛巾捂脸上分把钟,然后再刮脸剃胡须,再捏肩拍背,走出店门,人觉特别神清气爽。小孩剃头没这种享受,落在身上碎头发还刺痒难耐,所以怕剃头。我喜欢甘大叔是他治骨头脱臼的本领高。儿时,与大人拽着手膀嬉戏时,或搬东西不慎,肩关节脱臼了,疼得哭叫不息。父亲赶忙把我抱到甘大叔身边,甘大叔一边跟父亲说着笑着,一边抓着我的小臂膀抖了下,只听“咔”一声:“好了!”这声音极轻微也极清晰。有些大人说笑话,小孩吃东西,把下巴弄脱臼了,也都来找甘大叔。他也不收钱,只当做善事,人缘极好。远处几条街巷的人,都特意来找他剃头,生意自然兴旺。
豆腐店隔扇墙,是爿四五平方米的裁缝店。我进过店里一次。那年过十岁,妈妈在家门口通过邻里众筹互助,给我做了件三个衣兜的蓝色学生装,量尺寸时,妈妈特意让裁缝师傅放大些尺码,记得我一直穿到初中毕业。
上江考棚仅有的几爿小店都开在中段,街巷前后两段安安静静,有些冷僻。
街边小店对左邻右舍、行人车辆很重要,它标志着烟火人气。如今我老了,不会在网上购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担心到手就后悔,退货又烦人,还是逛路边店令人称心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