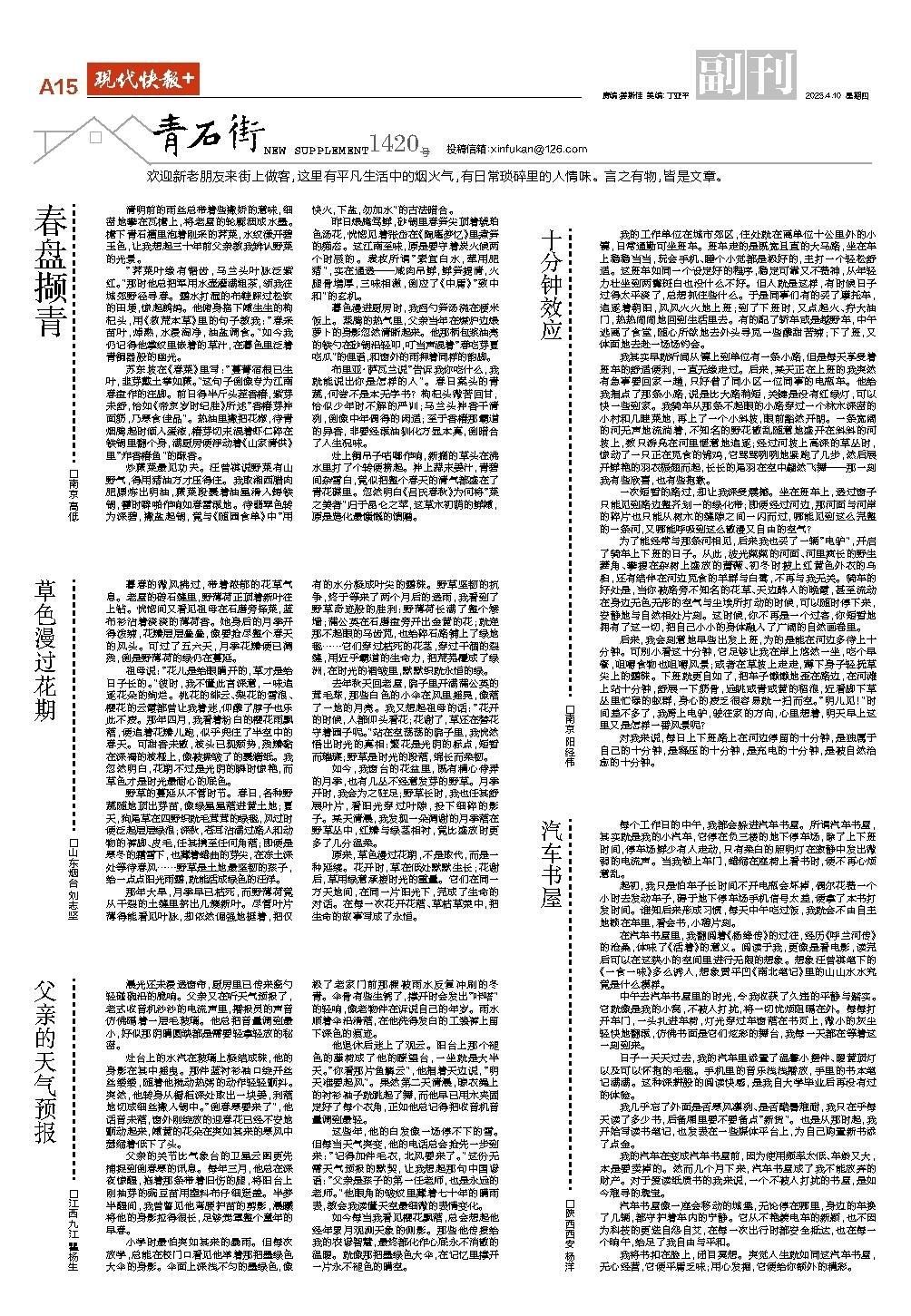□南京 高低
清明前的雨丝总带着些撒娇的意味,细密地攀在瓦檐上,将老屋的轮廓洇成水墨。檐下青石槽里泡着刚采的荠菜,水纹漾开碧玉色,让我想起三十年前父亲教我辨认野菜的光景。
“荠菜叶缘有锯齿,马兰头叶脉泛紫红。”那时他总把军用水壶灌满粗茶,领我往城郊野径寻春。露水打湿的布鞋踩过松软的田埂,惊起鹧鸪。他俯身掐下嫩生生的枸杞头,用《救荒本草》里的句子教我:“春采苗叶,焯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如今我仍记得他掌纹里嵌着的草汁,在暮色里泛着青铜器般的幽光。
苏东坡在《春菜》里写:“蔓菁宿根已生叶,韭芽戴土拳如蕨。”这句子倒像专为江南春盘作的注脚。前日得半斤头茬香椿,紫芽未舒,恰如《帝京岁时纪胜》所述“香椿芽拌面筋,乃寒食佳品”。热油里撒把花椒,待青烟腾起时倾入蛋液,椿芽切末混着虾仁碎在铁锅里翻个身,满厨房便浮动着《山家清供》里“炸香椿鱼”的酥香。
炒蕨菜最见功夫。汪曾祺说野菜有山野气,得用猪油方才压得住。我取湘西腊肉肥膘炼出明油,蕨菜段裹着油星滑入铸铁锅,霎时噼啪作响如春雷滚地。待翡翠色转为深碧,撒盐起锅,竟与《随园食单》中“用快火,下盐,勿加水”的古法暗合。
昨日煨腌笃鲜,砂锅里春笋尖顶着琥珀色汤花,恍惚见着张岱在《陶庵梦忆》里煮笋的痴态。这江南至味,原是要守着炭火候两个时辰的。袁枚所谓“素宜白水,荤用肥猪”,实在通透——咸肉吊鲜,鲜笋提清,火腿骨增厚,三味相激,倒应了《中庸》“致中和”的玄机。
暮色漫进厨房时,我舀勺笋汤浇在粳米饭上。蒸腾的热气里,父亲当年在煤炉边煨萝卜的身影忽然清晰起来。他那柄包浆油亮的铁勺在砂锅沿轻叩,叮当声混着“春吃芽夏吃瓜”的俚语,和窗外的雨押着同样的韵脚。
布里亚·萨瓦兰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怎样的人”。春日案头的青蔬,何尝不是本无字书?枸杞头微苦回甘,恰似少年时不解的严训;马兰头拌香干清冽,倒像中年偶得的闲适;至于香椿那霸道的异香,非要经滚油驯化方显本真,倒暗合了人生况味。
灶上铜吊子咕嘟作响,新摘的草头在沸水里打了个转便捞起。拌上蒜末姜汁,青碧间杂雪白,竟似把整个春天的清气都盛在了青花碟里。忽然明白《吕氏春秋》为何将“菜之美者”归于昆仑之苹,这草木初萌的鲜嫩,原是造化最慷慨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