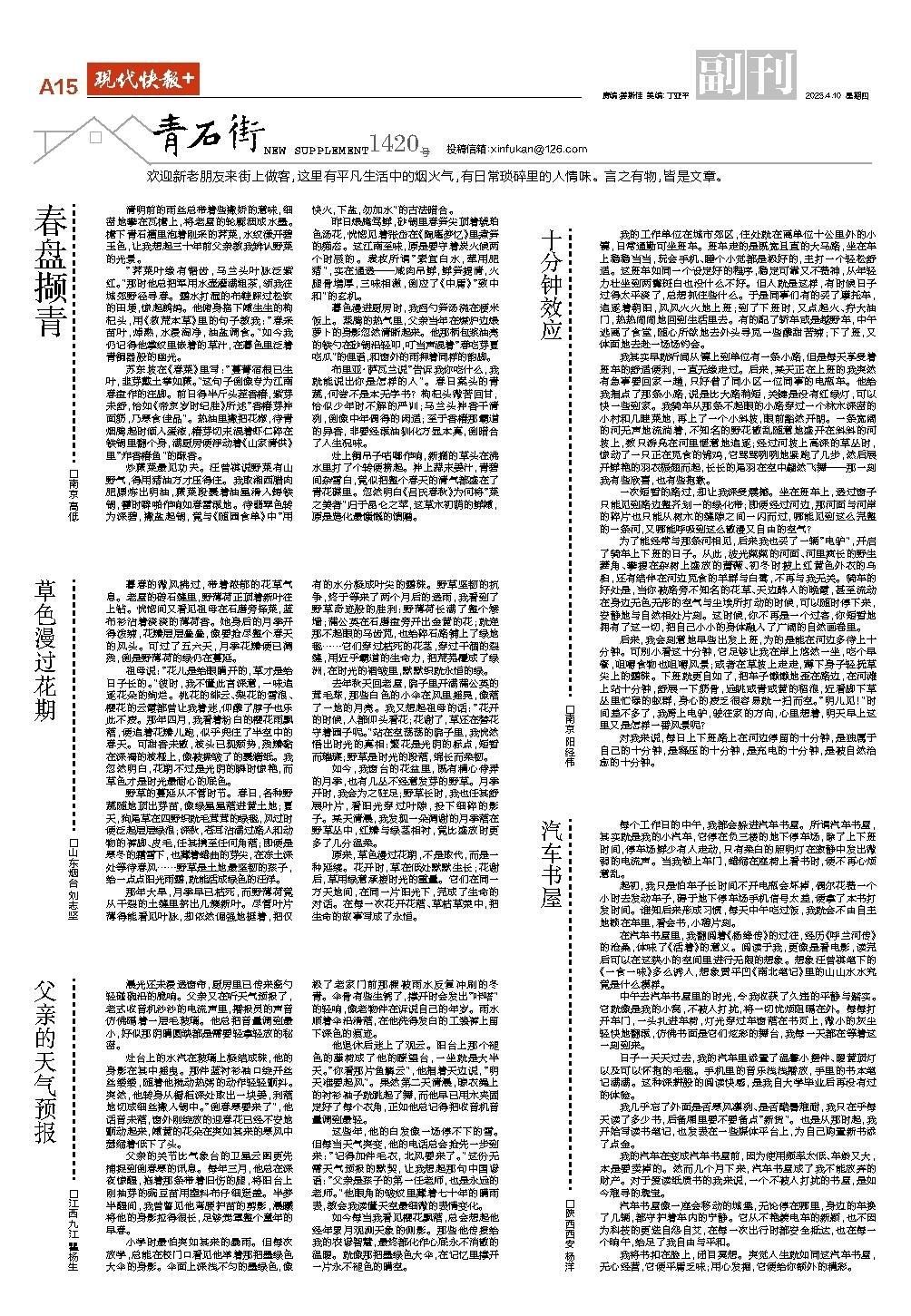□江西九江 瞿杨生
晨光还未浸透窗帘,厨房里已传来瓷勺轻碰碗沿的脆响。父亲又在听天气预报了,老式收音机沙沙的电流声里,播报员的声音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他总把音量调到最小,好似那阴晴圆缺都是需要轻拿轻放的秘密。
灶台上的水汽在玻璃上凝结成珠,他的身影在其中摇曳。那件蓝衬衫袖口绽开丝丝缕缕,随着他搅动热粥的动作轻轻颤抖。突然,他转身从橱柜深处取出一块姜,利落地切成细丝撒入锅中。“倒春寒要来了”,他话音未落,窗外刚绽放的迎春花已经不安地颤动起来,嫩黄的花朵在突如其来的寒风中瑟缩着低下了头。
父亲的关节比气象台的卫星云图更先捕捉到倒春寒的讯息。每年三月,他总在深夜惊醒,拖着那条带着旧伤的腿,将阳台上刚抽芽的豌豆苗用塑料布仔细遮盖。半梦半醒间,我曾瞥见他弯腰护苗的剪影,晨曦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足够笼罩整个童年的早春。
小学时最怕突如其来的暴雨。但每次放学,总能在校门口看见他举着那把墨绿色大伞的身影。伞面上深浅不匀的墨绿色,像极了老家门前那棵被雨水反复冲刷的冬青。伞骨有些生锈了,撑开时会发出“咔嗒”的轻响,像老物件在诉说自己的年岁。雨水顺着伞沿滑落,在他洗得发白的工装裤上留下深色的痕迹。
他退休后迷上了观云。阳台上那个褪色的藤椅成了他的瞭望台,一坐就是大半天。“你看那片鱼鳞云”,他指着天边说,“明天准要起风”。果然第二天清晨,晾衣绳上的衬衫袖子就跳起了舞,而他早已用木夹固定好了每个衣角,正如他总记得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轻。
这些年,他的白发像一场停不下的雪。但每当天气突变,他的电话总会抢先一步到来:“记得加件毛衣,北风要来了。”这份无需天气预报的默契,让我想起那句中国谚语:“父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永远的老师。”他眼角的皱纹里藏着七十年的晴雨表,教会我读懂天空最细微的表情变化。
如今每当我看见樱花飘落,总会想起他经年累月观测天象的侧影。那些他传授给我的农谚智慧,最终都化作心底永不消散的温暖。就像那把墨绿色大伞,在记忆里撑开一片永不褪色的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