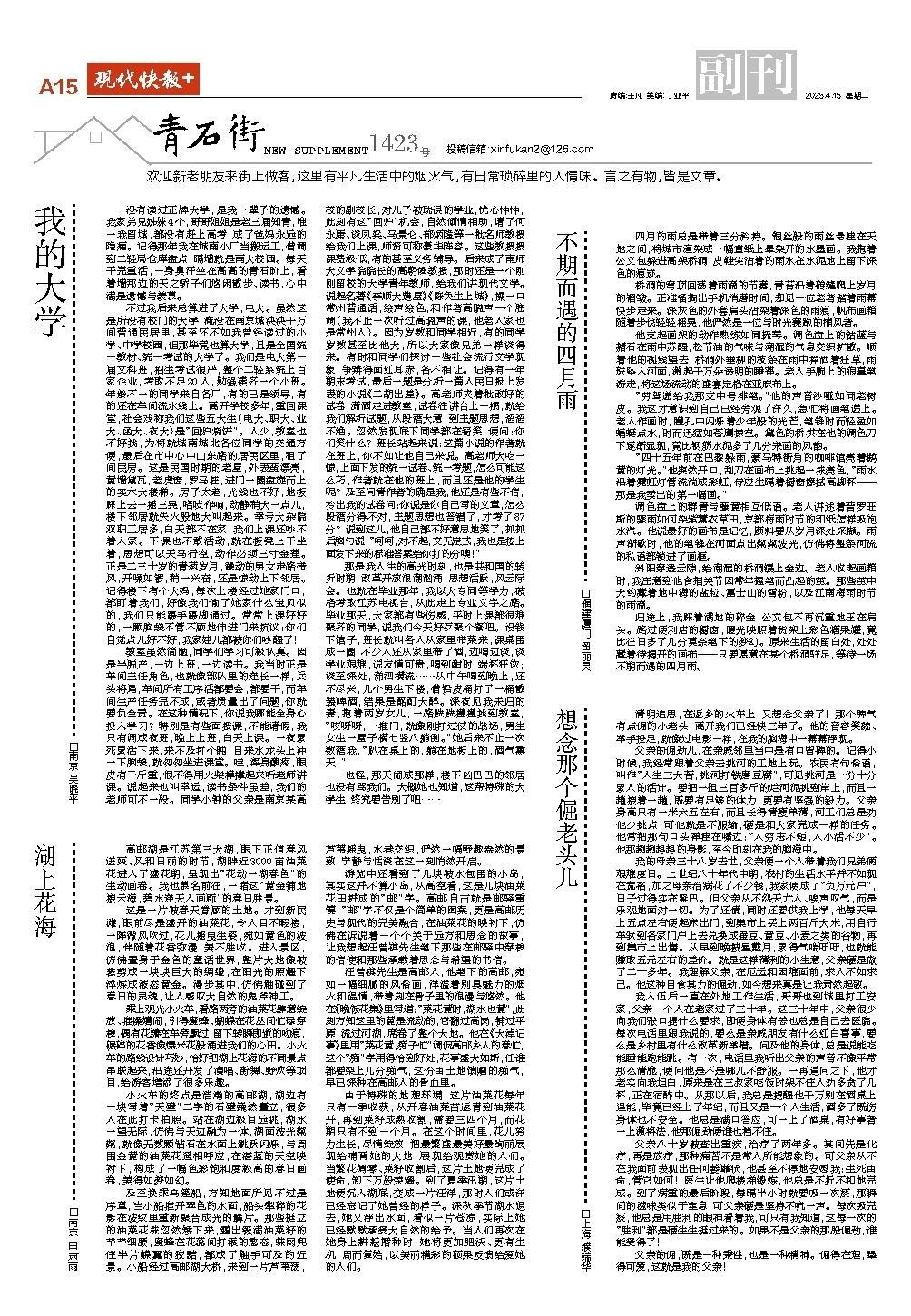□南京 吴晓平
没有读过正牌大学,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家弟兄姊妹4个,哥哥姐姐是老三届知青,唯一我留城,都没有赶上高考,成了爸妈永远的隐痛。记得那年我在城南小厂当搬运工,借调到二轻局仓库盘点,隔墙就是南大校园。每天干完重活,一身臭汗坐在高高的青石阶上,看着墙那边的天之骄子们悠闲散步、读书,心中满是遗憾与羡慕。
不过我后来总算进了大学,电大。虽然这是所没有校门的大学,淹没在南京城泱泱千万间普通民居里,甚至还不如我曾经读过的小学、中学校园,但那毕竟也算大学,且是全国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的大学了。我们是电大第一届文科班,招生考试很严,整个二轻系统上百家企业,考取不足20人,勉强凑齐一个小班。年龄不一的同学来自各厂,有的已是领导,有的还在车间流水线上。离开学校多年,重回课堂,社会戏称我们这些五大生(电大、职大、业大、函大、夜大)是“回炉烧饼”。人少,教室也不好找,为将就城南城北各位同学的交通方便,最后在市中心中山东路的居民区里,租了间民房。这是民国时期的老屋,外表蛮漂亮,黄墙黛瓦,老虎窗,罗马柱,进门一圈盘旋而上的实木大楼梯。房子太老,光线也不好,地板踩上去一摇三晃,咯吱作响,动静稍大一点儿,楼下邻居就失火般地大叫起来。幸亏大杂院双职工居多,白天都不在家,我们上课还吵不着人家。下课也不敢活动,就在板凳上干坐着,思想可以天马行空,动作必须三寸金莲。正是二三十岁的青葱岁月,躁动的男女走路带风,开嗓如锣,稍一兴奋,还是惊动上下邻居。记得楼下有个大妈,每次上楼经过她家门口,都盯着我们,好像我们偷了她家什么宝贝似的,我们只能蹑手蹑脚通过。常常上课好好的,一颗脑袋不管不顾地伸进门来抗议:你们自觉点儿好不好,我家娃儿都被你们吵醒了!
教室虽然简陋,同学们学习可极认真。因是半脱产,一边上班,一边读书。我当时正是车间主任角色,也就像部队里的连长一样,兵头将尾,车间所有工序活都要会,都要干,而车间生产任务完不成,或者质量出了问题,你就要负全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哪能全身心投入学习?特别是有些面授课,不能请假,我只有调成夜班,晚上上班,白天上课。一夜累死累活下来,来不及打个盹,自来水龙头上冲一下脑袋,就匆匆坐进课堂。哇,浑身酸疼,眼皮有千斤重,恨不得用火柴棒撑起来听老师讲课。说起来也叫幸运,读书条件虽差,我们的老师可不一般。同学小钟的父亲是南京某高校的副校长,对儿子被耽误的学业,忧心忡忡,此刻有这“回炉”机会,自然倾情相助,请了何永康、谈凤梁、马景仑、郁炳隆等一批名师教授给我们上课,师资可称豪华阵容。这些教授授课费极低,有的甚至义务辅导。后来成了南师大文学院院长的高朝俊教授,那时还是一个刚刚留校的大学青年教师,给我们讲现代文学。说起名著《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操一口常州普通话,绘声绘色,和作者高晓声一个腔调(我不止一次听过高晓声的课,他老人家也是常州人)。因为岁数和同学相近,有的同学岁数甚至比他大,所以大家像兄弟一样谈得来。有时和同学们探讨一些社会流行文学现象,争辩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记得有一年期末考试,最后一题是分析一篇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小说《二胡出差》。高老师夹着批改好的试卷,潇洒走进教室,试卷往讲台上一掼,就给我们解析试题,从段落大意,到主题思想,滔滔不绝。忽然发现底下同学都在窃笑,便问:你们笑什么?班长站起来说:这篇小说的作者就在班上,你不如让他自己来说。高老师大吃一惊,上面下发的统一试卷、统一考题,怎么可能这么巧,作者就在他的班上,而且还是他的学生呢?及至问清作者的确是我,他还是有些不信,拎出我的试卷问:你说是你自己写的文章,怎么段落分得不对,主题思想也答错了,才考了87分?说到这儿,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了,抓抓后脑勺说:“呵呵,对不起,文无定式,我也是按上面发下来的标准答案给你打的分噢!”
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共和国的转折时期,改革开放浪潮汹涌,思想活跃,风云际会。也就在毕业那年,我以大专同等学力,破格考取江苏电视台,从此走上专业文字之路。毕业那天,大家都有些伤感,平时上课都很难聚齐的同学,说我们今天好歹聚个餐吧。没钱下馆子,班长就叫各人从家里带菜来,课桌围成一圈,不少人还从家里带了酒,边喝边谈,谈学业艰难,说友情可贵,喝到酣时,端杯狂饮;谈至深处,涕泗横流……从中午喝到晚上,还不尽兴,几个男生下楼,借铅皮桶打了一桶散装啤酒,结果是酩酊大醉。深夜见我未归的妻,抱着两岁女儿,一路跌跌撞撞找到教室,“哎呀呀,一推门,就像刚打过仗的战场,男生女生一屋子横七竖八躺倒。”她后来不止一次数落我,“趴在桌上的,躺在地板上的,酒气熏天!”
也怪,那天闹成那样,楼下凶巴巴的邻居也没有骂我们。大概她也知道,这帮特殊的大学生,终究要告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