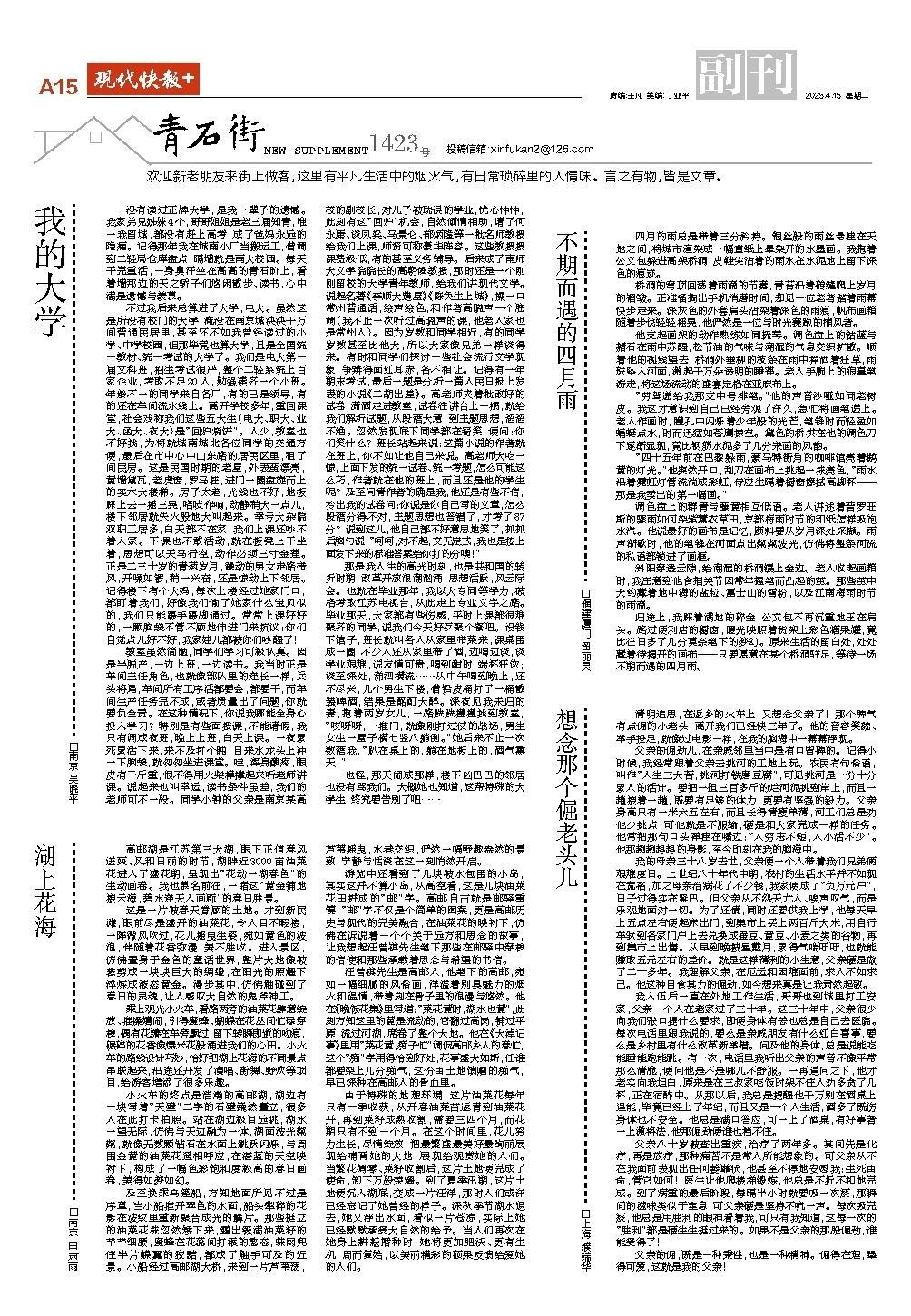□福建厦门 留丽灵
四月的雨总是带着三分矜持。银丝般的雨丝悬挂在天地之间,将城市渲染成一幅宣纸上晕染开的水墨画。我抱着公文包躲进高架桥洞,皮鞋尖沾着的雨水在水泥地上留下深色的痕迹。
桥洞的穹顶回荡着雨滴的节奏,青苔沿着砖缝爬上岁月的褶皱。正准备掏出手机消磨时间,却见一位老者踏着雨幕快步走来。深灰色的外套肩头沾染着深色的雨痕,帆布画箱随着步伐轻轻摇晃,他俨然是一位与时光赛跑的捕风者。
他支起画架的动作熟练如同抚琴。调色盘上的钴蓝与赭石在雨中苏醒,松节油的气味与潮湿的气息交织扩散。顺着他的视线望去,桥洞外垂柳的枝条在雨中挥洒着狂草,雨珠坠入河面,激起千万朵透明的睡莲。老人手腕上的狼毫笔游走,将这场流动的盛宴定格在亚麻布上。
“劳驾递给我那支中号排笔。”他的声音沙哑如同老树皮。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旁观了许久,急忙将画笔递上。老人作画时,瞳孔中闪烁着少年般的光芒,笔锋时而轻盈如蜻蜓点水,时而迅猛如苍鹰掠空。黛色的桥拱在他的调色刀下逐渐显现,竟比钢筋水泥多了几分宋画的风韵。
“四十五年前在巴黎躲雨,蒙马特街角的咖啡馆亮着鹅黄的灯光。”他突然开口,刮刀在画布上挑起一抹亮色,“雨水沿着霓虹灯管流淌成彩虹,侍应生隔着橱窗擦拭高脚杯——那是我卖出的第一幅画。”
调色盘上的群青与藤黄相互低语。老人讲述着普罗旺斯的骤雨如何染紫薰衣草田,京都梅雨时节的和纸怎样吸饱水汽。他说最好的画布是记忆,颜料要从岁月深处采撷。雨声渐歇时,他的笔锋在河面点出粼粼波光,仿佛将整条河流的私语都锁进了画框。
斜阳穿透云隙,给潮湿的桥洞镶上金边。老人收起画箱时,我注意到他食指关节因常年握笔而凸起的茧。那些茧中大约藏着地中海的盐粒、富士山的雪粉,以及江南梅雨时节的雨滴。
归途上,我踩着满地的碎金,公文包不再沉重地压在肩头。路过便利店的橱窗,暖光映照着货架上彩色糖果罐,竟比往日多了几分莫奈笔下的梦幻。原来生活的留白处,处处藏着待揭开的画布——只要愿意在某个桥洞驻足,等待一场不期而遇的四月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