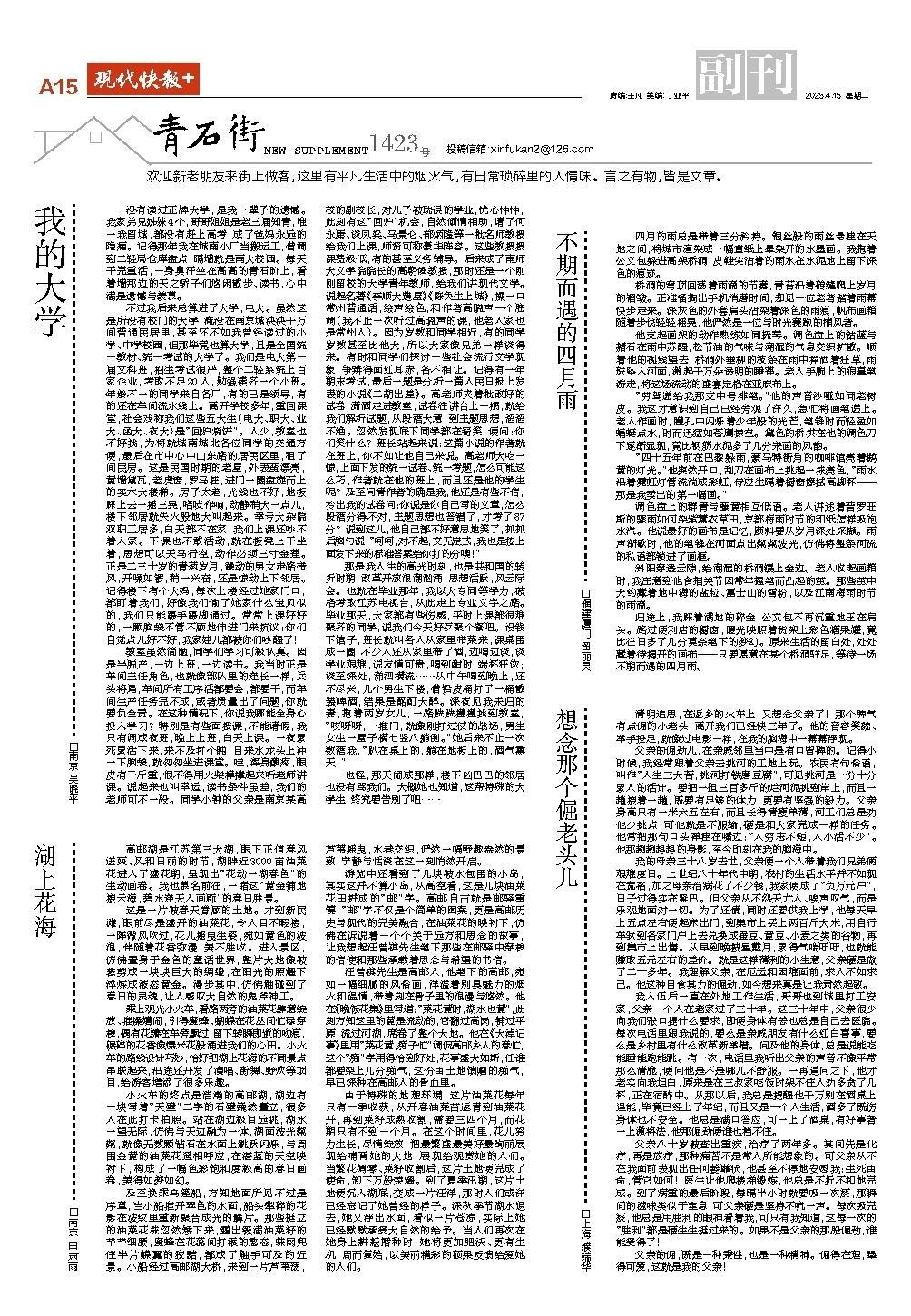□上海 濮端华
清明追思,在返乡的火车上,又想念父亲了!那个脾气有点倔的小老头,离开我们已经快三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父亲的倔劲儿,在亲戚邻里当中是有口皆碑的。记得小时候,我经常跟着父亲去挑河的工地上玩。农民有句俗语,叫作“人生三大苦,挑河打铁磨豆腐”,可见挑河是一份十分累人的活计。要把一担三百多斤的烂河泥挑到岸上,而且一趟接着一趟,既要有足够的体力,更要有坚强的毅力。父亲身高只有一米六五左右,而且长得清瘦单薄,河工们总是劝他少挑点,可他就是不服输,硬是和大家完成一样的任务。他常把那句口头禅挂在嘴边:“人穷志不短,人小活不少”。他那趔趔趄趄的身影,至今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母亲三十八岁去世,父亲便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弟俩艰难度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生活水平并不如现在宽裕,加之母亲治病花了不少钱,我家便成了“负万元户”,日子过得实在紧巴。但父亲从不怨天尤人、唉声叹气,而是乐观地面对一切。为了还债,同时还要供我上学,他每天早上五点左右便起床出门,到集市上买上两百斤大米,用自行车驮到各家门户上去兑换成蚕豆、黄豆、小麦之类的谷物,再到集市上出售。从早到晚披星戴月,累得气喘吁吁,也就能赚取五元左右的差价。就是这样薄利的小生意,父亲硬是做了二十多年。我理解父亲,在厄运和困难面前,求人不如求己。他这种自食其力的倔劲,如今想来真是让我肃然起敬。
我入伍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生活,哥哥也到城里打工安家,父亲一个人在老家过了三十年。这三十年中,父亲很少向我们张口提什么要求,即便身体有恙也总是自己去医院。每次电话里跟我说的,要么是亲戚朋友有什么红白喜事,要么是乡村里有什么改革新举措。问及他的身体,总是说能吃能睡能跑能跳。有一次,电话里我听出父亲的声音不像平常那么清脆,便问他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一再逼问之下,他才老实向我坦白,原来是在三叔家吃饭时架不住人劝多贪了几杯,正在宿醉中。从那以后,我总是提醒他千万别在酒桌上逞能,毕竟已经上了年纪,而且又是一个人生活,酒多了既伤身体也不安全。他总是满口答应,可一上了酒桌,有好事者一上激将法,他那倔劲便谁也挡不住。
父亲八十岁被查出重疾,治疗了两年多。其间先是化疗,再是放疗,那种痛苦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可父亲从不在我面前表现出任何萎靡状,他甚至不停地安慰我:生死由命,管它如何!医生让他爬楼梯锻炼,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到了病重的最后阶段,每隔半小时就要吸一次痰,那瞬间的滋味类似于窒息,可父亲硬是坚持不吭一声。每次吸完痰,他总是用胜利的眼神看着我,可只有我知道,这每一次的“胜利”都是硬生生挺过来的。如果不是父亲的那股倔劲,谁能受得了!
父亲的倔,既是一种秉性,也是一种精神。倔得在理,犟得可爱,这就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