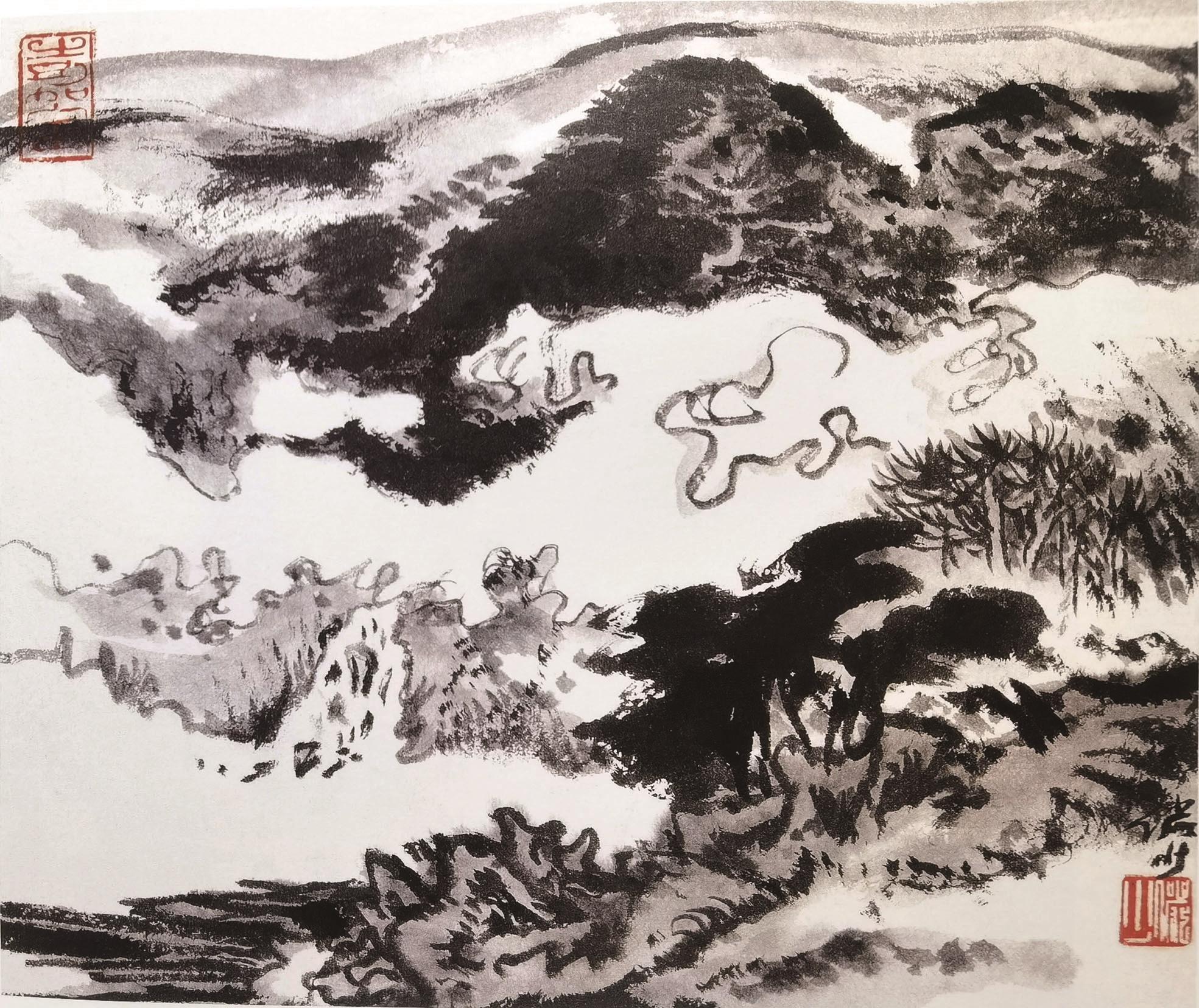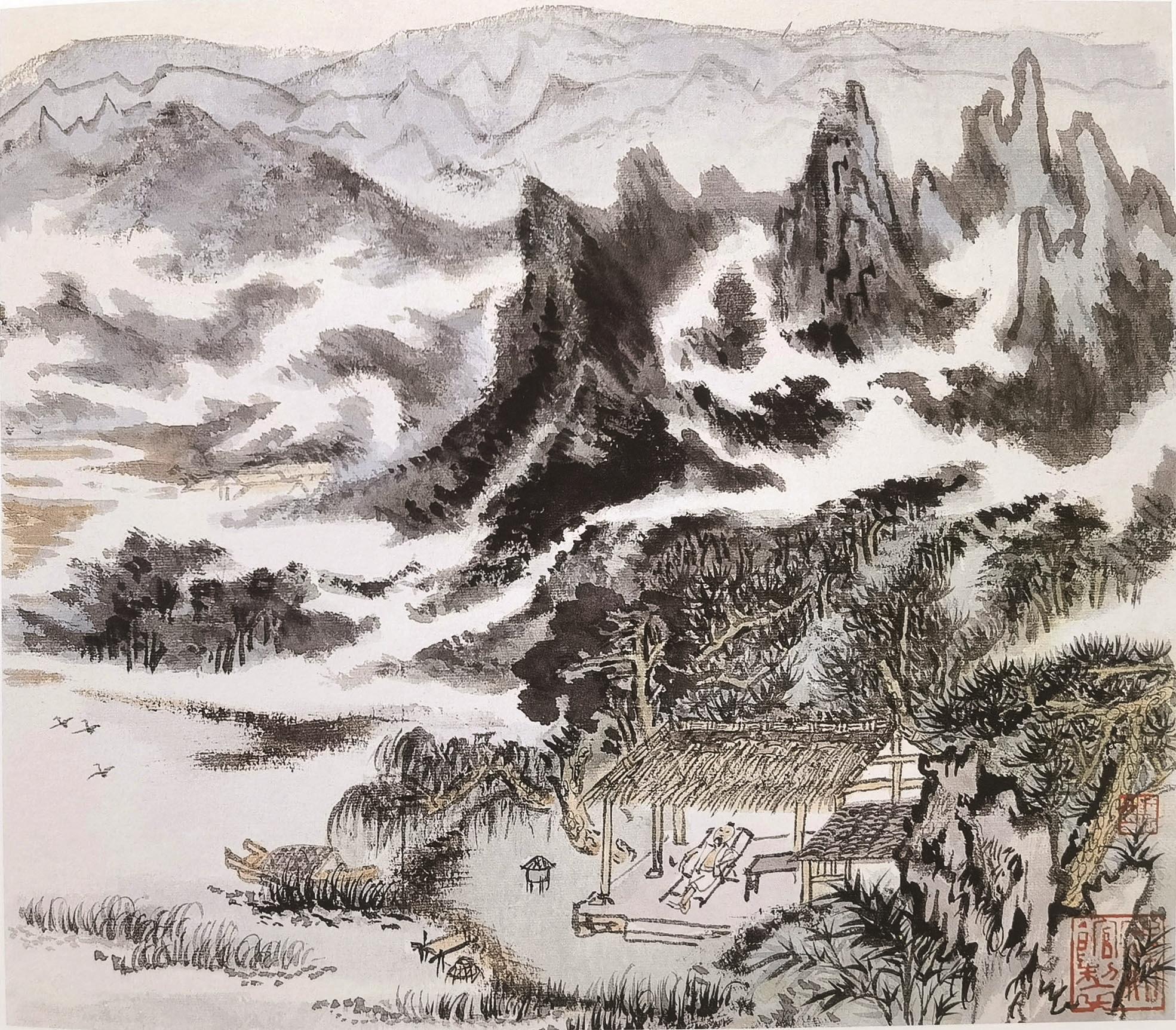□萧平
以王翚比陆俨少,是因为他们对于传统的共同点,前者是三百年前的集大成者。然而笔者以为,陆又不同于王,且远过于王。王翚早年得王鑑、王时敏指点,后又应召去北京数年,看到许多历代名迹,并一一临摹,这就造就了他摹古精到逼肖的才能,后人也因此得以一睹赖其笔墨才保存的前贤风貌。他以此为本线,提出“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的大成计划。而其晚年定型的套式画风,却反映其“大综合”计划并不成功。陆俨少早年囿于老师,所临“四王”一类真迹亦有限,南京画展中的古画名迹才使其“暴富”起来。他传统的财富主要是看、读来的,所以存之于胸的是精华和大意,汰去了次要的细节;他的这些财富,又不断地用于创作实践,在实践中得以巩固和发展。他禀性倔强刚直,他的“自我”便会在对于传统的应用中顽强地显露出来。换言之,他在虔心传统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强烈的“自我”。对于传统,他“入”得有性格,“出”时就自然潇洒得多了。这个基础,导致了他最终步入前无古人的艺术境界。
对于传统的汲取,俨少先生提出“识辨”二字,他说:“识辨对于学画,至关重要,即对包括古人和今人的作品,要有正确的见解,即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这样才能吸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又说:“人的禀赋不一,何者是自己的所长,何者是自己的所短,明乎此,那么以我所短,学他的所长,永远不能胜过他,永远跟在他后面。只有用我所长,那么可以胜过他。”(《学画微言》)俨少先生讲了主客两个方面,即对传统和自己都要进行分析,也就是识辨。人们往往只注意其一而忽视了其二,殊不知这正是陆氏最终开辟自己道路的关键。他在总结自己经验时举例:他青年时期,吴湖帆山水画已名重一时,吴画妙在有一种明丽婉约的词境。而他禀赋刚健木强,近乎沉郁的杜甫诗风,二者禀性不近,同能不如独诣,故自辟蹊径,使吴画不能笼罩他。六十年代之前吴湖帆曾以自己的斋名为题,请他画一大青绿,他有意避开吴氏青绿法,吸取敦煌及唐画勾线,并参以赵孟頫、钱选两家之法而成。刘海粟见了,十分赏识,说可作宋画看。
陆氏的“识辨”,还表现在对前贤理论的解析和批评,如对“六法”中“气韵生动”的解释:“中国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似乃具象,不似为抽象。一图之中除去具象之外,其余皆在抽象范围之内,生动而后气韵生焉。”(《论画七则》)后来,他又有了新的说法:“气韵生动,历来不易说明白,我想用‘灵变’两字来解释,虽不完全适当,但也虽不中,不远矣。”(《学画微言》)“气韵生动”是中国历来品评绘画的最高标准,俨少先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用心,可见他居高临下,把握大局的思路。再如,他针对董其昌著名的“南北宗论”说:“不必斤斤于南北宗之论,而受其限制。土山石山,皆在表现对象范围之内,尽可因对象之不同,以斧劈披麻,加减穿插互用之。”南北分宗的观点,曾经困扰了几代画人,陆氏不仅在文字上,更在实践中揉合南北,穿插互用,不露痕迹地建立了自己的新面目。这一事实说明,他在传统的探索中,强调独立的思考而不受派别的限制。这也是他“集大成”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