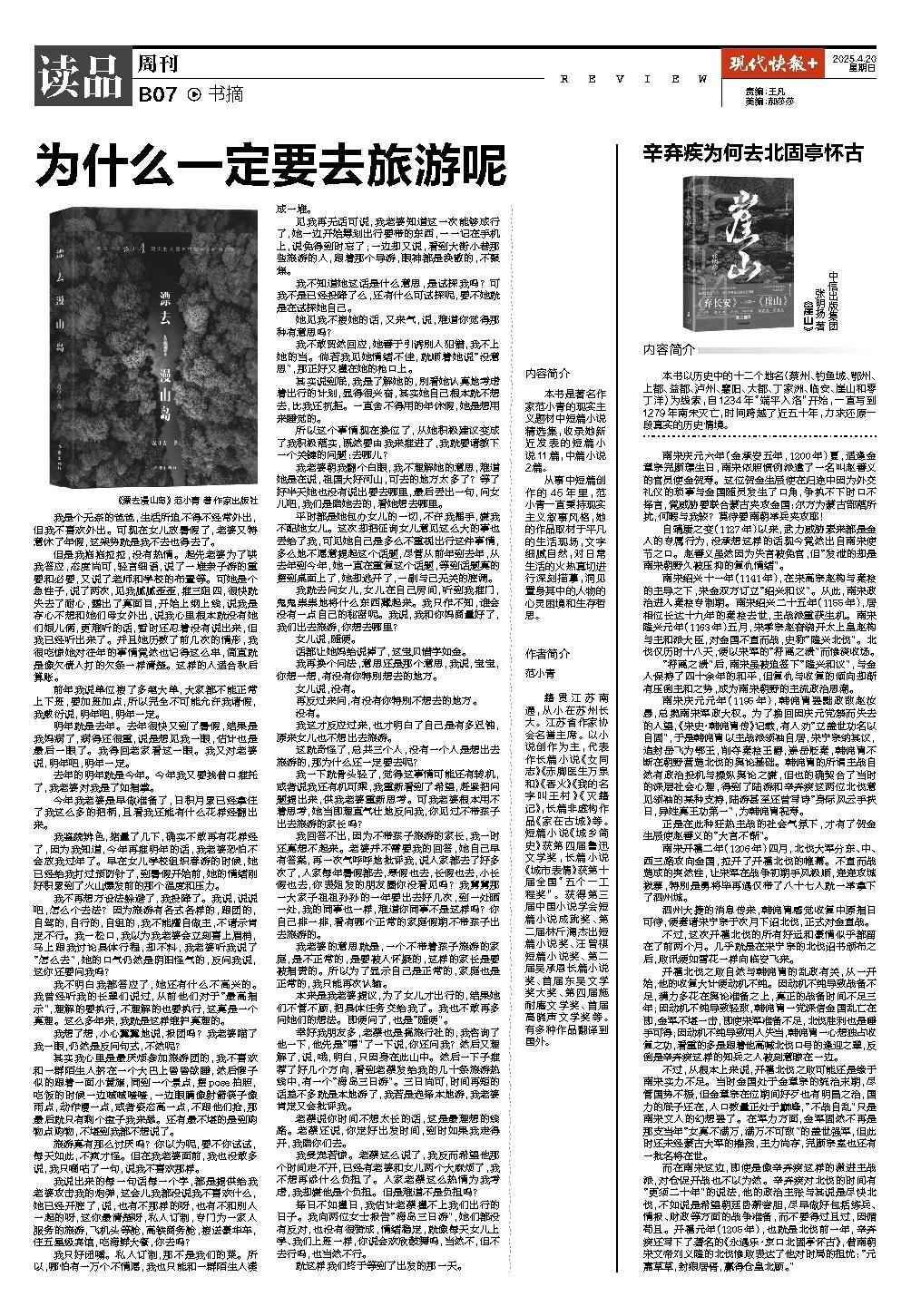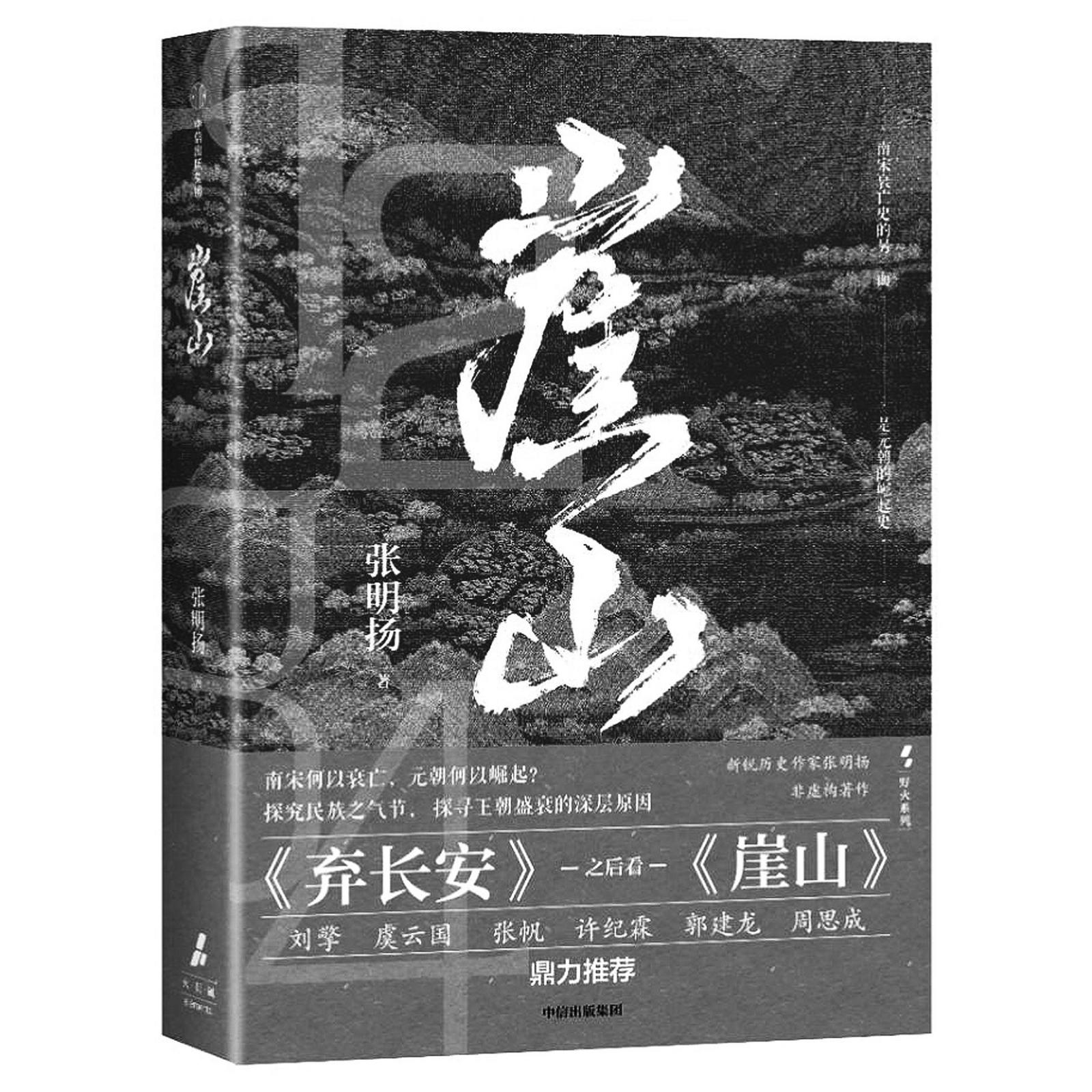内容简介
本书以历史中的十二个地名(蔡州、钓鱼城、鄂州、上都、益都、泸州、襄阳、大都、丁家洲、临安、崖山和零丁洋)为线索,自1234年“端平入洛”开始,一直写到1279年南宋灭亡,时间跨越了近五十年,力求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情境。
南宋庆元六年(金承安五年,1200年)夏,适逢金章宗完颜璟生日,南宋依照惯例派遣了一名叫赵善义的官员使金贺寿。这位贺金生辰使在归途中因为外交礼仪的琐事与金国随员发生了口角,争执不下时口不择言,竟威胁要联合蒙古夹攻金国:尔方为蒙古部落所扰,何暇与我较?莫待要南朝举兵夹攻耶!
自靖康之变(1127年)以来,武力威胁素来都是金人的专属行为,没承想这样的话现今竟然出自南宋使节之口。赵善义虽然因为失言被免官,但“发泄的却是南宋朝野久被压抑的复仇情绪”。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在宋高宗赵构与秦桧的主导之下,宋金双方订立“绍兴和议”。从此,南宋政治进入秦桧专制期。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居相位长达十九年的秦桧去世,主战派重获生机。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宋孝宗赵昚绕开太上皇赵构与主和派大臣,对金国不宣而战,史称“隆兴北伐”。北伐仅历时十八天,便以宋军的“符离之溃”而惨淡收场。
“符离之溃”后,南宋虽被迫签下“隆兴和议”,与金人保持了四十余年的和平,但复仇与收复的倾向却渐有压倒主和之势,成为南宋朝野的主流政治思潮。
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韩侂胄罢黜政敌赵汝愚,总揽南宋军政大权。为了挽回因庆元党禁而失去的人望,《宋史·韩侂胄传》记载,有人劝“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于是韩侂胄以主战派领袖自居,宋宁宗纳其议,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夺秦桧王爵,崇岳贬秦,韩侂胄不断在朝野营造北伐的舆论基础。韩侂胄的所谓主战自然有政治投机与操纵舆论之嫌,但也的确契合了当时的深层社会心理,得到了陆游和辛弃疾这两位北伐意见领袖的某种支持,陆游甚至还曾写诗“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为韩侂胄祝寿。
正是在此种狂热主战的社会气氛下,才有了贺金生辰使赵善义的“大言不惭”。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北伐大军分东、中、西三路攻向金国,拉开了开禧北伐的帷幕。不宣而战造成的突然性,让宋军在战争初期手风极顺,连连攻城拔寨,特别是勇将毕再遇仅带了八十七人就一举拿下了泗州城。
泗州大捷的消息传来,韩侂胄感觉收复中原指日可待,便奏请宋宁宗于次月下诏北伐,正式对金宣战。
不过,这次开禧北伐的所有好运和豪情似乎都留在了前两个月。几乎就是在宋宁宗的北伐诏书颁布之后,败讯便如雪花一样向临安飞来。
开禧北伐之败自然与韩侂胄的乱政有关,从一开始,他的收复大计便动机不纯。因动机不纯导致战备不足,精力多花在舆论准备之上,真正的战备时间不足三年;因动机不纯导致轻敌,韩侂胄一党深信金国乱亡在即,金军不堪一击,即使宋军准备不足,北伐胜利也是唾手可得;因动机不纯导致用人失当,韩侂胄一心想独占收复之功,看重的多是跟着他高喊北伐口号的逢迎之辈,反倒是辛弃疾这样的知兵之人被刻意晾在一边。
不过,从根本上来说,开禧北伐之败可能还是缘于南宋实力不足。当时金国处于金章宗的统治末期,尽管国势不振,但金章宗在位期间好歹也有明昌之治,国力的底子还在,人口数量正处于巅峰,“不战自乱”只是南宋文人的幻想罢了。在军力方面,金军固然不再是那支当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盖世强军,但此时还未经蒙古大军的摧残,主力尚存,完颜宗室也还有一批名将在世。
而在南宋这边,即使是像辛弃疾这样的激进主战派,对仓促开战也不以为然。辛弃疾对北伐的时间有“更须二十年”的说法,他的政治主张与其说是尽快北伐,不如说是希望朝廷卧薪尝胆,尽早做好包括练兵、情报、财政等方面的战争准备,而不要得过且过,因循苟且。开禧元年(1205年),也就是北伐前一年,辛弃疾还写下了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借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北伐惨败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担忧:“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