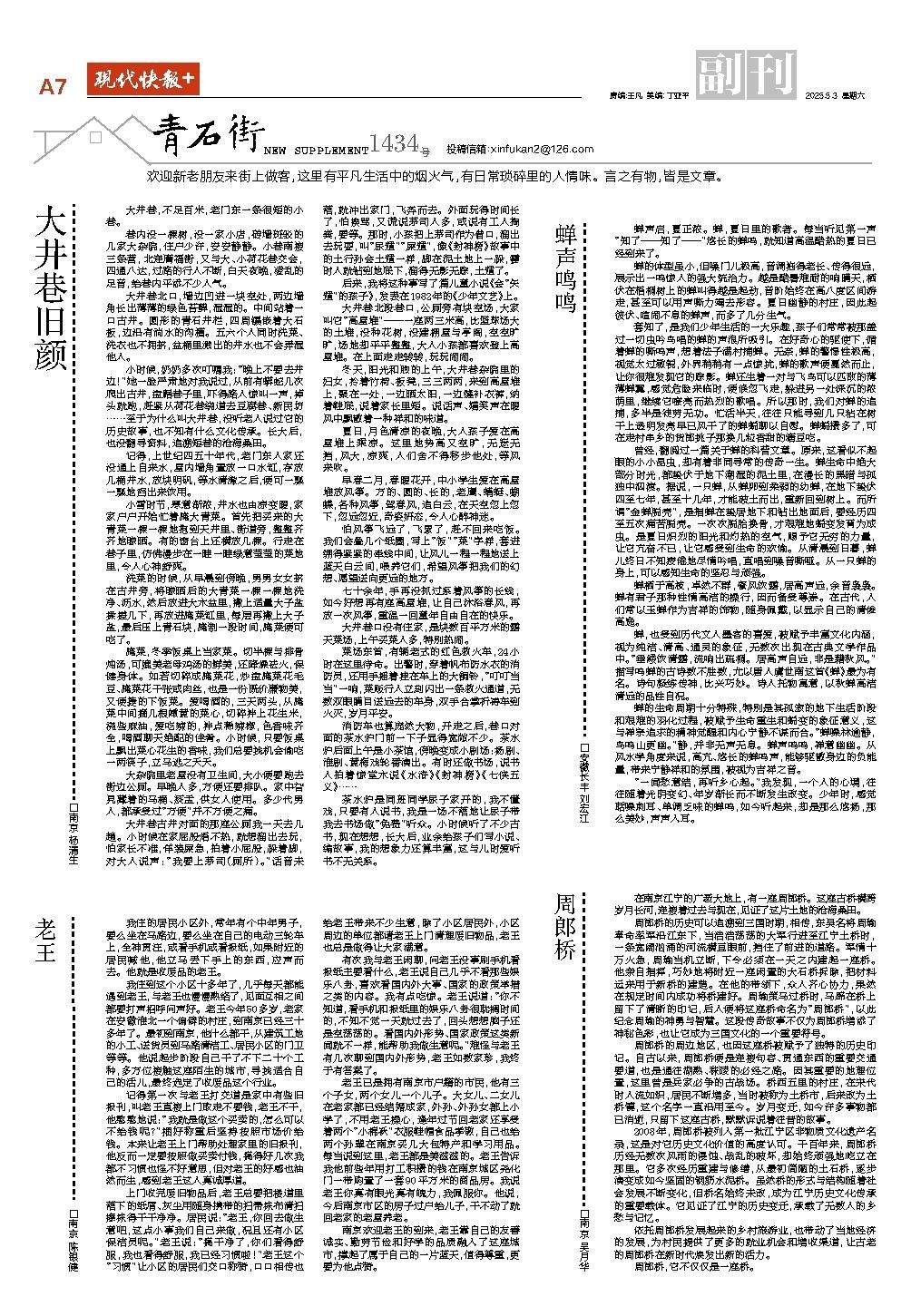□南京 杨清生
大井巷,不足百米,老门东一条很短的小巷。
巷内没一棵树,没一家小店,砖墙斑驳的几家大杂院,住户少许,安安静静。小巷南接三条营,北连膺福街,又与大、小荷花巷交会,四通八达,过路的行人不断,白天夜晚,凌乱的足音,给巷内平添不少人气。
大井巷北口,墙边凹进一块空处,两边墙角长出薄薄的绿色苔藓,湿湿的。中间站着一口古井。圆形的青石井栏,四周镶嵌着大石板,边沿有淌水的沟槽。五六个人同时洗菜、洗衣也不拥挤,盆桶里溅出的井水也不会弄湿他人。
小时候,奶奶多次叮嘱我:“晚上不要去井边!”她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过,从前有蟒蛇几次爬出古井,盘踞巷子里,吓得路人惊叫一声,掉头就跑,赶紧从荷花巷绕道去豆腐巷、新民坊……至于为什么叫大井巷,没听老人说过它的历史故事,也不知有什么文化传承。长大后,也没翻寻资料,追溯短巷的沧海桑田。
记得,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老门东人家还没通上自来水,屋内墙角置放一口水缸,存放几桶井水,放块明矾,等水清澈之后,便可一瓢一瓢地舀出来饮用。
小雪时节,寒意渐浓,井水也由凉变暖,家家户户开始忙着腌大青菜。首先把买来的大青菜一棵一棵地抱到天井里、街道旁,整整齐齐地晾晒。有的窗台上还横放几棵。行走在巷子里,仿佛漫步在一畦一畦绿意莹莹的菜地里,令人心神舒爽。
洗菜的时候,从早晨到傍晚,男男女女挤在古井旁,将晾晒后的大青菜一棵一棵地洗净、沥水,然后放进大木盆里,撒上适量大子盐揉搓几下,再放进腌菜缸里,每层再撒上大子盐,最后压上青石块,腌制一段时间,腌菜便可吃了。
腌菜,冬季饭桌上当家菜。切半棵与排骨炖汤,可媲美老母鸡汤的鲜美,还降燥祛火,保健身体。如若切碎成腌菜花,炒盘腌菜花毛豆、腌菜花千张或肉丝,也是一份既价廉物美,又便捷的下饭菜。爱喝酒的,三天两头,从腌菜中间摘几根嫩黄的菜心,切碎拌上花生米,浇些麻油,爱吃辣的,拌点稀辣椒,色香味齐全,喝酒聊天绝配的佳肴。小时候,只要饭桌上飘出菜心花生的香味,我们总要找机会偷吃一两筷子,立马逃之夭夭。
大杂院里老屋没有卫生间,大小便要跑去街边公厕。早晚人多,方便还要排队。家中旮旯藏着的马桶、痰盂,供女人使用。多少代男人,都承受过“方便”并不方便之痛。
大井巷古井对面的那座公厕我一天去几趟。小时候在家屁股焐不热,就想溜出去玩,怕家长不准,佯装屎急,拍着小屁股,跺着脚,对大人说声:“我要上茅司(厕所)。”话音未落,就冲出家门,飞奔而去。外面玩得时间长了,怕挨骂,又谎说茅司人多,或说有工人掏粪,要等。那时,小孩把上茅司作为借口,溜出去玩耍,叫“尿遁”“屎遁”,像《封神榜》故事中的土行孙会土遁一样,脚在泥土地上一跺,霎时人就钻到地底下,溜得无影无踪,土遁了。
后来,我将这种事写了篇儿童小说《会“矢遁”的孩子》,发表在1982年的《少年文艺》上。
大井巷北段巷口,公厕旁有块空场,大家叫它“高屋堆”——一座两三米高,比篮球场大的土堆,没种花树,没建棚屋与亭阁,空空旷旷,场地却平平整整,大人小孩都喜欢登上高屋堆。在上面走走转转,玩玩闹闹。
冬天,阳光和煦的上午,大井巷杂院里的妇女,拎着竹椅、板凳,三三两两,来到高屋堆上,聚在一处,一边晒太阳,一边缝补衣裤,纳着鞋底,说着家长里短。说话声、嬉笑声在暖风中飘散着一种祥和的味道。
夏日,月色清凉的夜晚,大人孩子爱在高屋堆上乘凉。这里地势高又空旷,无遮无挡,风大,凉爽,人们舍不得移步他处,等风来吹。
早春二月,春暖花开,中小学生爱在高屋堆放风筝。方的、圆的、长的,老鹰、蜻蜓、蝴蝶,各种风筝,驾春风,追白云,在天空忽上忽下,忽远忽近,奇姿妍态,令人心醉神迷。
怕风筝飞远了,飞累了,赶不回来吃饭。我们会叠几个纸圈,写上“饭”“菜”字样,套进绷得紧紧的牵线中间,让风儿一程一程地送上蓝天白云间,喂养它们,希望风筝把我们的幻想、愿望送向更远的地方。
七十余年,手再没抓过系着风筝的长线,如今好想再有座高屋堆,让自己沐浴春风,再放一次风筝,重温一回童年自由自在的快乐。
大井巷口没有住家,是块数百平方米的露天菜场,上午买菜人多,特别热闹。
菜场东首,有辆老式的红色救火车,24小时在这里待命。出警时,穿着帆布防水衣的消防员,还用手摇着挂在车上的大铜铃,“叮叮当当”一响,菜贩行人立刻闪出一条救火通道,无数双眼睛目送远去的车身,双手合掌祈祷车到火灭,岁月平安。
消防车也算庞然大物,开走之后,巷口对面的茶水炉门前一下子显得宽敞不少。茶水炉后面上午是小茶馆,傍晚变成小剧场:扬剧、淮剧、黄梅戏轮番演出。有时还做书场,说书人拍着惊堂木说《水浒》《封神榜》《七侠五义》……
茶水炉是同班同学尿子家开的,我不懂戏,只要有人说书,我是一场不落地让尿子带我去书场做“免费”听众。小时候听了不少古书,现在想想,长大后,业余给孩子们写小说、编故事,我的想象力还算丰富,这与儿时爱听书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