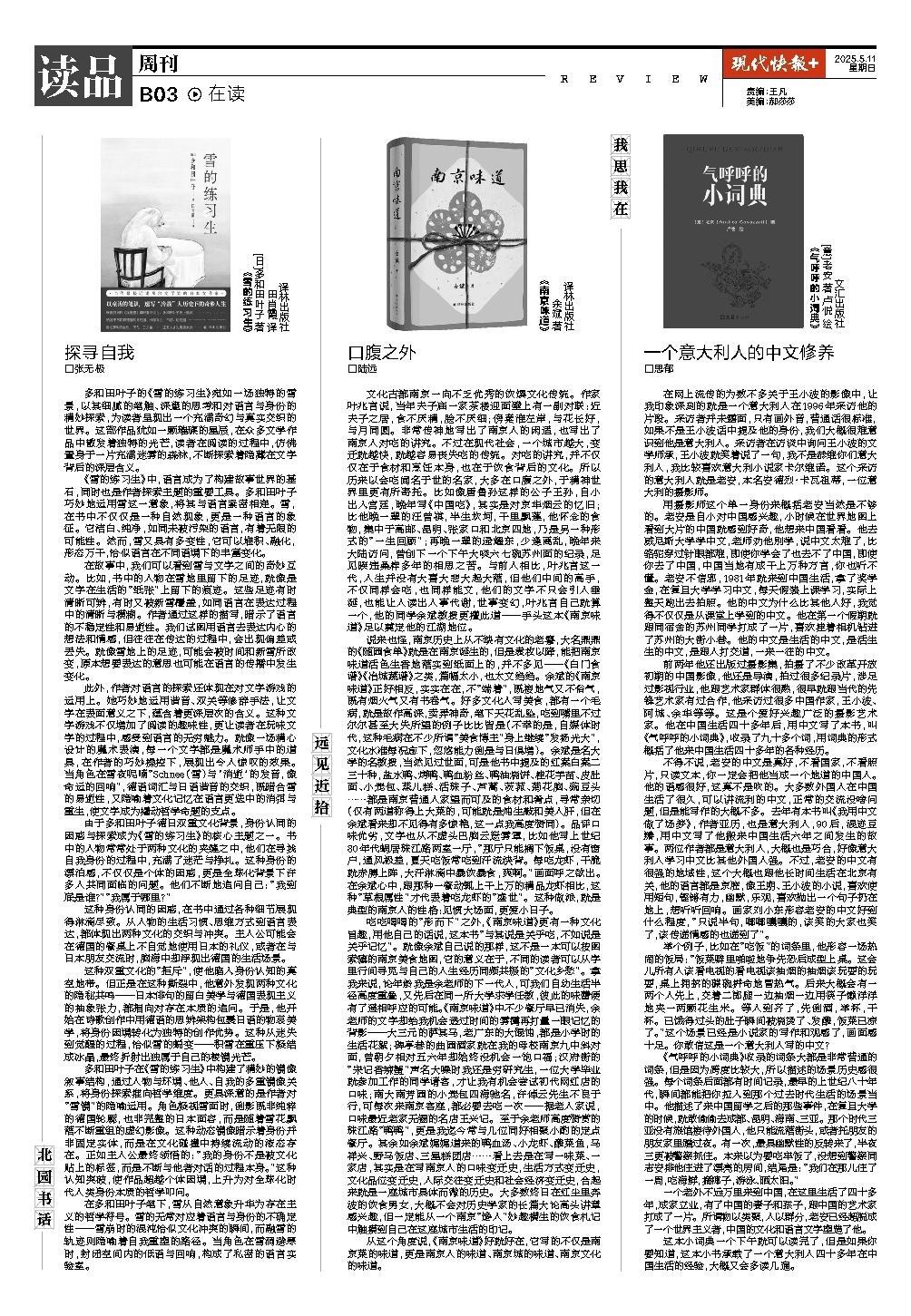□陆远
文化古都南京一向不乏优秀的饮馔文化传统。作家叶兆言说,当年夫子庙一家茶楼迎面壁上有一副对联: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同圆。非常传神地写出了南京人的闲适,也写出了南京人对吃的讲究。不过在现代社会,一个城市越大,变迁就越快,就越容易丧失吃的传统。对吃的讲究,并不仅仅在于食材和烹饪本身,也在于饮食背后的文化。所以历来以会吃闻名于世的名家,大多在口腹之外,于精神世界里更有所寄托。比如像唐鲁孙这样的公子王孙,自小出入宫廷,晚年写《中国吃》,其实是对京华烟云的忆旧;比他晚一辈的汪曾祺,半生坎坷,千里飘蓬,他怀念的食物,集中于高邮、昆明、张家口和北京四地,乃是另一种形式的“一生回顾”;再晚一辈的逯耀东,少逢离乱,晚年来大陆访问,曾创下一个下午大啖六七碗苏州面的纪录,足见暌违桑梓多年的相思之苦。与前人相比,叶兆言这一代,人生并没有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但他们中间的高手,不仅同样会吃,也同样能文,他们的文字不只会引人垂涎,也能让人读出人事代谢,世事变幻,叶兆言自己就算一个,他的同学余斌教授更擅此道——手头这本《南京味道》足以奠定他的江湖地位。
说来也怪,南京历史上从不缺有文化的老饕,大名鼎鼎的《随园食单》就是在南京诞生的,但是袁枚以降,能把南京味道活色生香地落实到纸面上的,并不多见——《白门食谱》《冶城蔬谱》之类,篇幅太小,也太文绉绉。余斌的《南京味道》正好相反,实实在在,不“端着”,既接地气又不俗气,既有烟火气又有书卷气。好多文化人写美食,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故作高深,卖弄神奇,笔下天花乱坠,吃到嘴里不过尔尔甚至大失所望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幸的是,自媒体时代,这种毛病在不少所谓“美食博主”身上继续“发扬光大”,文化水准每况愈下,忽悠能力倒是与日俱增)。余斌是名大学的名教授,当然见过世面,可是他书中提及的红案白案二三十种,盐水鸭、烤鸭、鸭血粉丝、鸭油烧饼、桂花芋苗、皮肚面、小笼包、蒸儿糕、活珠子、芦蒿、茨菰、菊花脑、豌豆头……都是南京普通人家望而可及的食材和肴点,寻常亲切(仅有两道称得上大菜的,可能就是炖生敲和美人肝,但在余斌看来却不见得有多惊艳,这一点我高度赞同)。品评口味优劣,文字也从不虚头巴脑云遮雾罩,比如他写上世纪80年代蜗居珠江路两室一厅,“那厅只能搁下饭桌,没有窗户,通风极差,夏天吃饭常吃到汗流浃背。每吃龙虾,干脆就赤膊上阵,大汗淋漓中暴饮暴食,爽啊。”画面呼之欲出。在余斌心中,跟那种一餐动辄上千上万的精品龙虾相比,这种“草根属性”才代表着吃龙虾的“盛世”。这种做派,就是典型的南京人的性格:见惯大场面,更爱小日子。
吃吃喝喝的“形而下”之外,《南京味道》更有一种文化旨趣,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与其说是关乎吃,不如说是关乎记忆”。就像余斌自己说的那样,这不是一本可以按图索骥的南京美食地图,它的意义在于,不同的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寻觅与自己的人生经历同频共振的“文化乡愁”。拿我来说,论年龄我是余老师的下一代人,可我们自幼生活半径高度重叠,又先后在同一所大学求学任教,彼此的味蕾便有了遥相呼应的可能。《南京味道》中不少餐厅早已消失,余老师的文字却给我机会透过时间的雾霭再打量一眼记忆的背影——大三元的萨其马,老广东的大馄饨,都是小学时的生活花絮;碑亭巷的曲园酒家就在我的母校南京九中斜对面,曾朝夕相对五六年却始终没机会一饱口福;汉府街的“宋记香辣蟹”声名大噪时我还是穷研究生,一位大学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同学请客,才让我有机会尝试初代网红店的口味;南大南芳园的小笼包四海驰名,许倬云先生不良于行,可每次来南京客座,都必要去吃一次——据老人家说,口味最近老家无锡的名店王兴记。至于余老师高度赞赏的珠江路“鸭鸭”,更是我迄今常与几位同好相聚小酌的定点餐厅。其余如余斌娓娓道来的鸭血汤、小龙虾、酸菜鱼,马祥兴、野马饭店、三星糕团店……看上去是在写一味菜、一家店,其实是在写南京人的口味变迁史,生活方式变迁史,文化品位变迁史,人际交往变迁史和社会经济变迁史,合起来就是一座城市具体而微的历史。大多数终日在红尘里奔波的饮食男女,大概不会对历史学家的长篇大论高头讲章感兴趣,但一定能从一个南京“馋人”妙趣横生的饮食札记中触摸到自己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印记。
从这个角度说,《南京味道》好就好在,它写的不仅是南京菜的味道,更是南京人的味道、南京城的味道、南京文化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