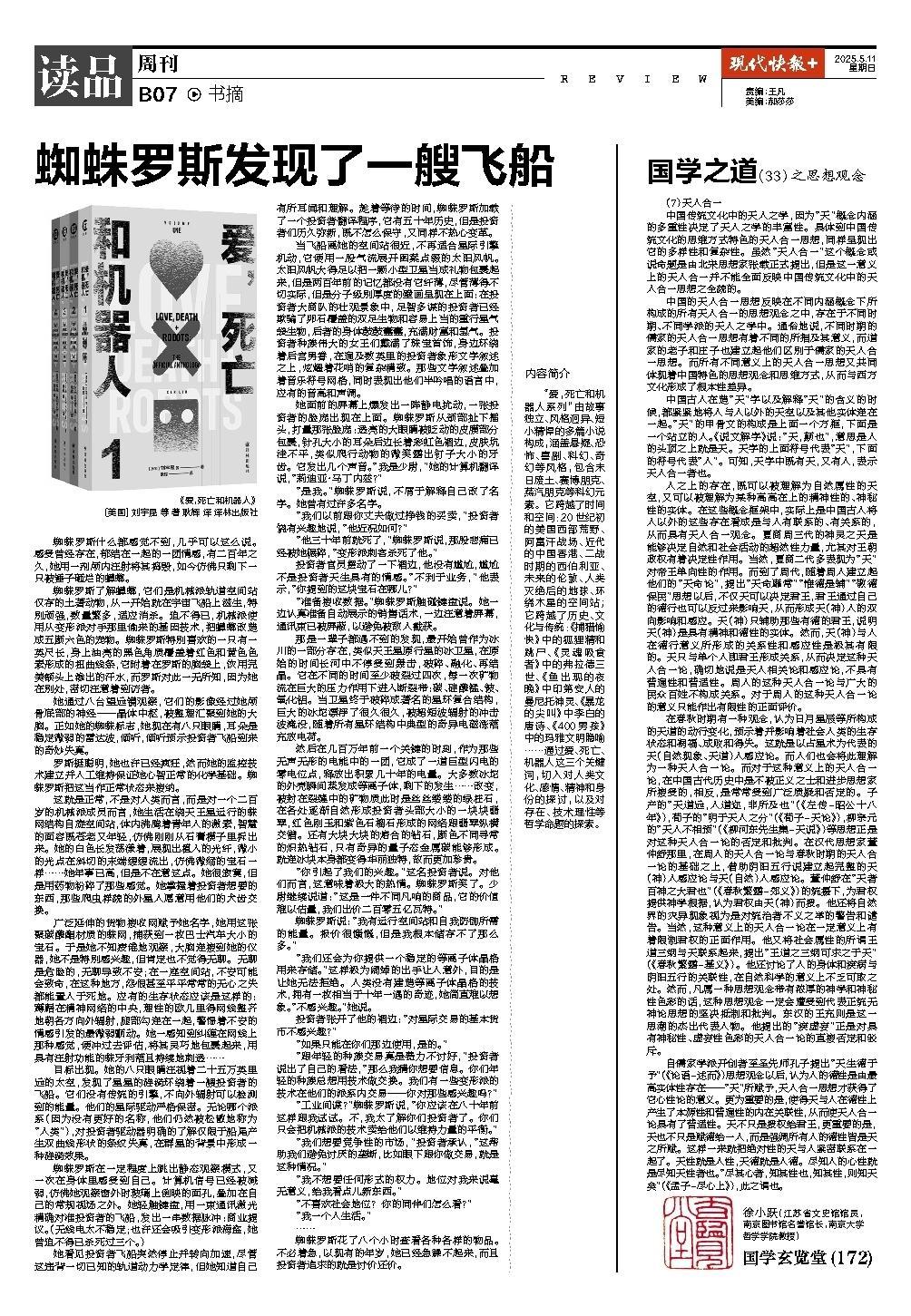(7)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之学,因为“天”概念内涵的多重性决定了天人之学的丰富性。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同样呈现出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虽然“天人合一”这个概念或说命题是由北宋思想家张载正式提出,但是这一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之全貌的。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反映在不同内涵概念下所构成的所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之中,存在于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天人之学中。通俗地说,不同时期的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有着不同的所指及其意义,而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也建立起他们区别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而所有不同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思想又共同体现着中国特色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与西方文化形成了根本性差异。
中国古人在造“天”字以及解释“天”的含义的时候,都紧紧地将人与人以外的天空以及其他实体连在一起。“天”的甲骨文的构成是上面一个方框,下面是一个站立的人。《说文解字》说:“天,颠也”,意思是人的头顶之上就是天。天字的上面符号代表“天”,下面的符号代表“人”。可知,天字中既有天,又有人,表示天人合一者也。
人之上的存在,既可以被理解为自然属性的天空,又可以被理解为某种高高在上的精神性的、神秘性的实体。在这些概念框架中,实际上是中国古人将人以外的这些存在看成是与人有联系的、有关系的,从而具有天人合一观念。夏商周三代的神灵之天是能够决定自然和社会活动的超然性力量,尤其对王朝政权有着决定性作用。当然,夏商二代多表现为“天”对帝王单向性的作用。而到了周代,随着周人建立起他们的“天命论”,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敬德保民”思想以后,不仅天可以决定君王,君王通过自己的德行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天,从而形成天(神)人的双向影响和感应。天(神)只辅助那些有德的君王,说明天(神)是具有精神和德性的实体。然而,天(神)与人在德行意义所形成的关系性和感应性是极其有限的。天只与单个人即君王形成关系,从而决定这种天人合一论,确切地说是天人相关论和感应论,不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周人的这种天人合一论与广大的民众百姓不构成关系。对于周人的这种天人合一论的意义只能作出有限性的正面评价。
在春秋时期有一种观念,认为日月星辰等所构成的天道的动行变化,预示着并影响着社会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祸福、成败和得失。这就是以占星术为代表的天(自然现象、天道)人感应论。而人们也会将此理解为一种天人合一论。而对于这种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是不被正义之士和进步思想家所接受的,相反,是常常受到广泛质疑和否定的。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柳河东先生集-天说》)等思想正是对这种天人合一论的否定和批判。在汉代思想家董仲舒那里,在周人的天人合一论与春秋时期的天人合一论的基础之上,借助阴阳五行说建立起完整的天(神)人感应论与天(自然)人感应论。董仲舒在“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义》)的统摄下,为君权提供神学根据,认为君权由天(神)而授。他还将自然界的灾异现象视为是对统治者不义之举的警告和谴告。当然,这种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论在一定意义上有着限制君权的正面作用。他又将社会属性的所谓王道三纲与天联系起来,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他还讨论了人的身体和疾病与阴阳五行的关联性,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不乏可取之处。然而,凡属一种思想观念带有浓厚的神学和神秘性色彩的话,这种思想观念一定会遭受到代表正统无神论思想的坚决抵制和批判。东汉的王充则是这一思潮的杰出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疾虚妄”正是对具有神秘性、虚妄性色彩的天人合一论的直接否定和驳斥。
自儒家学派开创者至圣先师孔子提出“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思想观念以后,认为人的德性是由最高实体性存在——“天”所赋予,天人合一思想才获得了它心性论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使得天与人在德性上产生了本源性和普遍性的内在关联性,从而使天人合一论具有了普适性。天不只是授权给君王,更重要的是,天也不只是赋德给一人,而是强调所有人的德性皆是天之所赋。这样一来就把绝对性的天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天性就是人性,天德就是人德。尽知人的心性就是尽知天性者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