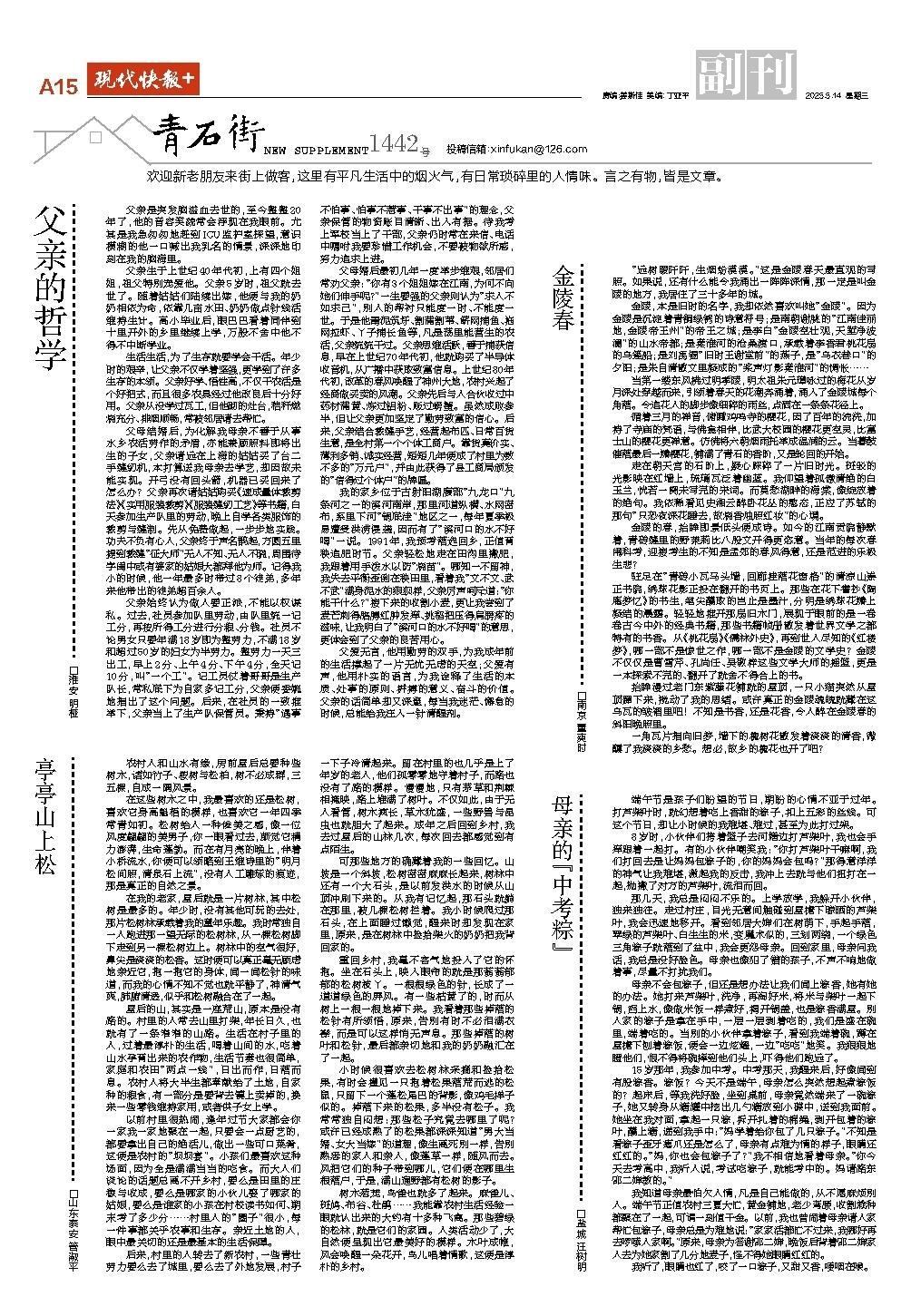□淮安 明桠
父亲是突发脑溢血去世的,至今整整2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常会浮现在我眼前。尤其是我急匆匆地赶到 ICU监护室探望,意识模糊的他一口喊出我乳名的情景,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上有四个姐姐,祖父特别宠爱他。父亲5岁时,祖父就去世了。随着姑姑们陆续出嫁,他便与我的奶奶相依为命,依靠几亩水田、奶奶做点针线活维持生计。高小毕业后,眼巴巴看着同伴到十里开外的乡里继续上学,万般不舍中他不得不中断学业。
生活生活,为了生存就要学会干活。年少时的艰辛,让父亲不仅学着坚强,更学到了许多生存的本领。父亲好学、悟性高,不仅干农活是个好把式,而且很多农具经过他改良后十分好用。父亲从没学过瓦工,但他砌的灶台,秸秆燃烧充分、排烟顺畅,常被邻居请去帮忙。
父母结婚后,为化解我母亲不善于从事水乡农活劳作的矛盾,亦能兼顾照料即将出生的子女,父亲请远在上海的姑姑买了台二手缝纫机,本打算送我母亲去学艺,却因故未能实现。开弓没有回头箭,机器已买回来了怎么办?父亲再次请姑姑购买《速成量体裁剪法》《实用服装裁剪》《服装缝纫工艺》等书籍,白天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晚上自学各类服饰的裁剪与缝制。先从免费做起,一步步地实践。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终于声名鹊起,方圆五里提到裁缝“征大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周围待字闺中或有婆家的姑娘大都拜他为师。记得我小的时候,他一年最多时带过8个徒弟,多年来他带出的徒弟超百余人。
父亲始终认为做人要正派,不能以权谋私。过去,社员参加队里劳动,由队里统一记工分,再按所得工分进行分粮、分钱。社员不论男女只要年满18岁即为整劳力,不满18岁和超过50岁的妇女为半劳力。整劳力一天三出工,早上2分、上午4分、下午4分,全天记10分,叫“一个工”。记工员仗着哥哥是生产队长,常私底下为自家多记工分,父亲便委婉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在社员的一致推举下,父亲当上了生产队保管员。秉持“遇事不怕事、怕事不惹事、干事不出事”的理念,父亲保管的物资账目清晰、出入有据。待我考上军校当上了干部,父亲仍时常在来信、电话中嘱咐我要珍惜工作机会,不要被物欲所惑,努力追求上进。
父母婚后最初几年一度举步维艰,邻居们常劝父亲:“你有3个姐姐嫁在江南,为何不向她们伸手呢?”一生要强的父亲则认为“求人不如求己”,别人的帮衬只能度一时、不能度一世。于是他罱泥筑圩、割蒲割苇、簖网捕鱼、拖网拉虾、丫子捕长鱼等,凡是荡里能营生的农活,父亲统统干过。父亲思维活跃,善于捕获信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就购买了半导体收音机,从广播中获取致富信息。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春风唤醒了神州大地,农村兴起了经商做买卖的风潮。父亲先后与人合伙收过中药材蒲黄、炼过铝粉、贩过螃蟹。虽然成败参半,但让父亲更加坚定了勤劳致富的信心。后来,父亲结合裁缝手艺,经营起布匹、日常百货生意,是全村第一个个体工商户。靠货真价实、薄利多销、诚实经营,短短几年便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万元户”,并由此获得了县工商局颁发的“信得过个体户”的牌匾。
我的家乡位于古射阳湖腹部“九龙口”九条河之一的溪河南岸,那里河道纵横、水网密布,系里下河“锅底洼”地区之一,每年夏季极易遭受洪涝侵袭,因而有了“溪河口的水不好喝”一说。1991年,我预考落选回乡,正值育秧追肥时节。父亲轻松地走在田沟里撒肥,我跟着用手泼水以防“烧苗”。哪知一不留神,我失去平衡歪倒在秧田里,看着我“文不文、武不武”满身泥水的狼狈样,父亲厉声呵斥道:“你能干什么?”接下来的收割小麦,更让我尝到了麦芒刺得胳膊红肿发痒、挑稻把压得肩膀疼的滋味,让我明白了“溪河口的水不好喝”的意思,更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父爱无言,他用勤劳的双手,为我成年前的生活撑起了一片无忧无虑的天空;父爱有声,他用朴实的语言,为我诠释了生活的本质、处事的原则、拼搏的意义、奋斗的价值。父亲的话简单却又深邃,每当我迷茫、懈怠的时候,总能给我注入一针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