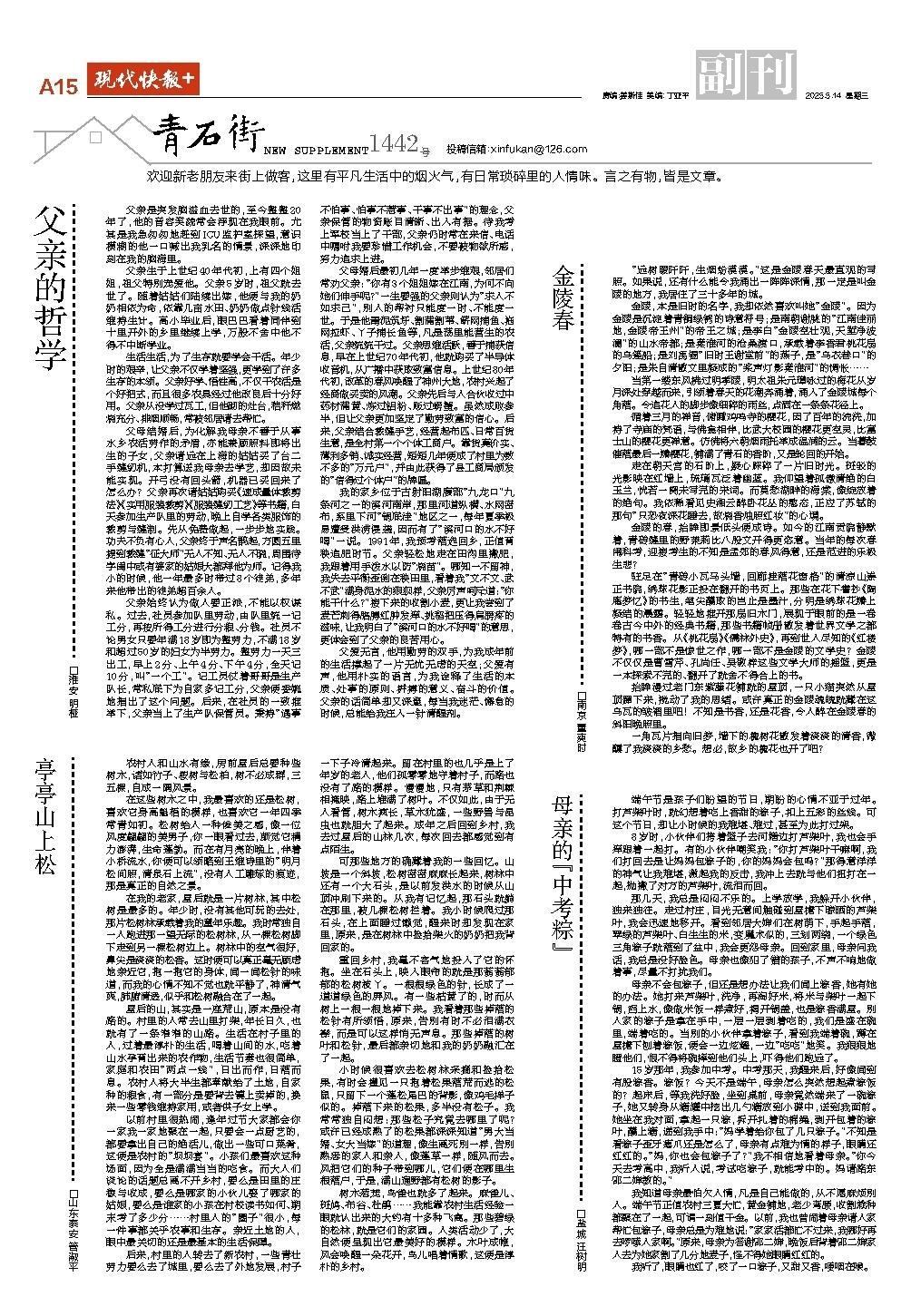□盐城 汪树明
端午节是孩子们盼望的节日,期盼的心情不亚于过年。打芦柴叶时,就幻想着吃上香甜的粽子,扣上五彩的丝线。可这个节日,却让小时候的我难堪、难过,甚至为此打过架。
8岁时,小伙伴们挎着篮子去河塘边打芦柴叶,我也会手痒跟着一起打。有的小伙伴嘲笑我:“你打芦柴叶干嘛啊,我们打回去是让妈妈包粽子的,你的妈妈会包吗?”那得意洋洋的神气让我难堪,激起我的反击,我冲上去就与他们扭打在一起,抛撒了对方的芦柴叶,流泪而回。
那几天,我总是闷闷不乐的。上学放学,我躲开小伙伴,独来独往。走过村庄,目光无意间触碰到屋檐下晾晒的芦柴叶,我会迅速地移开。看到邻居大婶们在树荫下,手起手落,翠绿的芦柴叶、白生生的米,变魔术似的,三划两绕,一个绿色三角粽子就落到了盆中,我会更怨母亲。回到家里,母亲问我话,我总是没好脸色。母亲也像犯了错的孩子,不声不响地做着事,尽量不打扰我们。
母亲不会包粽子,但还是想办法让我们闻上粽香,她有她的办法。她打来芦柴叶,洗净,再淘好米,将米与柴叶一起下锅,舀上水,像做米饭一样煮好,揭开锅盖,也是粽香满屋。别人家的粽子是拿在手中,一层一层剥着吃的,我们是盛在碗里,端着吃的。当别的小伙伴拿着粽子,看到我端着碗,蹲在屋檐下刨着粽饭,便会一边炫耀,一边“吃吃”地笑。我狠狠地瞪他们,恨不得将碗摔到他们头上,吓得他们跑远了。
15岁那年,我参加中考。中考那天,我醒来后,好像闻到有股粽香。粽饭?今天不是端午,母亲怎么突然想起煮粽饭的?起床后,等我洗好脸,坐到桌前,母亲竟然端来了一碗粽子,她又转身从糖罐中挖出几勺糖放到小碟中,送到我面前。她坐在我对面,拿起一只粽,拆开扎着的棉绳,剥开包着的粽叶,蘸上糖,递到我手中:“妈学着给你包了几只粽子。”不知是看粽子歪牙瘪爪还是怎么了,母亲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眼睛还红红的。“妈,你也会包粽子了?”我不相信地看着母亲。“你今天去考高中,我听人说,考试吃粽子,就能考中的。妈请路东邵二婶教的。”
我知道母亲最怕欠人情,凡是自己能做的,从不愿麻烦别人。端午节正值农村三夏大忙,黄金铺地,老少弯腰,收割栽种都聚在了一起,可谓一刻值千金。以前,我也曾闹着母亲请人家帮忙包粽子,母亲总是为难地说:“家家活都忙不过来,我哪好再去啰嗦人家啊。”原来,母亲为答谢邵二婶,晚饭后背着邵二婶家人去为她家割了几分地麦子,怪不得她眼睛红红的。
我听了,眼睛也红了,咬了一口粽子,又甜又香,哽咽在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