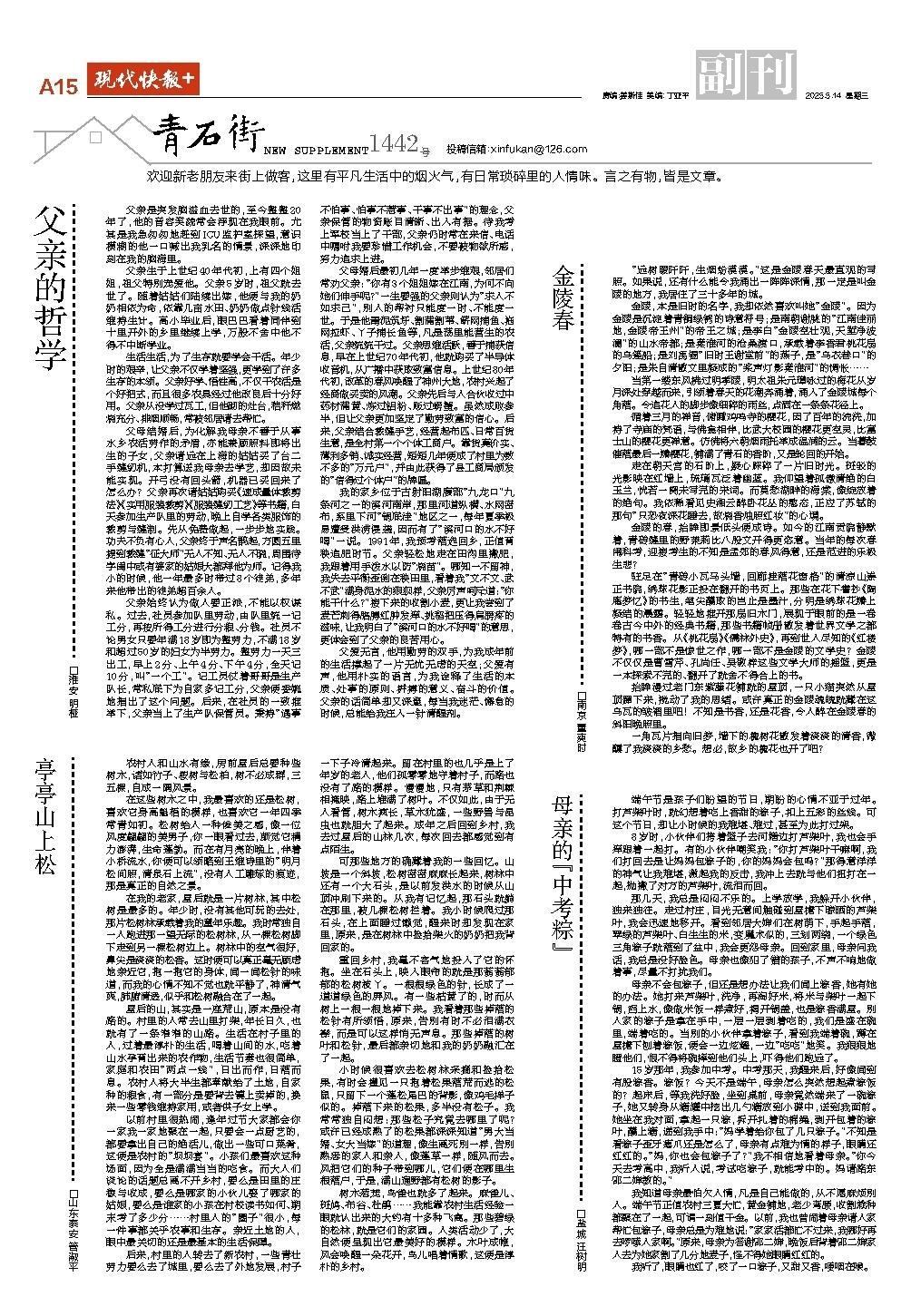□山东泰安 管淑平
农村人和山水有缘,房前屋后总要种些树木,诸如竹子、桉树与松柏,树不必成群,三五棵,自成一隅风景。
在这些树木之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松树,喜欢它身高魁梧的模样,也喜欢它一年四季常青如初。松树给人一种俊美之感,像一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你一眼看过去,颇觉它精力澎湃,生命蓬勃。而在有月亮的晚上,伴着小桥流水,你便可以领略到王维诗里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那是真正的自然之景。
在我的老家,屋后就是一片树林,其中松树是最多的。年少时,没有其他可玩的去处,那片松树林承载着我的童年乐趣。我时常独自一人跑进那一望无际的松树林,从一棵松树脚下走到另一棵松树边上。树林中的空气很好,鼻尖是淡淡的松香。这时便可以真正毫无顾虑地亲近它,抱一抱它的身体,闻一闻松针的味道,而我的心情不知不觉也就平静了,神清气爽,肺腑清透,似乎和松树融合在了一起。
屋后的山,其实是一座荒山,原本是没有路的。村里的人常去山里打柴,年长日久,也就有了一条窄窄的山路。生活在村子里的人,过着最淳朴的生活,喝着山间的水,吃着山水孕育出来的农作物,生活节奏也很简单,家庭和农田“两点一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村人将大半生都奉献给了土地,自家种的粮食,有一部分是要背去镇上卖掉的,换来一些零钱维持家用,或者供子女上学。
以前村里很热闹,逢年过节大家都会你一家我一家地聚在一起,只要会一点厨艺的,都要拿出自己的绝活儿,做出一些可口菜肴,这便是农村的“坝坝宴”。小孩们最喜欢这种场面,因为全是满满当当的吃食。而大人们谈论的话题总离不开乡村,要么是田里的庄稼与收成,要么是哪家的小伙儿娶了哪家的姑娘,要么是谁家的小孩在村校读书如何、期末考了多少分……村里人的“圈子”很小,每一件事都关乎农事和生存。亲近土地的人,眼中最关切的还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后来,村里的人转去了新农村,一些青壮劳力要么去了城里,要么去了外地发展,村子一下子冷清起来。留在村里的也几乎是上了年岁的老人,他们孤零零地守着村子,而路也没有了路的模样。慢慢地,只有茅草和荆棘相掩映,路上堆满了树叶。不仅如此,由于无人看管,树木疯长,草木犹盛,一些野兽与昆虫也就胆大了起来。成年之后回到乡村,我去过屋后的山林几次,每次回去都感觉到有点陌生。
可那些地方的确藏着我的一些回忆。山坡是一个斜坡,松树密密麻麻长起来,树林中还有一个大石头,是以前发洪水的时候从山顶冲刷下来的。从我有记忆起,那石头就躺在那里,被几棵松树拦着。我小时候爬过那石头,在上面睡过懒觉,醒来时却发现在家里,原来,是在树林中捡拾柴火的奶奶把我背回家的。
重回乡村,我毫不客气地投入了它的怀抱。坐在石头上,映入眼帘的就是那蓊蓊郁郁的松树枝丫。一根根绿色的针,长成了一道道绿色的屏风。有一些枯黄了的,时而从树上一根一根地掉下来。我看着那些掉落的松针有所领悟,原来,告别有时不必泪满衣襟,而是可以这样悄无声息。那些掉落的树叶和松针,最后都亲切地和我的奶奶融汇在了一起。
小时候很喜欢去松树林采摘和捡拾松果,有时会撞见一只抱着松果落荒而逃的松鼠,只留下一个蓬松尾巴的背影,像鸡毛掸子似的。掉落下来的松果,多半没有松子。我常常独自闷想:那些松子究竟去哪里了呢?或许已经成熟了的松果都深深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像生离死别一样,告别熟悉的家人和亲人,像蓬草一样,随风而去。风把它们的种子带到哪儿,它们便在哪里生根落户,于是,满山遍野都有松树的影子。
树木葱茏,鸟雀也就多了起来。麻雀儿、斑鸠、布谷、杜鹃……我能靠农村生活经验一眼就认出来的大约有十多种飞禽。那些碧绿的松林,就是它们的家园。人类活动少了,大自然便呈现出它最美好的模样。木叶成帷,风会唤醒一朵花开,鸟儿唱着情歌,这便是淳朴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