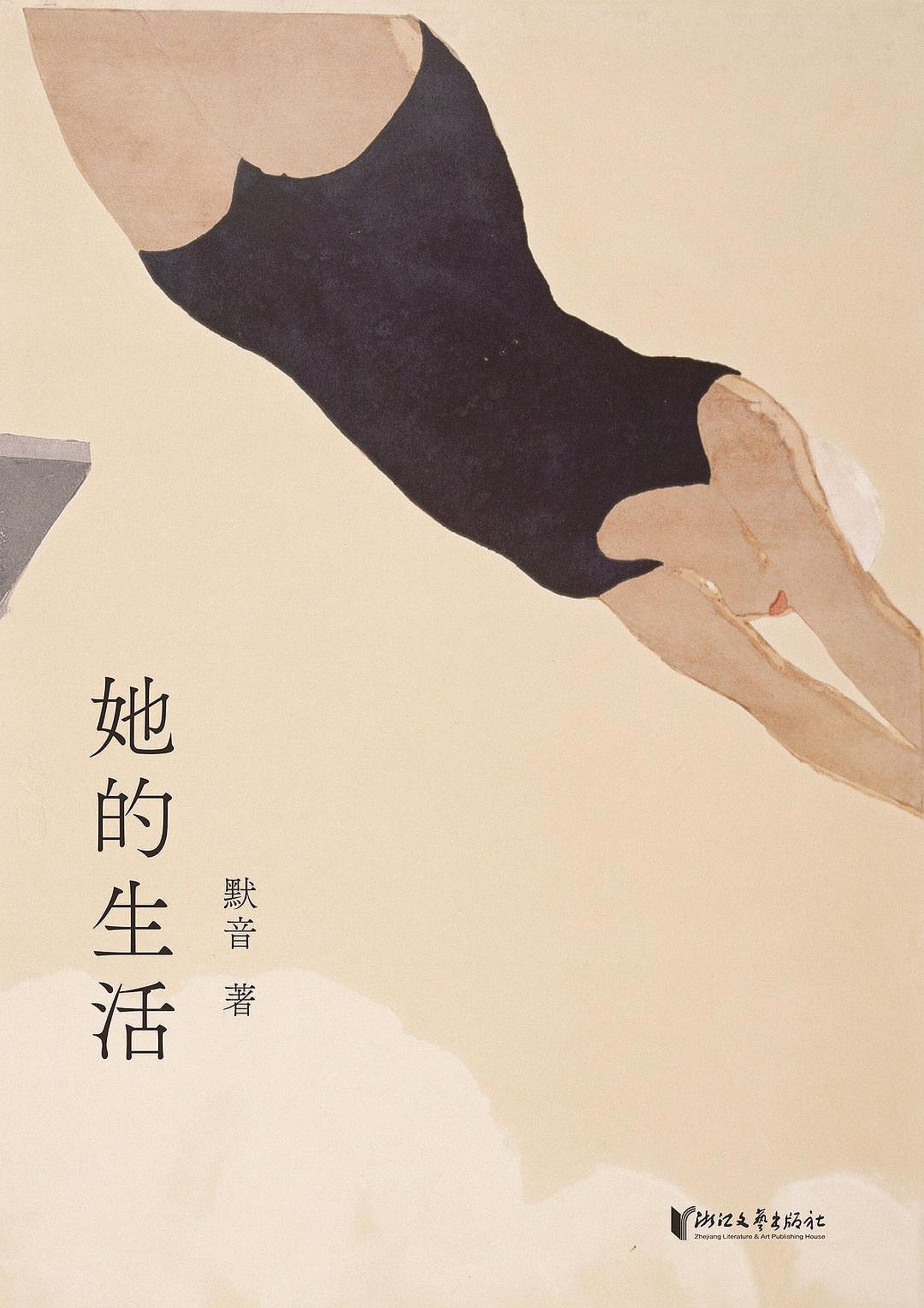默音的写作始于迷茫的16岁,当时她作为知青子女从云南回上海参加中考,结果失利考进了一所职校。在职校期间,默音偶然读到一本没有封皮,也没有前十几页的书,甚至不知道书名叫什么、是谁写的,看完后却惊为天人,还书的时候她才知道,这本书是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后来,因为日语不错,默音进入日资商场上海第一八佰伴实习,被分在中国字画和文房四宝柜台,“商场经理是一个文艺中年,他办了对商场来说规格过高的西安碑林拓片展,那个展厅没有一个人进来看,有一个星期我都站在《颜氏家庙碑》面前,看着古时候中国人的字迹,不知道自己将来是不是就这样一直当营业员。”
站柜台没事做的空闲里,默音想到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在同事的鼓励下写成科幻小说《花魂》,投给《科幻世界》后,获得“少年凡尔纳奖”,由此开启写作之路。而日语的精进,则让她从“村上春树的读者”逐渐成长为专业的译者,先后翻译了《青梅竹马》《日日杂记》等日本文学作品。
穿梭于作家与译者的双重身份之间,在默音笔下,现实与虚构相互渗透,记忆与历史交织共生。新近出版的两部作品延续了默音之前的创作脉络,《笔的重量》将镜头对准日本文学史上几位天才女性创作者,她们曾努力打破边界,却正在被人遗忘;《她的生活》中则讲述了六个不同的“她”的故事,投射了当代女性的生存境遇。两本新书互为镜像,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读者可以触达“她们”的世界,也可以照见自己的生活。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文 马晶晶 顾闻/摄
跨越百年,女性手中“笔的重量”
读品:《笔的重量》关注明治至昭和时代的女性创作者,为何选择聚焦于樋口一叶、田村俊子、武田百合子、尾竹红吉和高村智惠子,她们的经历中有哪些精神特质打动了您?
默音:首先并不是一开始我来选择这些题目,而是这些题目选择了我。契机是在2019年辞职以后对收入有点焦虑,就接了樋口一叶的翻译工作。在翻译樋口一叶的过程中,我发现她本人的日记和她同时代人写的关于她的文字出现了参差,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虚构,她描摹的是她理想的世界、理想的自己,并不是真实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想还原尽可能真实的一叶,就写了《一叶,在明治的尘世中》。当时还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就以樋口姐妹为原型,写了一个现代日本的故事。我把她写日记、写和歌的两种特质分别放在主人公和她妹妹身上,设想如果是在现代的东京,像她们这样非常年轻、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孩会有怎样的遭遇,以这样的初衷写了《彼岸之夏》这篇小说。
这些只是开始,樋口一叶之后,我想翻译自己最喜爱的作家武田百合子,便主动去向出版社建议。之前国内没有译介过武田百合子,要做一个没有译介过的作者其实是很困难的,我先给出版社写了作者和作品的简介,选择了她在世的时候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日日杂记》,因为她的作品到晚年迈入成熟期,这本书的体量也比较小,现代人阅读时比较容易进入。坦白说,我虽然非常喜爱武田百合子,并且读过她所有的作品,但我在翻译《日日杂记》的时候,对她的生平还不了解。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她,我读了大量的相关材料,这才惊讶地发现,如果不是她丈夫武田泰淳先去世了,我们可能无法读到武田百合子的作品。我感到有必要把她完整的人生历程呈现出来,就写了《口述笔记员的声音》。同样也是翻译,然后写非虚构,再拓展到小说,我又写
了科幻小说《梦城》,设想《富士日记》作为文本,在未来会有怎样的呈现。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田村俊子这里,遇到田村俊子完全是偶然,因为武田百合子拿了“田村俊子文学奖”,我想知道这个奖项背后的人是谁,开始读相关材料,没想到一读就花了大半年时间。写非虚构《她的生活》的过程,也是整理思路的过程。有许多激动的时刻,看到了不少有趣的材料,横向、纵向都可以联系起来。写完以后我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国内没有平台可以发一篇五万字的非虚构,这个时候我才想到,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文章合成一本书,后来又写了尾竹红吉那篇,就成了现在这本小书。这一步一步可以说是偶然,也可以说是必然。
读品:“笔的重量”既指物理重量,也指精神分量。在您看来,当代女性创作者面临着怎样的“笔的重量”?
默音:其实很多方面还是特别相像的。《笔的重量》写俊子的那篇提到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的小说《伸子》国内翻译成《逃走的伸子》,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作家结婚之后,她和丈夫的关系、和原生家庭的关系,所有的这些都在阻碍她继续写作,她想要从中挣脱出来。我看了《逃走的伸子》中译本的一些评论,尽管是一百多年前的小说,大家看的时候完全不会觉得它是一本过去的作品,伸子的处境跟我们现在的人还是非常接近的。我觉得有些东西永不过时,虽然时代进步了,进步的科技能让我们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解放,但本质上的一些东西是没有变化的。
一鱼三吃,打捞“她的生活”
读品:在写《笔的重量》时,您是否遇到过史料缺失的情况?如何通过旁证或文本细读还原这些女性作家的真实面貌?
默音:最开心的是找到这些女作家之外的人的记录。比如,田村俊子写过《千岁村的一天》记录一次聚会,在挖掘的时候,我发现有位研究农业的女性丸冈秀子写过一本书《田村俊子和我》,里面提到她就是在那场聚会上认识了田村俊子,当你发现这些巧合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有种可以把所有同时代的人串起来的感觉。
田村俊子在日本获得的研究是很充分的,她的全集是我见过最惊人的全集,每本都很厚。这套全集找到了她从明治、大正到昭和的所有文章原来登载的刊物,然后影印出来,你可以看到原来的字体,每一篇作品后面都有一篇解题,两位编者把她的生活经历,以及生活如何影响她的创作都写了出来,这套全集的工作真的是太伟大了。相对缺乏记录的是田村俊子晚年的上海经验,我在上海图书馆看了田村俊子主编的《女声》杂志电子扫描件,又去了俊子曾经工作过、居住过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好像离她更近了一些。
读品:小说集《她的生活》中《彼岸之夏》《竹本无心》《梦城》三篇与三位日本女作家的经历形成现代互文,为何选择将历史人物投射到当代上海、东京甚至未来的场景中?
默音:在翻译她们的作品、整理她们人生经历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你跟她们朝夕相处,就好像她们是你的朋友,所以写完非虚构,总觉得还没写够,就会想要用小说再做一些呈现。我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是“一鱼三吃”。反正每一次到最后还是要落回到小说上,可能我本质上还是写小说的人。樋口一叶和田村俊子,我把她们的人物形象在小说里做了一些折射。但是到了武田百合子这里,可能因为太喜欢她,我没有办法设想出一个像她的虚构人物,只能设想,到了未来,仍然有人在读《富士日记》,但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梦城》其实是前两年写的,当时我们关于AI的讨论还没有现在这么切近。
读品:在《梦城》中,人们通过脑机接口代入电视剧(视梦)角色。在现实生活里,VR、AR技术发展,沉浸式体验逐渐普及,您觉得未来的文学创作是否也会借助这类技术,实现全新的沉浸式创作与阅读模式?
默音:我对纯粹文字阅读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过去的这几十年间,观看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阅读。但阅读有它无可替代的一面,因为你在获得感知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想象在里面,而观看这件事情太便捷了,你习惯了一切都是别人灌输给你的,在生活中你会逐渐缺乏建构想象的能力。
“写自己想写的,才是最佳的复仇!”
读品:《口述笔记员的声音》写到武田泰淳小说对妻子武田百合子日记的“借用”,在泰淳去世后,身为随笔作家的武田百合子才悄然出现。《上海之夜》中龚清杨一度因被抄袭放弃写作,最后在与两位作家交谈后决定重新启航,“写自己想写的,才是最佳的复仇!”这是不是您对亲身经历过被抄袭事件的一种回应和了结?
默音:《上海之夜》的写作时间,其实是在抄袭事件被曝光之前,当时我觉得写完这一篇,等于是我个人对抄袭事件的一种了结。曝光之后,对方的种种回应让我很庆幸先写了小说。小说里的抄袭者具有他的才能,虽然是个坏人,但有他的魅力,那是我想象出来的人物。如果你看过现实中的人物,你就很难在小说中想象。
说到泰淳对百合子创作的挪用,我觉得是他们夫妻的一种心照不宣。百合子一开始写日记,就是因为泰淳要求她记下周围人的谈话,明显是要把妻子的日记作为素材本。包括后来他写《新·东海道五十三次》,还有最后写《眩晕的散步》,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百合子的笔记,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中已经非常习惯使用太太做的所有这些记录,他没有“这么做是在剽窃”的概念,百合子本人也没有。首先她本人不觉得自己是创作者,直到她成为作家之后,仍然没有创作者的自觉,她也没有像我们会有的创作者的焦虑,因为她的才能过于丰盛,她每天看到的东西就足够她写,甚至很多时候她只是穿过了生活,并没有写下来。她在临终前要求女儿武田花把她所有的手稿都烧掉,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她所有发表过的文字,可能在那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大家都没有办法看到。
读品:翻译工作、曾用日文写作的经历是否让您对中文创作产生了新的认知?中文与日文在写作时“手感”有何不同?
默音:手感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从16岁就开始写中文小说了,但写日文小说是从六七年前开始的,当时大概是一年写两篇的节奏。在写日文小说的时候,我感觉不是我,而是一个新的写作者,会想写很多迄今为止没有写过的题材,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种锻炼。我写的日文小说当中,只有《上海之夜》的日文版给我以前公司的日本上司看过,他看了之后似乎有些讶异,说“原来你写这样的小说”。在翻译武田百合子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写出像她那样精准的日语,总觉得用另一种语言创作还是有隔膜,所以后来就放弃了,还是回到中文写作。
读品:未来您有什么样的创作、翻译或其他计划可以透露?
默音:我今年修订完了一部以前翻译过的作品,梨木香步的《家守绮谭》,是早些年翻译的。之前一直觉得翻译得挺用心的,但这次花了将近两个月来修订这本很薄的书,我想这说明我进步了,也说明一个人总是有进步的空间。编辑说希望能看到新长篇,但是我暂时还没有长篇的计划,写长篇真的需要投入很多时间、精力和很大的决心,所以现在暂时在写中短篇。也想尽可能多看一些书。有很多感兴趣的范围,现在看的主要是历史方面的书,也不是说一定会在这个范围内写小说,目前就处在这种“播种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