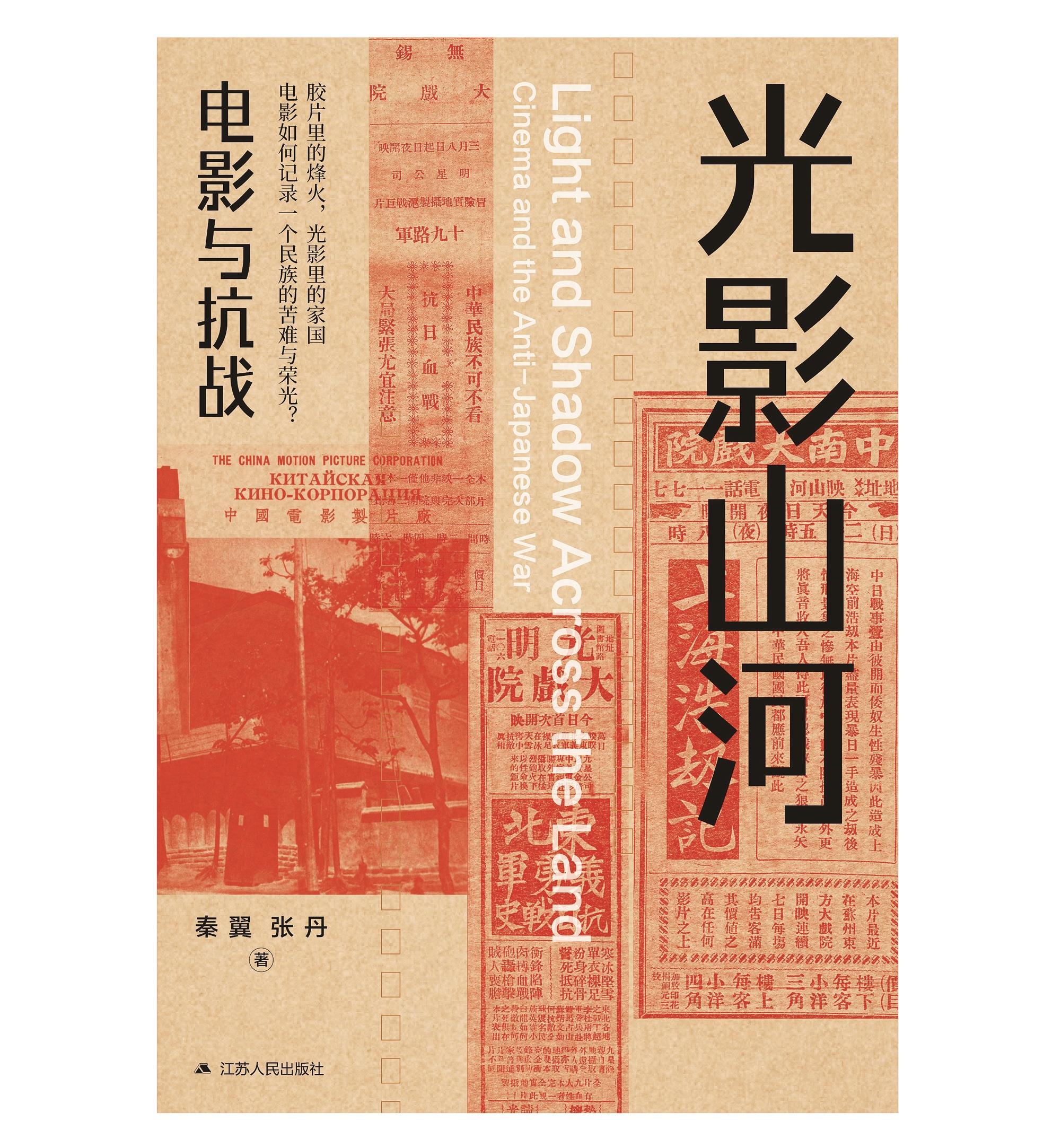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在此契机下,一本名为《光影山河》的新著出版发行。
抗战文学进入高考作文题,燃起了“民族魂”,抗战电影胶片的转动,投射出的亦是一个民族在战火硝烟中沉重的喘息、不屈的脊梁与投向未来的灼灼目光。十四年烽火,胶片不仅是记录者,更是参与者、武器,是山河破碎之际,一群电影人用镜头书写的“战地家书”。
本书作者秦翼与张丹,并没有将抗战电影史等闲看作艺术流变或行业兴衰的注脚。穿透尘封的影像档案与文献资料,她们将视角对准了银幕背后的文化暗战、产业挣扎与精神突围——
大后方的坚守、“孤岛”的求生、沦陷区的苦闷,还有根据地人民电影的星火初燃……每一格胶片,都浸染着时代的血泪与选择。
“那个年代山河破碎凋零,但许许多多的电影人选择用光影,将大好河山保留了下来。在他们的镜头里,我们的山河是屹立不倒的。”秦翼说,在《光影山河》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部电影史,更是半部沉甸甸的抗战史,是光影交织下一个民族于至暗时刻发出的呐喊与写给未来的证言。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文
马晶晶/摄
一部电影史,半部抗战史
读品:关于抗战电影史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为何要作《光影山河》这样一本书呢?
秦翼:这本书写得很早,大概是六七年前南京大学在编写一套《抗日战争专题研究》的丛书,近代史研究的泰斗张宪文老师,还有当时南大朱庆葆书记担任主编。他们布局了几个方向,有文学、有艺术,里面还细分有音乐、美术、电影等,分得比较细。我们负责的就是电影部分,我记得当时,张宪文老师亲自抓这个项目,还专程给我们培训,那可是我们学生时代就高山仰止的人物。张老师一直在提醒我们,说不要把它写成一个特别艺术的东西,比如电影艺术的分析,或者一些抒发个人情感的表达,它还是要有宏观的历史思维。所以,我们写的时候也是按照非常严格的历史学规范来书写,印象非常深刻。
那本书出来之后,反响还不错,我们的责编老师就说,何不尝试着把这本书进行商业化出版呢。其实我们最开始写这本书,就是面向学者和专门研究者的,没有想过要把它推广给更多读者。但是,这本书的市场反响确实又出乎我们的意料,收获了很多正面评价,我们也开始意识到对它进行一定通俗化的修订,重新出版是有价值的。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这个时候推出这样一本书恰逢其时。这段时间,我们收到了很多来自电影研究界之外的读者的反馈,大家都在说,原来那个时代的电影不只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遗珠存在,很惊喜、很新奇,我们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读品:书中引用了大量战时档案、文集、日记、回忆录等珍稀史料。在挖掘和运用这些一手材料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张丹: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在于大量影像是散佚的,比如说,我的研究涉及一部纪录片,叫作《华北是我们的》,书里也有提到,它一直被认为是一部散佚的电影。为了找到这部电影,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相关的电影机构,都没有结果。直到来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查询资料目录的时候,和去过的所有机构一样,检索未果,但看到了一个名字很像的影片叫《华北风光》。
当时不甘心一无所获,想着就当作学术观摩看这部电影。但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越往后播映就越像我们文献记载中的《华北是我们的》,后来其实基本能够确信这就是所谓“散佚”的那一部。伴随巨大的喜悦而来的还有疑惑,这部片子为什么又改了名字呢?在这之后我又几经辗转到香港查阅报刊,最后形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证据链。前后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有曲折有辗转,最后柳暗花明,还是很难忘的。
烽火十四年,中国影人的困顿与坚守
读品:抗日战争时期的大银幕也是战场,书中将其形容为“胶片背后的文化暗战”。电影在这场“暗战”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秦翼:是的,我们在这里面也有写到,从当时一些影片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一步一步进行文化侵略的图谋。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告诉中国电影人,你们拍什么都无所谓,不干涉创作。接下来,他们会倡导拍一些反对英美的片子,比如当时导演朱石麟就拍了一部《良宵花弄月》,片子里面揶揄了一个向往西式生活的留学生。我相信朱石麟拍摄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迎合日方的意图,但这部片子在宣传的时候,却被包装成了主张反英美的影片。再后来就是合拍电影,比如1943年先出了一部片子叫《万世流芳》,这个题材还比较正常,甚至是反侵略的,讲的是林则徐禁烟。1944年又出了一部《春江遗恨》,就开始一定程度上美化日本人了。可以看出,侵略者对电影的控制是一步步的。
另外一方面,身处其中的中国电影人处境也很复杂微妙,但绝大多数还是非常有气节的。就上海和香港两地来说,有大量的名导演,比如司徒慧敏,就是全然拒绝日本人的邀请,哪怕再也不做电影。香港更早期的电影人中还有一位叫侯曜,他拒绝配合日本人并逃到了新加坡。但那个时候,日本在南洋查禁逃过来的中国人,然后他们找到并杀害了侯曜。整个沦陷期间,香港没有出产过一部本土故事片。在上海,还有我们熟知的费穆导演,这个时候他也不拍电影了,一门心思去做话剧。
费穆曾经在孤岛时期创作了一个非常“异类”的孔子的银幕形象,别的古装片可能几千块成本就拍完了,那部片子用了60万,票房惨淡完全没有收回成本。在战乱纷纷、人心叵测的时代里不断受挫、不断流亡,孔门书生恪守信仰,却最终在乱世中找不到解救世道人心的途径。费穆抒发的,何尝不是自己的困顿与忧思,照见了那个环境下知识分子群体的困顿。这部《孔夫子》其实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自喻。非常巧合的一件事,那个时代背景下有两位“穆先生”,钱穆先生辗转治史,功德无量,费穆先生用影像记录历史,也传为佳话。历史上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战乱当中守住自己,保持初心,用这样的方式来唤醒我们的民族,我觉得这是他们共通的地方。
读品:不少影人的故事贯穿全书各个章节,若连起来看就会非常传奇。在研究这些艺术家个体时,哪些故事或细节最让你动容?
张丹:我们之前聊到过一位叫贺孟斧的影剧人,他在大后方从事电影、戏剧工作,导演了《风雪太行山》等电影,还包括很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剧目,夏衍的《愁城记》、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及改编自巴金小说的《家》,还有《忠王李秀成》《桃花扇》《北京人》等。但令人痛心的是,1945年的时候他去世了,死于贫病交加,没有等来抗战的胜利。他才华横溢,但后期的生活特别艰苦,而他始终没有媚俗地去拍一些赚钱的戏,他的一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还有郑君里,他在拍《民族万岁》的过程中,有一张照片令我印象深刻,之前在都市中的电影人往往是西装革履,和今天的电影明星殊无二致。但在抗战时期行路,他们完全换了一种形象,尤其是他的妻子黄晨,甚至已经看不出来是一位女性。那张照片给我的触动很大,他们虽然装束是那样朴素,但是有一种非常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有一位同去拍摄的美工师,叫韩尚义。他写过一篇回忆录,文字里看不到任何对艰难险阻的描述,而是跟他们的青春岁月交融在一起的壮怀激烈的回忆,这也是让我觉得很震撼的地方。他们是一群真正把命运交给电影的人,没有任何对艰苦和危险的环境描述,没有抱怨,或者是不忿,能够始终对置身的环境保持好奇与探索,应该是一种艺术家的审美追求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这在当代依然有非凡的价值,我上课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能把这种精神力量传递给青年学生,我觉得任何时代都需要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
一个民族写给未来的战地家书
读品:这本书里将抗战电影喻为“一个民族写给未来的战地家书”,怎么理解这个比喻?
秦翼:从历史的角度,从前我们说写本书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其实我觉得电影方面亦是如此,它用影像的留存方式帮我们记录下了那段时间的历史,可能纪录片的方式更原始,故事片当中可能更曲折,它是用艺术化的方式去写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包括城市风貌、男欢女爱、家庭生活,还包括当时青年面对时代的选择,全都记录下来了。
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在不断研究的过程当中,能感受到另外一层东西。就是当时的这些电影人,可能有很多东西是不能言说的,因此他们就把心底的东西非常曲折地“包裹”起来,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再展示,甚至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你看上去完全像是一个娱乐电影,但是这个影片里面它所包含的东西,它可能就是一个自我隐喻,或者说是一种很曲折的展示。
比如说我前几天刚写了一个东西。抗战时的物资,其实是不足以拍像《红楼梦》这样的大制作的,因为不管是资金或者胶片都很有限。但中国第一部完整有声片的《红楼梦》是在1944年拍的,那个时候上海的电影业已经很困难了。这部电影里面就是宝黛钗的爱情,第一次看可能会觉得简化又简陋。但结合那个时代再去看,你会发现,这里面充满了隐喻:贾府就是“孤岛”,里面的贾宝玉以死抗争,也不愿意受人摆布,苟活于世。这种曲折,你说要花多少心思去解读,去和这些电影人的诉求沟通。所以我经常说做电影史,做到最后就“通灵”了,你不知道在哪个节骨眼上,突然就读懂了那封写给未来的“家书”。
秦翼
文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国电影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史论。著有《民国时期喜剧电影研究》等。
张丹
电影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史、电影口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