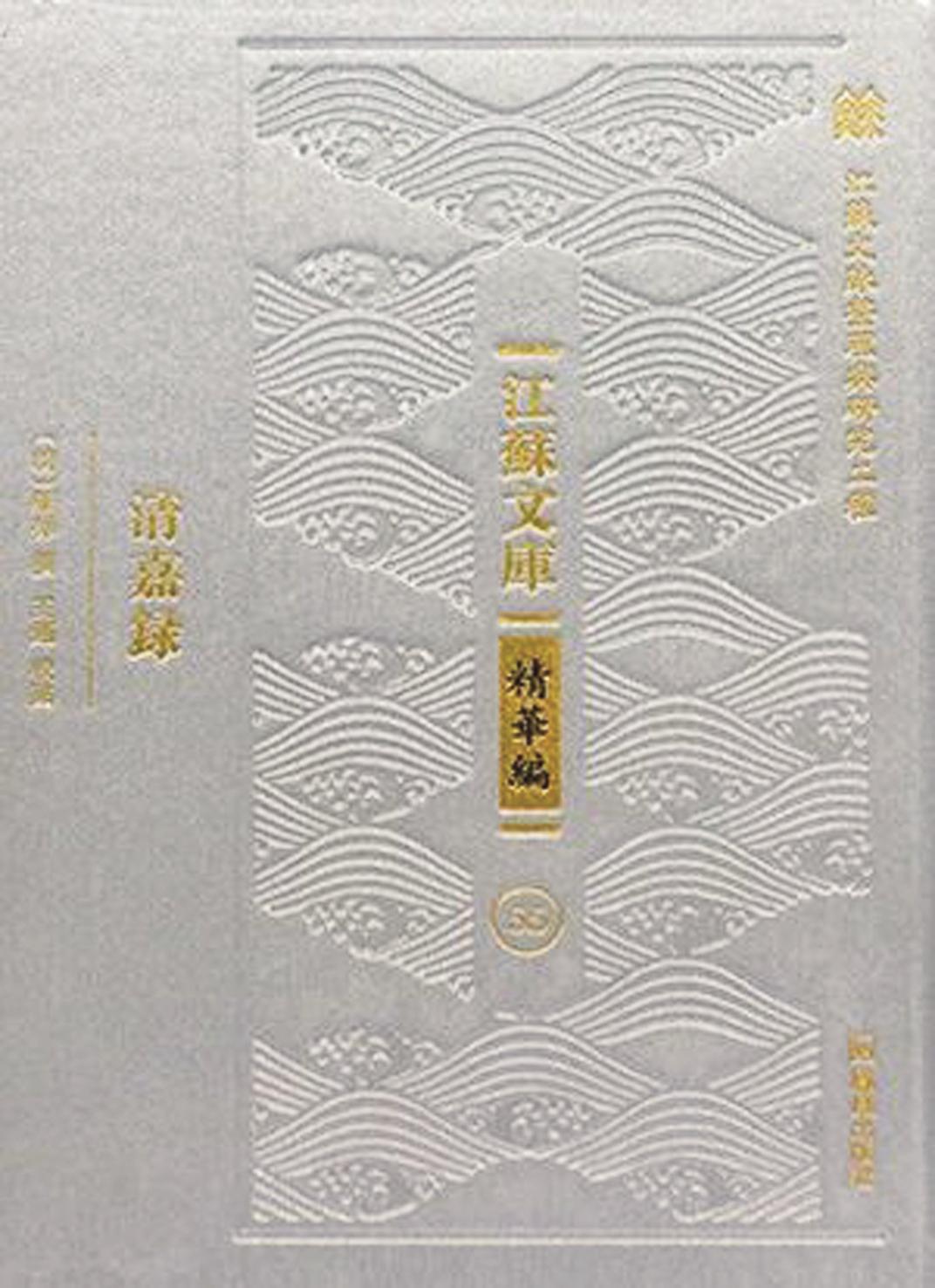最近,江苏多地接连官宣入梅。空气里浮动着水汽的重量。
千百年来,潮湿的梅雨不仅浸润了土地,更渗透进方言的肌理。
如果只能用一句话形容黄梅天,你会怎么说?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裴诗语/文 钱念秋/摄(除署名外)
南京
一到梅雨季,南京人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蛮再下点儿雨,湿答答的更难受,还雾躁。”
意思是:如果再下雨,就更潮湿难受了,还很闷热。
作为南北交汇之地,南京方言中既有北方的直率,又有江南的细腻。
梅雨季的南京,曾催生别样风雅。清代文人偏爱在此时节携壶聚于妙相庵,檐外雨帘垂落,檐内茶烟轻扬,一场场“雨集”诗会便在淅沥声中铺展。
史志学家陈作霖在《可园备忘录》中曾记:“五月雨集妙相庵,六月刘园观荷,七月飞霞阁看云,八月秦淮水榭玩月,皆具并文社会饮也。”
甘熙宅第的居民则展现出实用智慧:堂屋门口架设可拆卸的木质踏步,离地半米,隔绝潮气,晴日收起,雨时展开——一拆一装间,尽显生活巧思。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宋代赵师秀《约客》中的这句话,至今仍是梅雨最贴切的注脚。南京人在蛙鸣与棋声中,学会了与潮湿共处。
苏州
“哦哟,这个黄梅天真的是难行的。湿答答,身上么淂滋滋,衣服么潮扭扭,闻一闻么还有点馊嘎嘎……”梅雨季,苏州人用吴侬软语嗔怪雨水濡湿衣衫。
更烦躁的时候,苏州人会说:“雨下得人‘窝涩’的了”,用“齁丝热”形容天气闷热无比。
梅雨浸润了苏州的艺术灵魂。
明代沈周驻足太湖畔,将迷蒙雨雾凝成《西山雨观图》,水墨氤氲间尽显“烟雨江南”意境。
清代顾禄在《清嘉录》中记载了更风雅的习俗:家家以缸瓮接蓄“梅水”,用以烹茶,认为此时雨水“味独甘”。
于是有《吴中竹枝词》云:“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熏蒸润绿苔。瓷瓮竞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
至今老苏州人仍认为,梅水煮茶可解暑祛湿。一盏清茗中,喝的是天赐的滋润。
无锡
“个黄梅天么天天落雨,落得到处潮塌塌里,个衣裳黏答答里,一股霉尘头气。”无锡作为吴语核心区,方言中自带水汽。
在无锡方言中,人们习惯将“下雨”称为“落雨”;“潮塌塌”多指地面潮湿。
无锡宜兴,正是“梅雨”一词的诞生地。1700年前,宜兴人周处在《阳羡风土记》中首次定义:“夏至之雨,名为黄梅雨,沾衣服皆败黦(yuè)”。
至今,宜兴周王庙仍供奉周处,这位“除三害”的英杰,为江南留下了最早的气象记录。
苏东坡也钟爱此地,留下了“买田阳羡吾将老”的诗句,把宜兴作为他颐养天年的落脚地,想必也曾为黄梅时节又爱又恼。
常州
“阵头响霍霍显,雨落则密密猛猛。”在常州话里,“雷”叫“阵头”,乌云来袭要打雷下雨,用常州话讲就是“起阵头咧”;“霍霍显”或“霍显”在常州话中是“闪电”的意思。
常州方言中还有许多形容雨势大的词汇,形容雨下得大就用“密密猛猛落下来”;窗外雨太大,忘记关窗雨打进窗户里,常州话会说雨大到“哈进来”;雨大了屋里漫水,常州话叫“盘水”。
每当毗陵大地迎来阴雨连绵的梅雨季,家家户户都会想起一个人,他就是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葛洪。
梅雨时节,葛洪发现以盐晶炼丹,再溶以水,以青蒿枝蘸取洒身,可以祛除周身“霉气”,让人保持清爽健康,并将丹药命名为“盐丹”。
“盐丹”可以去湿气、清热解毒,在梅雨时节用更是疗效甚好,葛洪便将此法推广给茅山地区的民众。
镇江
“乖乖,这个雨落得‘结棍’。”“告诉你今天下雨,你非不听不带伞,你看看呢,汏得跟落汤鸡一样的。”
镇江这座江南城市却操江淮官话。镇江话里,把“淋雨”说成是汏雨。梅雨季又叫“时梅天”。
“水漫金山”的传说在镇江生根,每当《白蛇传》演出到白娘子借长江怒涛倒灌金山寺时,看戏的镇江人总忍不住嘀咕:“这雨怕不是比黄梅天还凶?”
诗人赵翼曾在梅雨季路过镇江,并留下诗句:“还乡正是黄梅候,且喜连朝澍雨零。”雨量少,总体没有影响他的归程。
随着气候变迁,“烟雨江南”正经历深刻转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研究显示,上世纪60年代以来,江苏梅雨期的“烟雨偏离度”持续上升,温和绵长的梅雨渐被暴雨或高温取代。
方言里的梅雨记忆越发珍贵。
乡音如伞
为每个江苏人撑起一片永恒的雨季天空
当老人教孙辈念“潮滋滋”“湿答答”
当茶馆里仍有人煮沸珍藏的“梅水”
那沾衣欲湿的惆怅、梅子黄时的期盼
便在水汽蒸腾中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