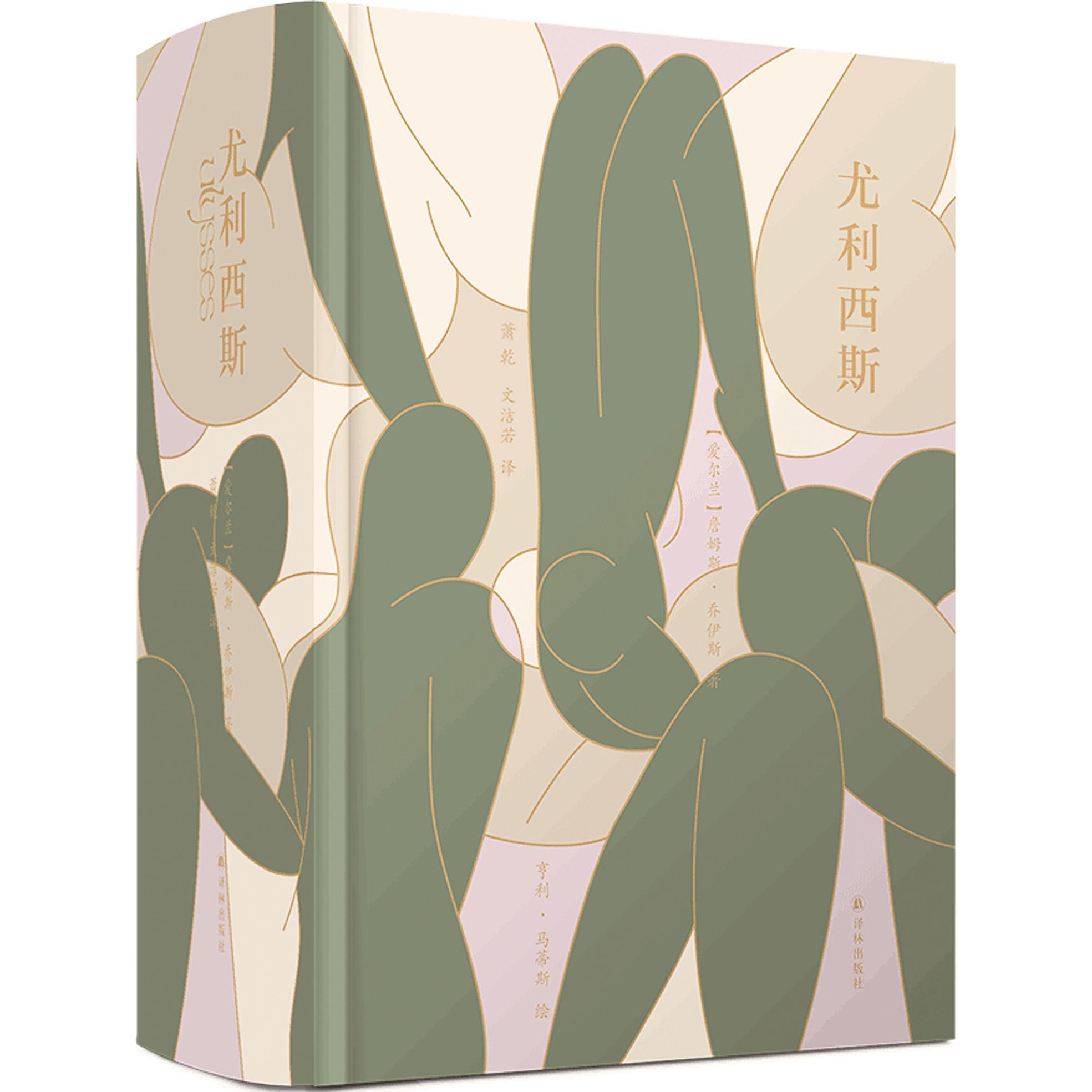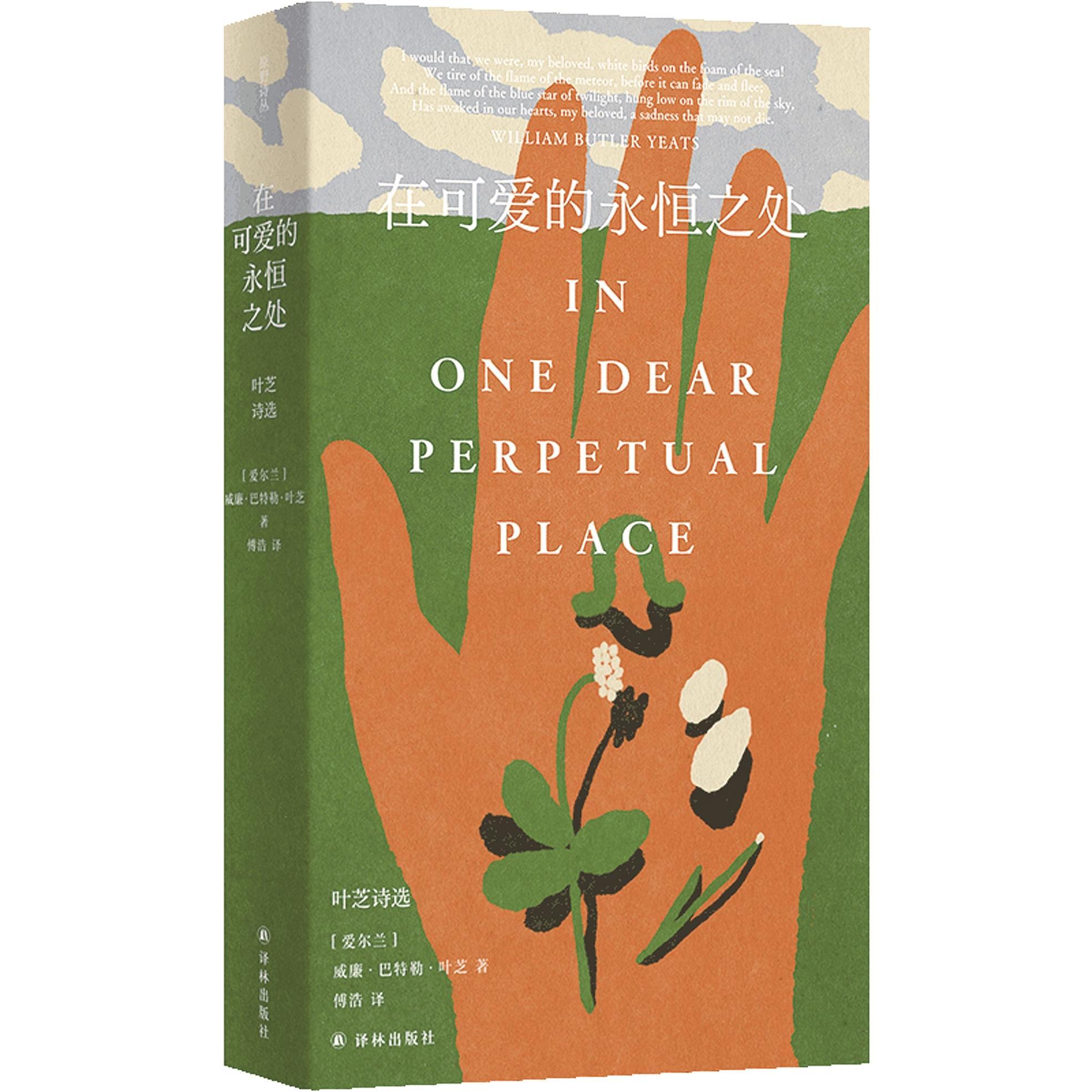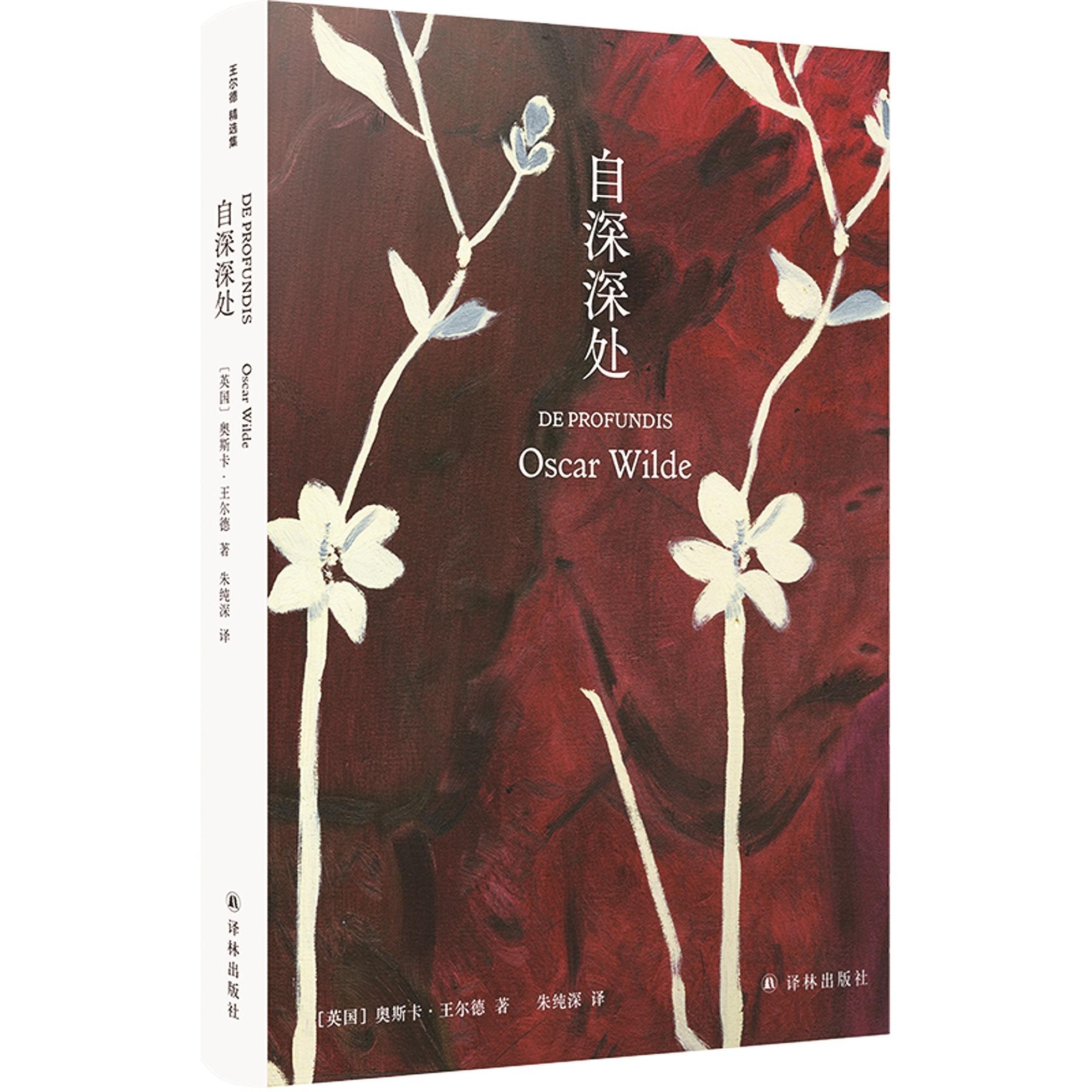“布卢姆日”是为数不多的为虚构人物设置的节日之一,它起源于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作品《尤利西斯》,该作讲述了主人公布卢姆在一昼夜间的游荡。每年6月16日,热爱《尤利西斯》的读者,会纷纷走上都柏林街头,乔装打扮,跟随布卢姆的行走路线,沉浸式体验主人公的一天。
今年的“布卢姆日”,爱尔兰驻上海总领事莫大维抵达南京,于先锋书店开启布卢姆日系列文化活动。
南京与《尤利西斯》渊源深厚——这里正是这部巨著首个中译本的诞生地。1991年,译林出版社决定出版中文版《尤利西斯》,几番波折后最终请到了萧乾、文洁若夫妇翻译。1994年,第一个《尤利西斯》中文全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在海内外引起了关注。百年《尤利西斯》,见证了两座“文学之都”的不解之缘。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世界文学高地爱尔兰
“爱尔兰虽地域狭小,却孕育了穿透时空的文化力量。”莫大维在致辞中细数爱尔兰文化符号:从风靡全球的《大河之舞》到西城男孩、恩雅等音乐传奇,从西里安·墨菲、保罗·麦斯卡到西尔莎·罗南的光影魅力,而文学领域的影响力尤为夺目。尤其是詹姆斯·乔伊斯,以《尤利西斯》重塑了现代文学的叙事边界,而每年6月16日的布卢姆日,正是全球读者以街头巡游、书店共读等形式致敬这部“文学奇书”的独特庆典。
如今,“布卢姆日”已从乔伊斯友人的小型聚会,演变为融合文字游戏、城市漫游的全球性文化狂欢。今年的“布卢姆日”庆典延伸至上海、苏州、南京三地,除聚焦《尤利西斯》外,更着眼爱尔兰文学的多元脉络:从叶芝、塞缪尔·贝克特、王尔德等巨匠,到希尼、克莱尔·基根、科尔姆·托宾等当代作家,他们以小说、诗歌、戏剧等多元体裁,将普通人的生活淬炼为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学图景。
现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但汉松和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子,开展了一场文学对谈,与大家共同探讨“乔伊斯与爱尔兰文学”。
话题首先从《尤利西斯》中嵌入的爱尔兰地理坐标开始。即便从未涉足爱尔兰,叶子却对小说中的霍斯角半岛印象深刻,指出此地在《尤利西斯》与《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双重意义——这里既是莫莉·布卢姆答应布卢姆求婚的浪漫地,那句决定性的“yes”成为乔伊斯笔下象征生命力的符号,也是《芬尼根的守灵夜》开篇承载爱尔兰历史的“思想发源地”。
但汉松则提及第三章斯蒂芬·迪达勒斯漫步的桑迪芒特海滩。在这段以“哲学迷宫”著称的章节中,青年主角目睹死狗,观察路人,串联起从亚里士多德到贝克莱的哲学思辨。“这是乔伊斯对读者的筛选,”但汉松表示,“唯有沉入斯蒂芬的思想世界,才能获得理解这部小说的密钥。”
难以逃避的都柏林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以考据般的精确还原了都柏林的城市细节,人们甚至可以拿这本书当作导览。为何乔伊斯一生力图逃避都柏林,写作却始终离不开这个原点?
叶子讲述了乔伊斯与都柏林的复杂羁绊。乔伊斯一生都在贫困中挣扎,即便《尤利西斯》出版后仍需靠借钱度日,拖家带口频繁租房迁居。青年时期他曾想过学医,甚至鲁莽地决定去巴黎用法语攻读医科。“他的前辈,比如王尔德、萧伯纳、叶芝都选择了伦敦,乔伊斯却偏要去往更具异国风情的欧洲大陆,先后旅居巴黎、的里雅斯特等地,刻意让自己处于‘既不在那里又不在这里’的边缘位置。”
在都柏林时,乔伊斯的创作之路布满荆棘,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1910年代的爱尔兰出版时,辗转数十家出版社,出版人理查兹以审查为由百般刁难,这让他心寒不已,决心远离都柏林开展文学事业。但他始终清醒地意识到“把握都柏林” 的重要性——他并非被动漂泊,而是主动选择不回归故土,却在小说中一遍遍重构这座城市,将其化为文学创作的精神原点。
出于对“爱尔兰文学被誉为世界最佳”这一现象的好奇,非英语专业出身的叶子,在南大开设DIY课程,带领学生探讨乔伊斯与爱尔兰文学前辈的复杂关系。她发现,乔伊斯在人际交往中近乎“不近人情”,尽管他曾获得很多前辈的提携,如叶芝早年在伦敦悉心照料初到异乡的乔伊斯,为其安排一日三餐、引荐出版商与作家 ,但乔伊斯并不领情。
叶芝的书信记录了一段颇具象征意义的对话:20岁的乔伊斯问39岁的叶芝年龄,当得知对方实际年龄后,他直言“你太老了,我们见面的时间太晚,我已无法影响你”。这段被双方共同印证的往事,反映出乔伊斯对文学传统的叛逆——他既从爱尔兰土壤汲取养分,又刻意挣脱本土话语的束缚,为其日后走向世界性写作埋下伏笔。
在但汉松看来,对乔伊斯而言,都柏林不仅是家乡,更是一个浓缩的“微型宇宙”。为精准还原这座城市,他曾购买都柏林黄册,从中了解啤酒商、猪肉铺等市井细节,以“人类志”般的严谨构建文学场景。他与母国的关系极为矛盾,宣称要在小说中“锻造民族尚未生成的良知”,笔下人物斯蒂芬·迪达勒斯更喊出“不奉祀”的叛逆宣言。他反感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复古主义倾向,认为那是从坟墓中刨出死去的文化,而非面向未来。
20世纪初的爱尔兰处于民族认同的十字路口,乔伊斯以近乎偏执的热情记录城市肌理,坚信“即便都柏林被时间销毁,也能通过《尤利西斯》复建”。他去世时爱尔兰文化官员未曾到场,数十年后“布卢姆日”却成为国家节日,印证了他以文学对抗时间的胜利。
但汉松指出,乔伊斯对过度本土化的创作保持警惕,而将《荷马史诗》作为《尤利西斯》的精神原型,小说第九章,斯蒂芬在图书馆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开展讲座,其实就是一种文学声明——他的文学之父是威廉·莎士比亚,一个英格兰人。这在当时被视为“背叛”,但乔伊斯以狂傲姿态突破了地域文化的束缚。
值得关注的是,乔伊斯的实验主义背离了爱尔兰老派的现实主义传统,却被贝克特等作家继承;而更多本土作家,如描写乡村小镇的创作者,则以现实主义笔触延续民族叙事。“若只读乔伊斯,会误以为爱尔兰只有大都市景观。”
一场意识流的交响乐
谈到《尤利西斯》这部小说与音乐的关系时,叶子介绍说,《尤利西斯》里的布卢姆认为每个棺材里都应该放一部电话,以防尸体还活着,他还认为应该用留声机来保存死者的声音。这是对声音的敏感,也是在想象声音的 “永生”。
乔伊斯一家都有着惊人的好嗓音,他自己年轻时也跟随都柏林最好的声乐老师学唱。 《尤利西斯》里面,斯蒂芬或许也可以成为一名职业歌手,他受到另一种职业的诱惑,受到英语之外另一种语言的诱惑。但他知道,只有牺牲自己的写作野心才能做到这一点。
带着这种感受读《尤利西斯》第十一章会发现,乔伊斯追溯了《奥德赛》里海妖塞壬的故事,塞壬的歌声是诱惑英雄的死亡陷阱,现实中都柏林酒吧的侍女,也是上半身如塞壬般美丽,吧台之下却是肮脏的裙子、鞋子和倒掉的酒瓶子。
这是关于音乐的一章——用语言创造音乐效果的特技。乔伊斯写了五个月,称它为“按照规则的赋格曲”。他极为大胆地去尝试用语言模仿音乐,同时,又不任由音乐控制写作。恰恰是在对音乐的模仿中,他揭示和部署了文字的力量。
但汉松表示,《尤利西斯》中这一章节严格按赋格曲结构创作,源于两方面的原因:沃尔特·佩特说,从艺术传统看,小说、诗歌、雕塑等所有艺术都渴望成为音乐,因为音乐是一种纯粹体验, 能够超越语言直接打动人,“无论你来自非洲还
是亚洲,懂与不懂中文、英语、德语,都可以被瓦格纳、贝多芬所感动”,正如乔治·斯坦纳在《文学与沉默》中强调,伟大的艺术都试图跳脱出所指和能指,走向音乐。
此外,乔伊斯写这本书时饱受眼疾折磨,青光眼手术让他长时间不能睁眼,对声音格外敏感,担心失去视力。斯蒂芬在第三章说“I close my eyes to see”,体现了试图通过声音超越视觉依赖,进入艺术自由王国的理念。加上他本人的音乐才华,音乐对他而言不仅是媒介,更是逃离文字有限性的艺术境界。这种感受源于他的肉身之痛。
看过大海,就不能假装没看过
在探讨爱尔兰文学为何在中国引发持续热潮时,叶子以《尤利西斯》为切入点,揭示了这部书背后的人性共鸣密码。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尤利西斯》,这是一个‘父亲寻找儿子’的故事。”叶子指出,小说主角布卢姆因丧子之痛对青年斯蒂芬产生父性关怀,形成现代版《奥德赛》的归家叙事 ——但不同于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杀退求婚者的英雄主义,乔伊斯笔下的布卢姆是位“被妻子背叛却不敢归家的丈夫”,他在都柏林街头的游荡,实则是对现代婚姻困境的隐喻性书写,在当代社会仍能激起读者对情感异化的共鸣。
这种对英雄主义的消解,暗合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精神转型——相较于美国文学中“一路向上”的商人巴比特,这个“敏锐古怪却充满温情” 的都柏林人,以其被忽视的生存状态,成为现代性语境下的典型人物。“乔伊斯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不被看见的人。”
《尤利西斯》虽作为送给妻子诺拉的结婚礼物,却因深邃的实验性让她只读了不到 10 页。但汉松以这一细节说明作品的先锋性——相较于海明威式可效仿的写作,乔伊斯的文本如同不可逾越的高峰,成为定义文学巅峰的“纪念碑”。在大学课堂上,但汉松从不直接讲授《尤利西斯》,而是以《都柏林人》中《死者》作为 “文学开胃菜”。他连续十余年带领新生阅读这个故事,“只要你想让自己更像人,乔伊斯就是重要的选择。”
“不必读完《尤利西斯》,只需让它暴露在生活中。” 但汉松称经典如同 X 射线,即便每月只读几页,也能潜移默化重塑文学品位。在短视频与AI写作泛滥的时代,这部“难书” 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坐标:“我已经看过大海,就不能假装没有看过。读过《尤利西斯》就再难容忍网文的浅白,它让你知道人性复杂性能写到多深,文学天花板在哪里。”那句“每个人书架上都该有一本《尤利西斯》”的广告词,恰是对这种精神辐射力的通俗诠释。
在浅阅读盛行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不少人担忧写作已死、严肃文学终将消亡。但汉松指出,人工智能或大语言模型擅长通过概率运算将一切转化为套路,复制诸如极简写作或穿越文学的叙事框架,这对以“独特性”为核心的真正文学而言是巨大灾难。他特别欣赏乔伊斯对语言独特性的坚守,据说乔伊斯每天几易其稿,闭眼推敲字句,这种不向速食文化妥协的写作,本质上是在追求机器无法模仿的风格,甚至可上升到人的存在层面。
但汉松以林棹的《潮汐图》为例,称其广受赞誉,正在于拒绝跟风当红的口语化或短句写作,用充满抵抗力的语言构建了难以轻易进入的文本世界。
他表示,若这类坚守独特性的文学消失或无人阅读,人类可能在精神进化链上大幅倒退——这些需要读者主动跨越语言门槛的作品,恰是对抗算法套路,保留“无法被算法定义的人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