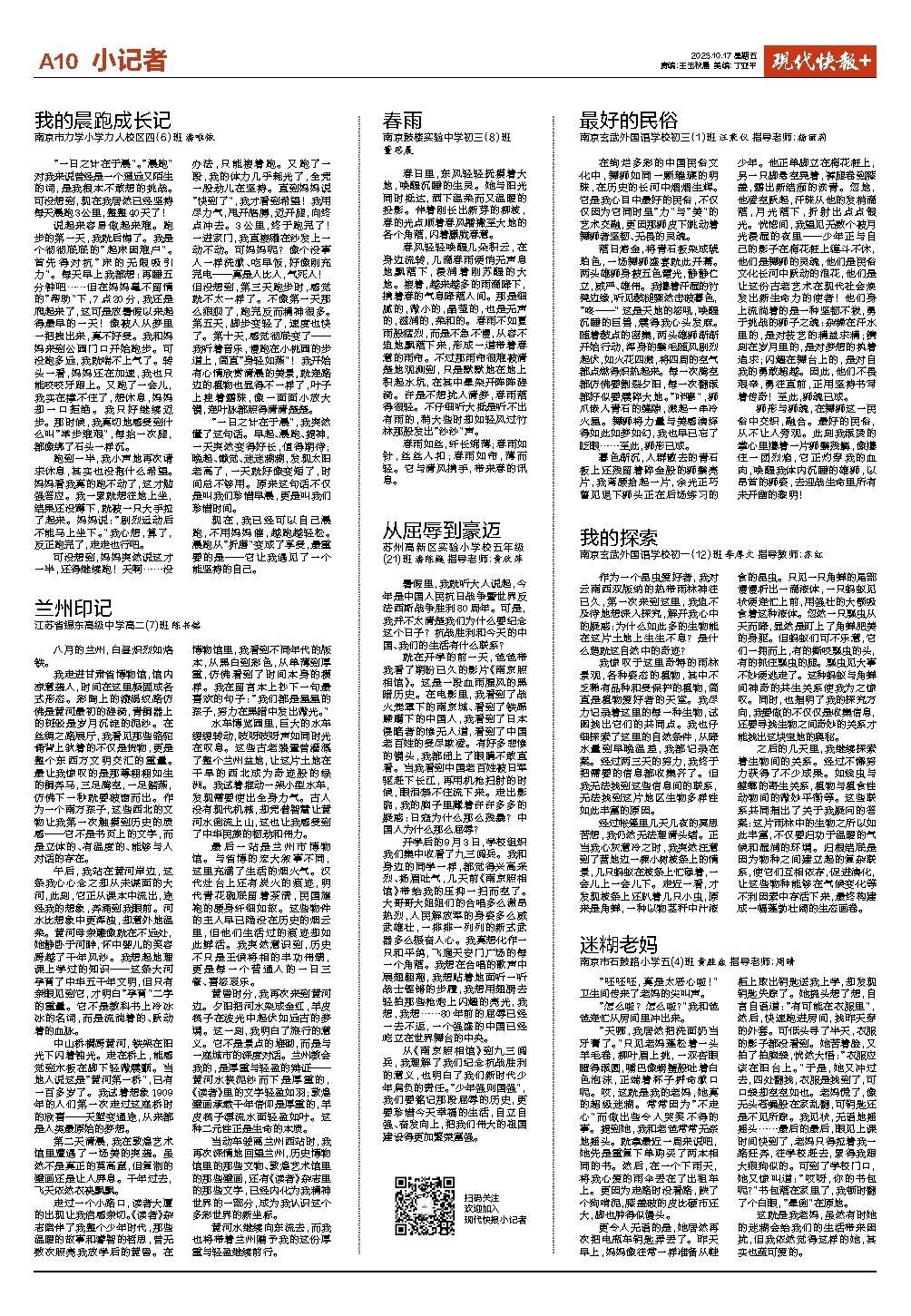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高二(7)班 陈书铭
八月的兰州,白昼炽烈如烙铁。
我走进甘肃省博物馆,馆内凉意袭人,时间在这里凝固成各式形态。彩陶上的漩涡纹路仿佛是黄河最初的涟漪,青铜器上的斑驳是岁月沉淀的泥沙。在丝绸之路展厅,我看见那些骆驼俑背上驮着的不仅是货物,更是整个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量。最让我惊叹的是那尊栩栩如生的铜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踏燕,仿佛下一秒就要破窗而出。作为一个南方孩子,这些西北的文物让我第一次触摸到历史的质感——它不是书页上的文字,而是立体的、有温度的、能够与人对话的存在。
午后,我站在黄河岸边,这条我心心念之却从未谋面的大河,此刻,它正从课本中流出,途经我的想象,奔涌到我眼前。河水比想象中更浑浊,却意外地温柔。黄河母亲雕像就在不远处,她静卧于河畔,怀中婴儿的笑容跨越了千年风沙。我想起地理课上学过的知识——这条大河孕育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但只有亲眼见到它,才明白“孕育”二字的重量。它不是教科书上冷冰冰的名词,而是流淌着的、跃动着的血脉。
中山桥横跨黄河,铁架在阳光下闪着钝光。走在桥上,能感觉到木板在脚下轻微震颤。当地人说这是“黄河第一桥”,已有一百多岁了。我试着想象1909年的人们第一次走过这座桥时的欣喜——天堑变通途,从来都是人类最原始的梦想。
第二天清晨,我在敦煌艺术馆里遭遇了一场美的突袭。虽然不是真正的莫高窟,但复制的壁画还是让人屏息。千年过去,飞天依然衣袂飘飘。
走过一个小路口,读者大厦的出现让我倍感亲切。《读者》杂志陪伴了我整个少年时代,那些温暖的故事和睿智的哲思,曾无数次照亮我放学后的黄昏。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不同年代的版本,从黑白到彩色,从单薄到厚重,仿佛看到了时间本身的模样。我在留言本上抄下一句最喜欢的句子:“我们都是星星的孩子,努力在黑暗中发出微光。”
水车博览园里,巨大的水车缓缓转动,吱呀吱呀声如同时光在叹息。这些古老装置曾灌溉了整个兰州盆地,让这片土地在干旱的西北成为奇迹般的绿洲。我试着推动一架小型水车,发现需要使出全身力气。古人没有现代机械,却凭借智慧让黄河水倒流上山,这也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韧劲和伟力。
最后一站是兰州市博物馆。与省博的宏大叙事不同,这里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汉代灶台上还有炭火的痕迹,明代青花碗底留着茶渍,民国旗袍的腰身纤细如故。这些物件的主人早已隐没在历史的烟云里,但他们生活过的痕迹却如此鲜活。我突然意识到,历史不只是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更是每一个普通人的一日三餐、喜怒哀乐。
黄昏时分,我再次来到黄河边。夕阳把河水染成金红,羊皮筏子在波光中起伏如远古的梦境。这一刻,我明白了旅行的意义。它不是景点的堆砌,而是与一座城市的深度对话。兰州教会我的,是厚重与轻盈的辩证——黄河水挟泥沙而下是厚重的,《读者》里的文字轻盈如羽;敦煌壁画承载千年信仰是厚重的,羊皮筏子漂流水面轻盈如叶。这种二元性正是生命的本质。
当动车驶离兰州西站时,我再次深情地回望兰州,历史博物馆里的那些文物、敦煌艺术馆里的那些壁画,还有《读者》杂志里的那些文字,已经内化为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成为我认识这个多彩世界的新坐标。
黄河水继续向东流去,而我也将带着兰州赠予我的这份厚重与轻盈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