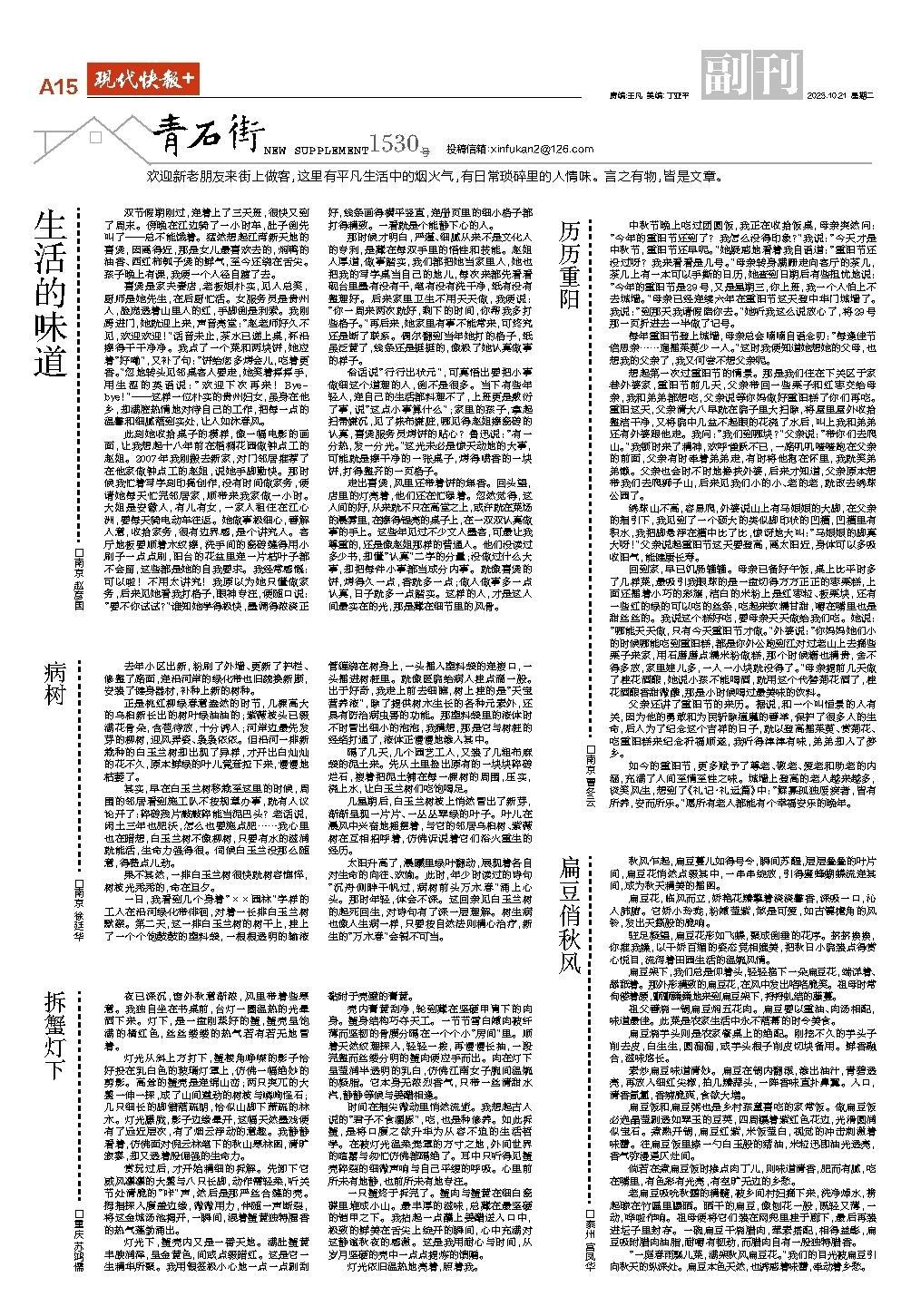□南京 赵彦国
双节假期刚过,连着上了三天班,很快又到了周末。傍晚在江边骑了一小时车,肚子倒先叫了——总不能饿着。猛然想起江湾新天地的喜煲,因离得近,那是女儿最喜欢去的,焖鸭的油香、西红柿瓠子煲的鲜气,至今还绕在舌尖。孩子晚上有课,我便一个人径自踱了去。
喜煲是家夫妻店,老板娘朴实,见人总笑,厨师是她先生,在后厨忙活。女服务员是贵州人,脸庞透着山里人的红,手脚倒是利索。我刚跨进门,她就迎上来,声音亮堂:“赵老师好久不见,欢迎欢迎!”话音未止,茶水已递上桌,杯沿擦得干干净净。我点了一个菜和两块饼,她应着“好嘞”,又补了句:“饼给您多烤会儿,吃着更香。”忽地转头见邻桌客人要走,她笑着挥挥手,用生涩的英语说:“欢迎下次再来!Bye-bye!”——这样一位朴实的贵州妇女,虽身在他乡,却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把每一点的温馨和细腻落到实处,让人如沐春风。
此刻她收拾桌子的模样,像一幅电影的画面,让我想起十八年前在梧桐花园做钟点工的赵姐。2007年我刚搬去新家,对门邻居推荐了在他家做钟点工的赵姐,说她手脚勤快。那时候我忙着写字刻印搞创作,没有时间做家务,便请她每天忙完邻居家,顺带来我家做一小时。大姐是安徽人,有儿有女,一家人租住在江心洲,要每天骑电动车往返。她做事极细心,善解人意,收拾家务,很有边界感,是个讲究人。客厅地板要顺着木纹擦,洗手间的瓷砖缝得用小刷子一点点刷,阳台的花盆里连一片枯叶子都不会留,这些都是她的自我要求。我经常感慨:可以啦!不用太讲究!我原以为她只懂做家务,后来见她看我打格子,眼神专注,便随口说:“要不你试试?”谁知她学得极快,墨调得浓淡正好,线条画得横平竖直,连册页里的细小格子都打得精致。一看就是个能静下心的人。
那时候才明白,严谨、细腻从来不是文化人的专利,是藏在每双手里的悟性和技能。赵姐人厚道,做事踏实,我们都把她当家里人,她也把我的写字桌当自己的地儿,每次来都先看看砚台里墨有没有干,笔有没有洗干净,纸有没有整理好。后来家里卫生不用天天做,我便说:“你一周来两次就好,剩下的时间,你帮我多打些格子。”再后来,她家里有事不能常来,可终究还是断了联系。偶尔翻到当年她打的格子,纸虽泛黄了,线条还是挺挺的,像极了她认真做事的样子。
俗话说“行行出状元”,可真悟出要把小事做细这个道理的人,倒不是很多。当下有些年轻人,连自己的生活都料理不了,上班更是敷衍了事,说“这点小事算什么”;家里的孩子,拿起扫帚嫌沉,见了抹布嫌脏,哪见得赵姐擦瓷砖的认真,喜煲服务员烤饼的贴心?鲁迅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光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能就是擦干净的一张桌子,烤得喷香的一块饼,打得整齐的一页格子。
走出喜煲,风里还带着饼的焦香。回头望,店里的灯亮着,他们还在忙碌着。忽然觉得,这人间的好,从来就不只在高堂之上,或许就在菜场的晨雾里,在擦得锃亮的桌子上,在一双双认真做事的手上。这些年见过不少文人墨客,可最让我尊重的,还是像赵姐那样的普通人。他们没读过多少书,却懂“认真”二字的分量;没做过什么大事,却把每件小事都当成分内事。就像喜煲的饼,烤得久一点,香就多一点;做人做事多一点认真,日子就多一点踏实。这样的人,才是这人间最实在的光,那是藏在细节里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