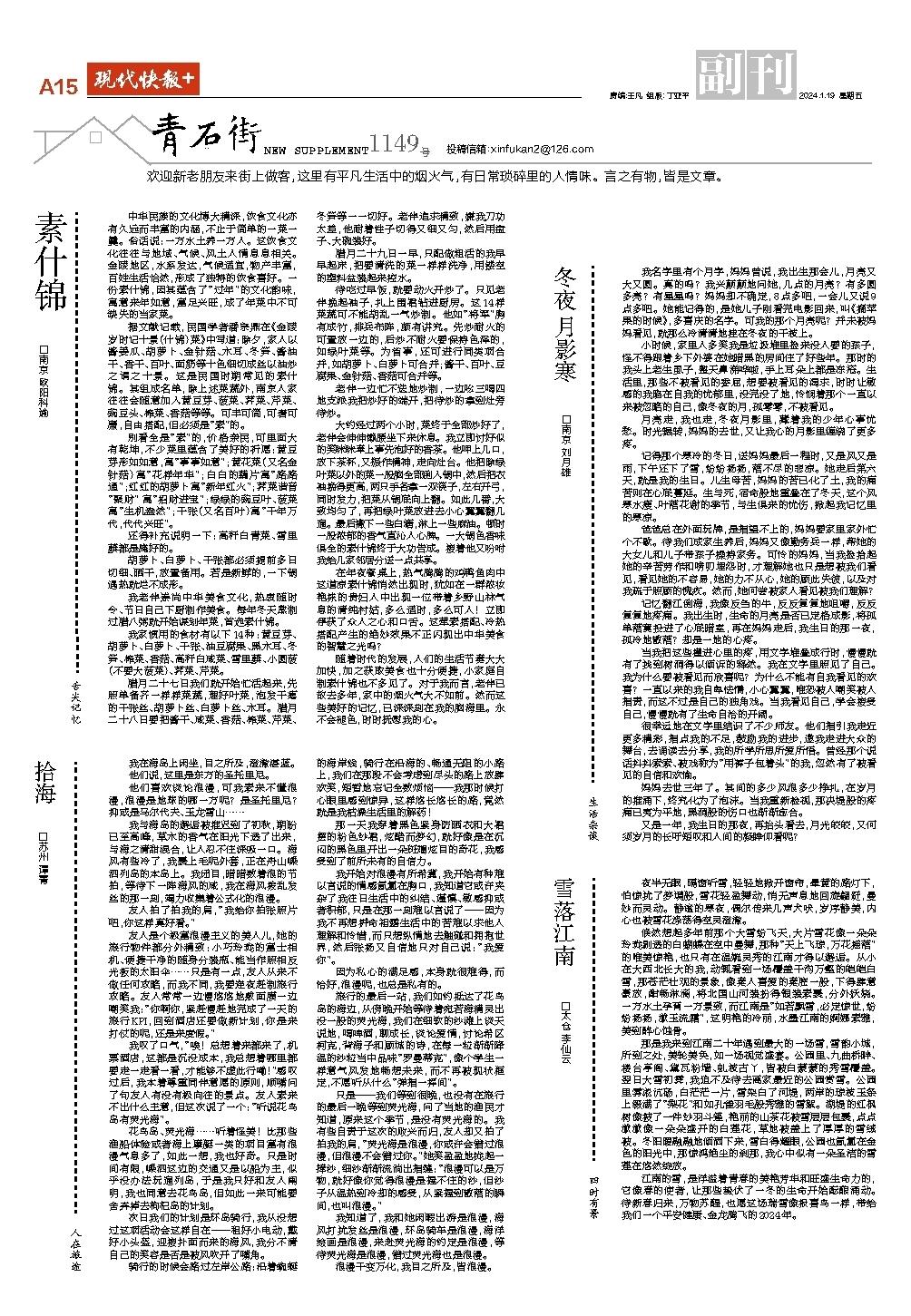□南京 刘月雄
我名字里有个月字,妈妈曾说,我出生那会儿,月亮又大又圆。真的吗?我兴颠颠地问她,几点的月亮?有多圆多亮?有星星吗?妈妈却不确定,8点多吧,一会儿又说9点多吧。她能记得的,是她儿子刚看完电影回来,叫《摘苹果的时候》,多喜庆的名字。可我的那个月亮呢?并未被妈妈看见,就那么冷清清地挂在冬夜的干枝上。
小时候,家里人多笑我是垃圾堆里捡来没人要的孩子,怪不得跟着乡下外婆在她暗黑的房间住了好些年。那时的我头上老生虱子,整天鼻涕哗啦,手上耳朵上都是冻疮。生活里,那些不被看见的委屈,想要被看见的渴求,时时让敏感的我陷在自我的忧郁里,没完没了地,怜悯着那个一直以来被忽略的自己,像冬夜的月,孤零零,不被看见。
月亮走,我也走,冬夜月影里,藏着我的少年心事忧愁。时光辗转,妈妈的去世,又让我心的月影里缠绕了更多疼。
记得那个寒冷的冬日,送妈妈最后一程时,又是风又是雨,下午还下了雪,纷纷扬扬,落不尽的悲凉。她走后第六天,就是我的生日。儿生母苦,妈妈的苦已化了土,我的痛苦则在心底蔓延。生与死,宿命般地重叠在了冬天,这个风寒水瘦、叶落花谢的季节,与生俱来的忧伤,掀起我记忆里的寒凉。
爸爸总在外面玩牌,是指望不上的,妈妈要家里家外忙个不歇。待我们成家生养后,妈妈又像勤务兵一样,帮她的大女儿和儿子带孩子操持家务。可怜的妈妈,当我捡拾起她的辛苦劳作和唠叨埋怨时,才理解她也只是想被我们看见,看见她的不容易,她的力不从心,她的顾此失彼,以及对我疏于照顾的愧疚。然而,她何尝被家人看见被我们理解?
记忆翻江倒海,我像反刍的牛,反反复复地咀嚼,反反复复地疼痛。我出生时,生命的月亮是否已定格成影,将孤单落寞投进了心底暗室,再在妈妈走后,我生日的那一夜,孤冷地散落?却是一地的心疼。
当我把这些撞进心里的疼,用文字堆叠成行时,慢慢就有了找到树洞得以倾诉的释然。我在文字里照见了自己。我为什么要被看见而欣喜呢?为什么不能有自我看见的欢喜?一直以来的我自卑怯懦,小心翼翼,唯恐被人嘲笑被人指责,而这不过是自己的独角戏。当我看见自己,学会接受自己,慢慢就有了生命自洽的开阔。
很幸运地在文字里结识了不少师友。他们指引我走近更多精彩,指点我的不足,鼓励我的进步,邀我走进大众的舞台,去诵读去分享,我的所学所思所爱所悟。曾经那个说话抖抖索索、被戏称为“用裤子包着头”的我,忽然有了被看见的自信和欢愉。
妈妈去世三年了。其间的多少风浪多少挣扎,在岁月的推涌下,终究化为了泡沫。当我重新检视,那决堤般的疼痛已夷为平地,黑洞般的伤口也渐渐愈合。
又是一年,我生日的那夜,再抬头看去,月光皎皎,又何须岁月的长吁短叹和人间的凝眸仰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