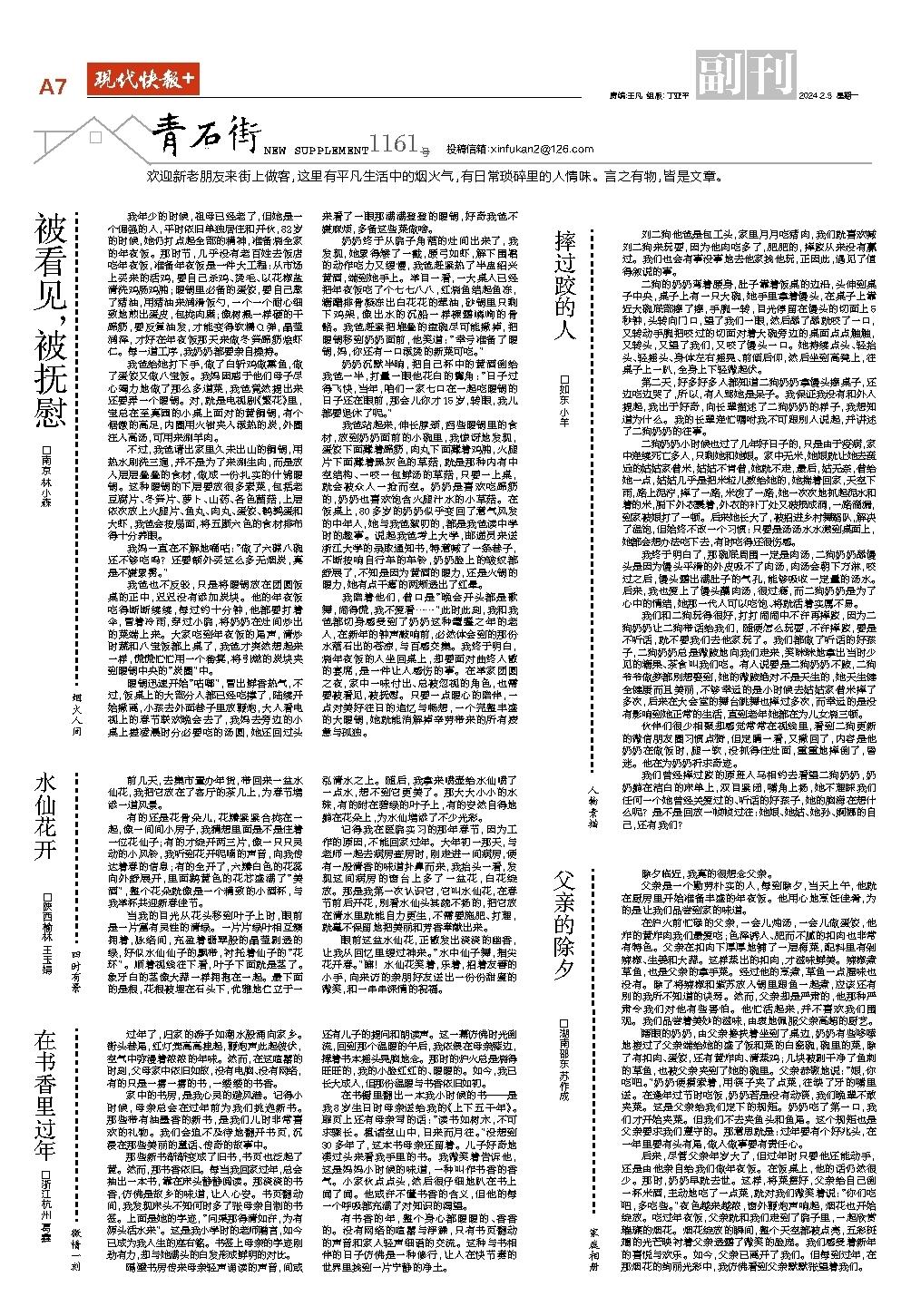□南京 林小森
烟火人间
我年少的时候,祖母已经老了,但她是一个倔强的人,平时依旧单独居住和开伙,82岁的时候,她仍打点起全部的精神,准备烧全家的年夜饭。那时节,几乎没有老百姓去饭店吃年夜饭,准备年夜饭是一件大工程:从市场上买来的活鸡,要自己杀鸡、烫毛、以花椒盐清洗鸡肠鸡肫;暖锅里必备的蛋饺,要自己熬了猪油,用猪油来润滑饭勺,一个一个耐心细致地煎出蛋皮,包拢肉糜;像树棍一样硬的干蹄筋,要反复油发,才能变得软糯Q弹,晶莹润泽,才好在年夜饭那天来做冬笋蹄筋烩虾仁。每一道工序,我奶奶都要亲自操持。
我爸给她打下手,做了白斩鸡做熏鱼,做了蛋饺又做八宝饭。我妈困惑于他们母子尽心竭力地做了那么多道菜,我爸竟然提出来还要弄一个暖锅。对,就是电视剧《繁花》里,宝总在至真园的小桌上面对的黄铜锅,有个倨傲的高足,内圈用火钳夹入滚热的炭,外圈注入高汤,可用来涮羊肉。
不过,我爸请出家里久未出山的铜锅,用热水刷洗三遍,并不是为了来涮生肉,而是放入层层叠叠的食材,做成一份扎实的什锦暖锅。这种暖锅的下层要放很多素菜,包括老豆腐片、冬笋片、萝卜、山药、各色菌菇,上层依次放上火腿片、鱼丸、肉丸、蛋饺、鹌鹑蛋和大虾,我爸会按扇面,将五颜六色的食材排布得十分养眼。
我妈一直在不解地嘀咕:“做了六碟八碗还不够吃吗?还要额外买这么多无烟炭,真是不嫌累赘。”
我爸也不反驳,只是将暖锅放在团圆饭桌的正中,迟迟没有添加炭块。他的年夜饭吃得断断续续,每过约十分钟,他都要打着伞,冒着冷雨,穿过小院,将奶奶在灶间炒出的菜端上来。大家吃到年夜饭的尾声,清炒时蔬和八宝饭都上桌了,我爸才突然想起来一样,慌慌忙忙用一个畚箕,将引燃的炭块夹到暖锅中央的“炭圈”中。
暖锅迅速开始“咕嘟”,冒出鲜香热气,不过,饭桌上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吃撑了,陆续开始撤离,小孩去外面巷子里放鞭炮,大人看电视上的春节联欢晚会去了,我妈去旁边的小桌上搓凌晨时分必要吃的汤圆,她还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那满满登登的暖锅,好奇我爸不嫌麻烦,多备这些菜做啥。
奶奶终于从院子角落的灶间出来了,我发现,她累得矮了一截,腰弓如虾,解下围裙的动作吃力又缓慢,我爸赶紧热了半盅绍兴黄酒,端到她手上。举目一看,一大桌人已经把年夜饭吃了个七七八八,红烧鱼结起鱼冻,糖醋排骨凝冻出白花花的荤油,砂锅里只剩下鸡架,像出水的沉船一样裸露嶙峋的骨骼。我爸赶紧把堆叠的盘碗尽可能撤掉,把暖锅移到奶奶面前,他笑道:“幸亏准备了暖锅,妈,你还有一口滚烫的新菜可吃。”
奶奶沉默半晌,把自己杯中的黄酒倒给我爸一半,打量一眼他花白的鬓角:“日子过得飞快,当年,咱们一家七口在一起吃暖锅的日子还在眼前,那会儿你才15岁,转眼,我儿都要退休了呢。”
我爸站起来,伸长脖颈,舀些暖锅里的食材,放到奶奶面前的小碗里,我惊讶地发现,蛋饺下面藏着蹄筋,肉丸下面藏着鸡肫,火腿片下面藏着黑灰色的草菇,就是那种内有中空结构、一咬一包鲜汤的草菇,只要一上桌,就会被众人一抢而空。奶奶是喜欢吃蹄筋的,奶奶也喜欢饱含火腿汁水的小草菇。在饭桌上,80多岁的奶奶似乎变回了意气风发的中年人,她与我爸絮叨的,都是我爸读中学时的趣事。说起我爸考上大学,邮递员来送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特意喊了一条巷子,不断按响自行车的车铃,奶奶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不知是因为黄酒的暖力,还是火锅的暖力,她有点干瘪的两颊透出了红晕。
我陪着他们,借口是“晚会开头都是歌舞,闹得慌,我不爱看……”此时此刻,我和我爸都切身感受到了奶奶这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新年的钟声敲响前,必然体会到的那份水落石出的苍凉,与百感交集。我终于明白,烧年夜饭的人坐回桌上,却要面对曲终人散的宴席,是一件让人感伤的事。在举家团圆之夜,家中一味付出、总被忽视的角色,也需要被看见,被抚慰。只要一点暖心的陪伴,一点对美好往日的追忆与畅想,一个完整丰盛的大暖锅,她就能消解掉辛劳带来的所有疲惫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