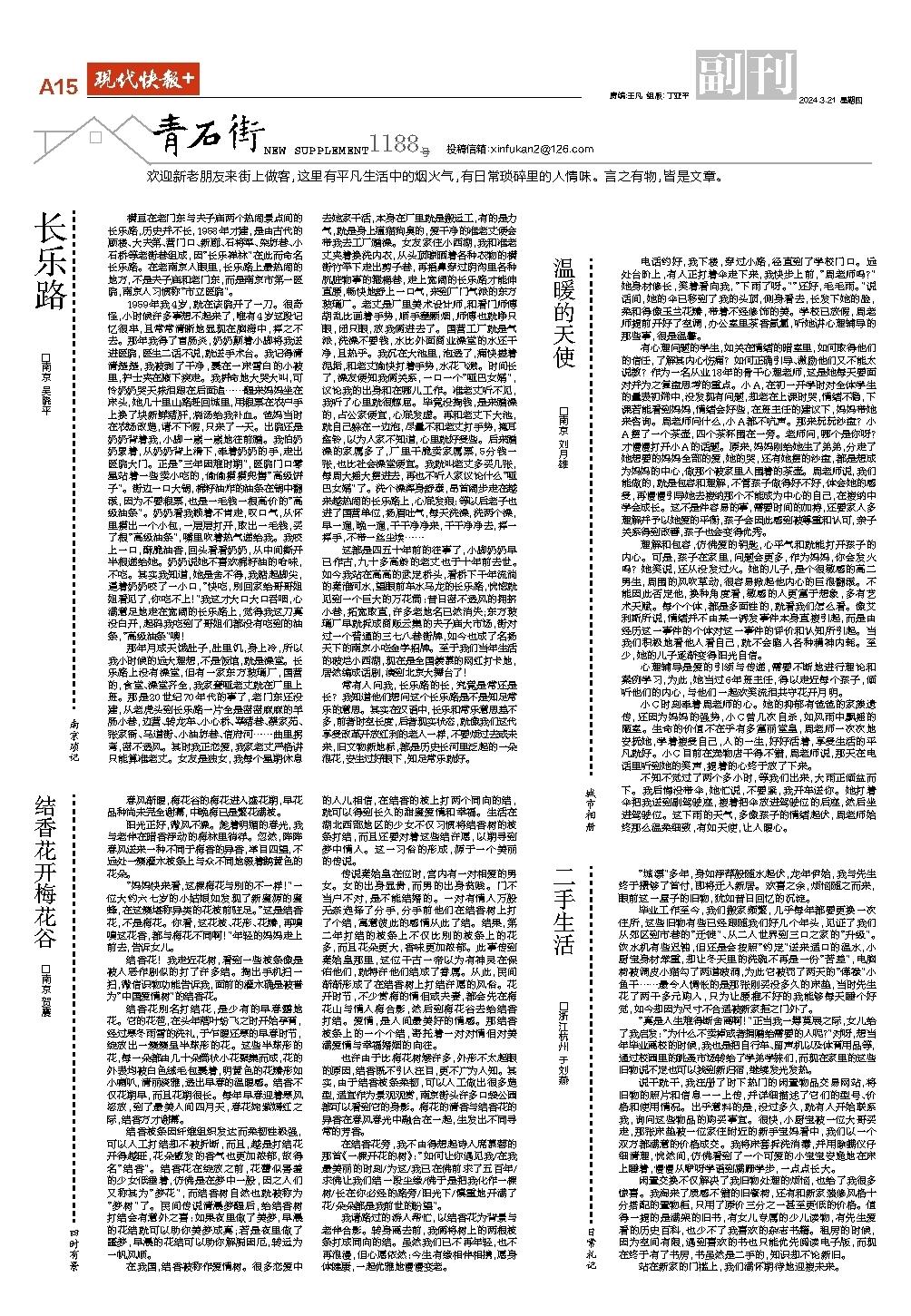□南京 吴晓平
横亘在老门东与夫子庙两个热闹景点间的长乐路,历史并不长,1958年才建,是由古代的顾楼、大夫第、营门口、新廊、石将军、染坊巷、小石桥等老街巷组成,因“长乐禅林”在此而命名长乐路。在老南京人眼里,长乐路上最热闹的地方,不是夫子庙和老门东,而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人习惯称“市立医院”。
1959年我4岁,就在该院开了一刀。很奇怪,小时候许多事想不起来了,唯有4岁这段记忆很牢,且常常清晰地显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那年我得了盲肠炎,奶奶颠着小脚将我送进医院,医生二话不说,就送手术台。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被剥了干净,裹在一床雪白的小被里,护士夹在腋下疾走。我拼命地大哭大叫,可怜奶奶哭天抹泪跟在后面追……醒来妈妈坐在床头,她几十里山路赶回城里,用粮票在农户手上换了块新鲜猪肝,烧汤给我补血。爸妈当时在农场改造,请不下假,只来了一天。出院还是奶奶背着我,小脚一崴一崴地往前蹭。我怕奶奶累着,从奶奶背上滑下,牵着奶奶的手,走出医院大门。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医院门口零星站着一些卖小吃的,偷偷摸摸兜售“高级饼子”。街边一口大锅,棉籽油炸的油条在锅中翻滚,因为不要粮票,也是一毛钱一根高价的“高级油条”。奶奶看我赖着不肯走,叹口气,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包,一层层打开,取出一毛钱,买了根“高级油条”,嘴里吹着热气递给我。我咬上一口,酥脆油香,回头看看奶奶,从中间撕开半根递给她。奶奶说她不喜欢棉籽油的呛味,不吃。其实我知道,她是舍不得,我踮起脚尖,逼着奶奶咬了一小口,“快吃,别回家给哥哥姐姐看见了,你吃不上!”我这才大口大口吞咽,心满意足地走在宽阔的长乐路上,觉得我这刀真没白开,起码我吃到了哥姐们都没有吃到的油条,“高级油条”噢!
那年月成天饿肚子,肚里饥,身上冷,所以我小时候的远大理想,不是饭馆,就是澡堂。长乐路上没有澡堂,但有一家东方玻璃厂,国营的,食堂、澡堂齐全,我家聋哑老丈就在厂里上班。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了,老门东还没建,从老虎头到长乐路一片全是密密麻麻的羊肠小巷,边营、转龙车、小心桥、宰猪巷、蔡家苑、张家衙、马道街、小油坊巷、信府河……曲里拐弯,密不透风。其时我正恋爱,我家老丈严格讲只能算准老丈。女友是独女,我每个星期休息去她家干活,本身在厂里就是搬运工,有的是力气,就是身上瘟猫狗臭的,爱干净的准老丈便会带我去工厂蹭澡。女友家住小西湖,我和准老丈夹着换洗内衣,从头顶晾晒着各种衣物的横街竹竿下走出剪子巷,再捂鼻穿过阴沟里各种肮脏物事的箍桶巷,走上宽阔的长乐路才能伸直腰,畅快地舒上一口气,来到厂门气派的东方玻璃厂。老丈是厂里美术设计师,和看门师傅胡乱比画着手势,顺手塞颗烟,师傅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放我俩进去了。国营工厂就是气派,洗澡不要钱,水比外面商业澡堂的水还干净,且热乎。我沉在大池里,泡透了,痛快搓着泥垢,和老丈愉快打着手势,水花飞溅。时间长了,澡友便知我俩关系,一口一个“哑巴女婿”,议论我的出身和在哪儿工作。准老丈听不见,我听了心里就很憋屈。毕竟没掏钱,是来蹭澡的,占公家便宜,心底发虚。再和老丈下大池,就自己躲在一边泡,尽量不和老丈打手势,掩耳盗铃,以为人家不知道,心里就好受些。后来蹭澡的家属多了,厂里干脆卖家属票,5分钱一张,也比社会澡堂便宜。我就叫老丈多买几张,每周大摇大摆进去,再也不听人家议论什么“哑巴女婿”了。洗个澡浑身舒泰,昂首阔步走在越来越热闹的长乐路上,心底发狠:等以后老子也进了国营单位,扬眉吐气,每天洗澡,洗两个澡,早一遍,晚一遍,干干净净来,干干净净去,挥一挥手,不带一丝尘埃……
这都是四五十年前的往事了,小脚奶奶早已作古,九十多高龄的老丈也于十年前去世。如今我站在高高的武定桥头,看桥下千年流淌的秦淮河水,望眼前车水马龙的长乐路,恍惚就见到一个巨大的万花筒:昔日密不透风的拥挤小巷,拓宽取直,许多老地名已然消失;东方玻璃厂早就拆成商贩云集的夫子庙大市场,街对过一个普通的三七八巷街牌,如今也成了名扬天下的南京小吃金字招牌。至于我们当年生活的破烂小西湖,现在是全国羡慕的网红打卡地,居然编成话剧,演到北京大舞台了!
常有人问我,长乐路的长,究竟是常还是长?我知道他们想问这个长乐路是不是知足常乐的意思。其实在汉语中,长乐和常乐意思差不多,前者时空长度,后者现实状态,就像我们这代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老人一样,不要烦过去或未来,旧文物新地标,都是历史长河里泛起的一朵浪花,安生过好眼下,知足常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