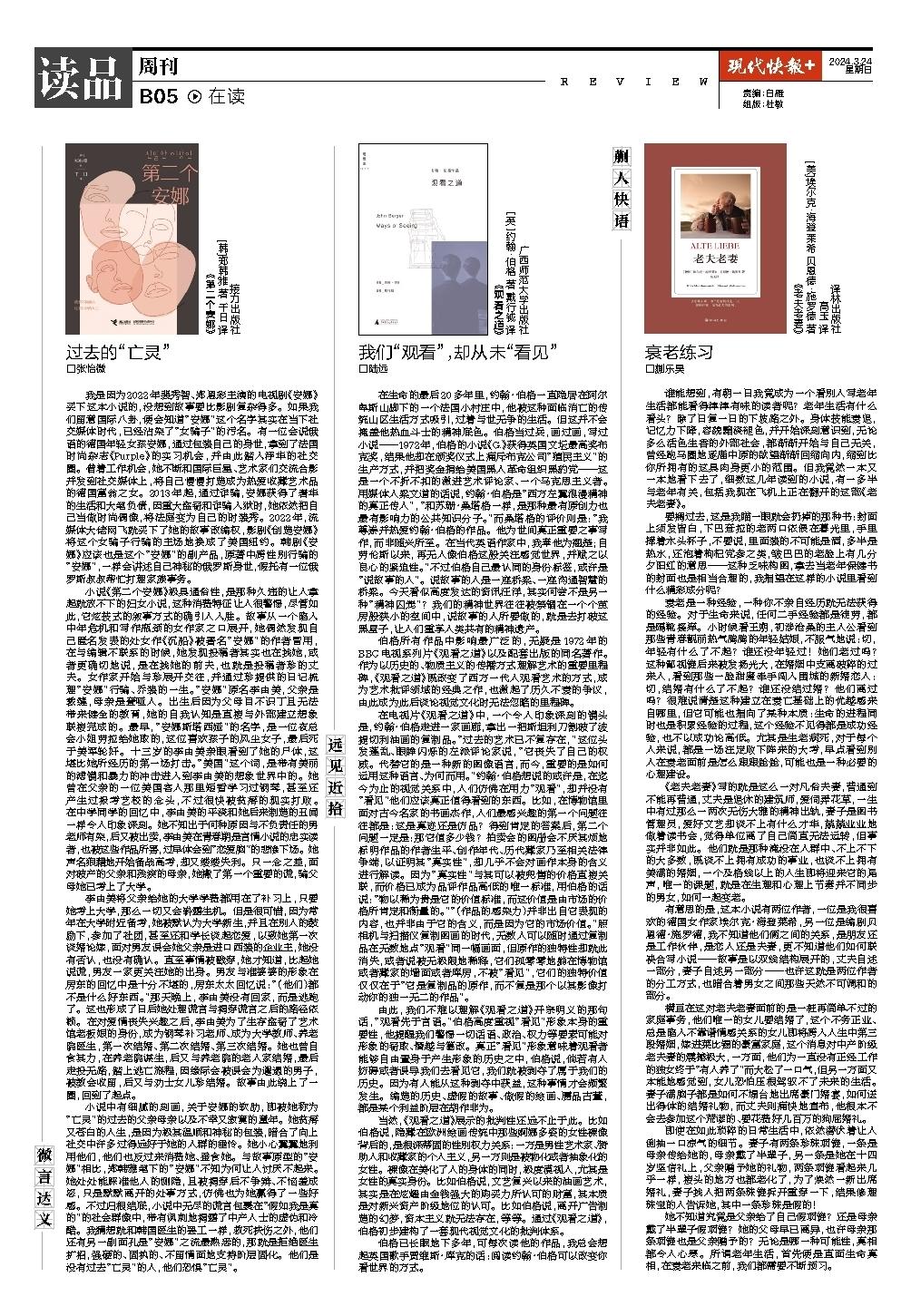□张怡微
我是因为2022年裴秀智、郑恩彩主演的电视剧《安娜》买下这本小说的,没想到故事要比影剧复杂得多。如果我们留意国际八卦,便会知道“安娜”这个名字其实在当下社交媒体时代,已经沾染了“女骗子”的污名。有一位会说俄语的德国年轻女孩安娜,通过包装自己的身世,拿到了法国时尚杂志《Purple》的实习机会,并由此踏入浮华的社交圈。借着工作机会,她不断和国际巨星、艺术家们交流合影并发到社交媒体上,将自己慢慢打造成为热爱收藏艺术品的德国富翁之女。2013年起,通过诈骗,安娜获得了奢华的生活和大笔负债,因重大盗窃和诈骗入狱时,她依然把自己当做时尚偶像,将法庭变为自己的时装秀。2022年,流媒体大佬网飞就买下了她的故事改编权,影剧《创造安娜》将这个女骗子行骗的主场地换成了美国纽约。韩剧《安娜》应该也是这个“安娜”的副产品,原著中跨性别行骗的“安娜”,一样会讲述自己神秘的俄罗斯身世,假托有一位俄罗斯叔叔帮忙打理家族事务。
小说《第二个安娜》极具通俗性,是那种久违的让人拿起就放不下的妇女小说,这种消费特征让人很警惕,尽管如此,它炫技式的叙事方式的确引人入胜。故事从一个陷入中年危机和写作瓶颈的女作家之口展开,她偶然发现自己匿名发表的处女作《沉船》被署名“安娜”的作者冒用,在与编辑不联系的时候,她发现投稿者其实也在找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找她的前夫,也就是投稿者珍的丈夫。女作家开始与珍展开交往,并通过珍提供的日记梳理“安娜”行骗、乔装的一生。“安娜”原名李由美,父亲是裁缝,母亲是聋哑人。出生后因为父母目不识丁且无法带来健全的教育,她的自我认知是直接与外部建立想象联接完成的。最早,“安娜斯塔西娅”的名字,是一位夜总会小姐劳拉给她取的,这位喜欢孩子的风尘女子,最后死于美军轮奸。十三岁的李由美亲眼看到了她的尸体,这堪比她所经历的第一场打击。“美国”这个词,是带有美丽的滤镜和暴力的冲击进入到李由美的想象世界中的。她曾在父亲的一位美国客人那里短暂学习过钢琴,甚至还产生过报考艺校的念头,不过很快被贫瘠的现实打败。在中学同学的回忆中,李由美的平淡和她后来制造的丑闻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她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与不负责任的男老师有染,后又被出卖,李由美在青春期是言情小说的忠实读者,也被这些作品所害,过早体会到“恋爱脑”的悲惨下场。她声名狼藉地开始备战高考,却又缕缕失利。只一念之差,面对破产的父亲和残疾的母亲,她撒了第一个重要的谎,骗父母她已考上了大学。
李由美将父亲给她的大学学费都用在了补习上,只要她考上大学,那么一切又会崭露生机。但是很可惜,因为常年在大学附近备考,她被默认为大学新生,并且在别人的鼓励下,参加了社团,甚至还和学长谈起恋爱,以致她第一次谈婚论嫁,面对男友误会她父亲是进口西装的企业主,她没有否认,也没有确认。直至事情被戳穿,她才知道,比起她说谎,男友一家更关注她的出身。男友与准婆婆的形象在房东的回忆中是十分不堪的,房东太太回忆说:“(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天晚上,李由美没有回家,而是逃跑了。这也形成了日后她处理谎言与揭穿谎言之后的路径依赖。在对爱情丧失兴趣之后,李由美为了生存盗窃了艺术馆老板娘的身份,成为钢琴补习老师、成为大学教师、养老院医生,第一次结婚、第二次结婚、第三次结婚。她也曾自食其力,在养老院谋生,后又与养老院的老人家结婚,最后走投无路,踏上逃亡旅程,因缘际会被误会为邋遢的男子,被教会收留,后又与劝士女儿珍结婚。故事由此绕上了一圈,回到了起点。
小说中有细腻的刻画,关于安娜的软肋,即被她称为“亡灵”的过去的父亲母亲以及不幸又寂寞的童年。她贫瘠又苍白的人生,是因为极其温顺和神秘的包装,暗合了向上社交中许多过得远好于她的人群的垂怜。她小心翼翼地利用他们,他们也反过来消费她、蚕食她。与故事原型的“安娜”相比,郑韩雅笔下的“安娜”不知为何让人讨厌不起来。她处处能踩准他人的恻隐,且被揭穿后不争辩、不恼羞成怒,只是默默离开的处事方式,仿佛也为她赢得了一些好感。不过归根结底,小说中无尽的谎言包裹在“假如我是真的”的社会群像中,带有讽刺地揭露了中产人士的虚伪和冷酷。我猜想就和韩国医生的罢工一样,救死扶伤之外,他们还有另一副面孔是“安娜”之流最熟悉的,那就是拒绝医生扩招,强硬的、固执的、不留情面地支持阶层固化。他们是没有过去“亡灵”的人,他们恐惧“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