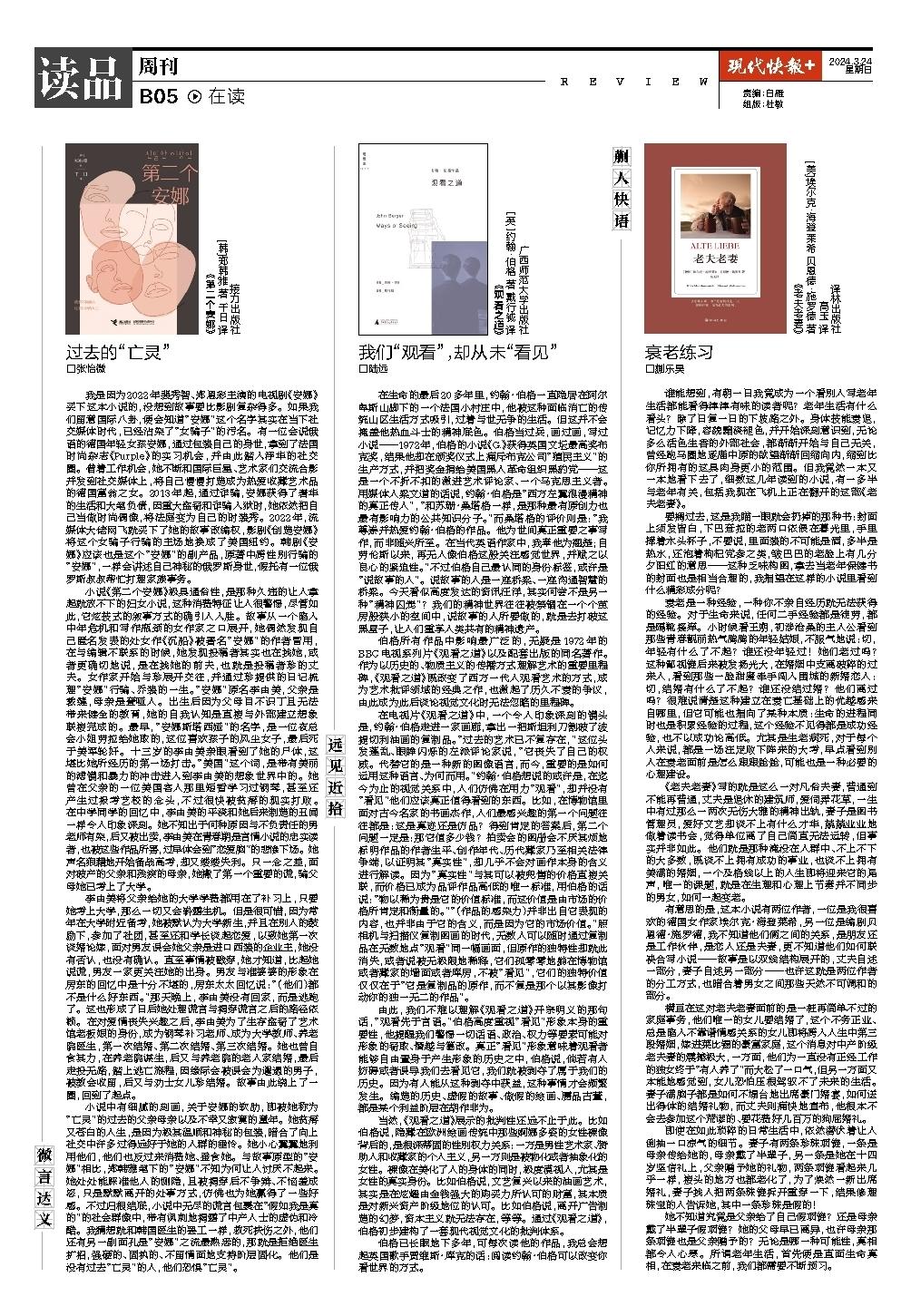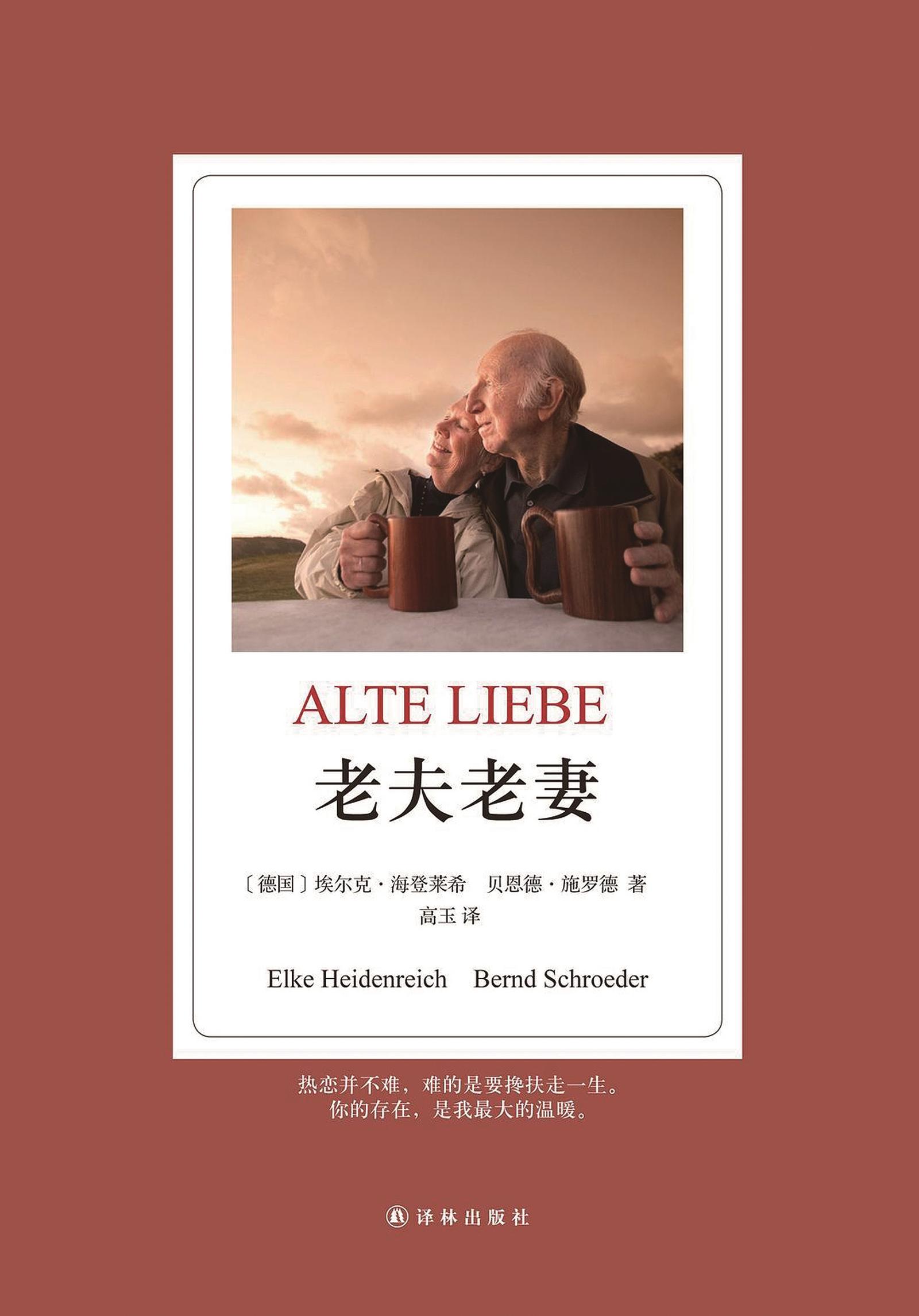□蒯乐昊
谁能想到,有朝一日我竟成为一个看别人写老年生活都能看得津津有味的读者呢?老年生活有什么看头?除了日复一日的下坡路之外。身体技能衰退,记忆力下降,容貌黯淡褪色,并开始深刻意识到,无论多么活色生香的外部社会,都渐渐开始与自己无关,曾经跑马圈地逐鹿中原的欲望渐渐回缩向内,缩到比你所拥有的这具肉身更小的范围。但我竟然一本又一本地看下去了,细数这几年读到的小说,有一多半与老年有关,包括我现在飞机上正在翻开的这部《老夫老妻》。
要搁过去,这是我瞄一眼就会扔掉的那种书:封面上须发皆白,下巴耷拉的老两口依偎在暮光里,手里捧着木头杯子,不要说,里面装的不可能是酒,多半是热水,还泡着枸杞党参之类,皱巴巴的老脸上有几分夕阳红的意思——这种乏味构图,拿去当老年保健书的封面也是相当合理的,我指望在这样的小说里看到什么精彩成分呢?
衰老是一种经验,一种你不亲自经历就无法获得的经验。对于生命来说,任何二手经验都是徒劳,都是隔靴搔痒。小时候看王朔,初涉沧桑的主人公看到那些青春靓丽热气腾腾的年轻姑娘,不服气地说:切,年轻有什么了不起?谁还没年轻过!她们老过吗?这种鄙视链后来被发扬光大,在婚姻中支离破碎的过来人,看到那些一脸甜蜜牵手闯入围城的新婚恋人:切,结婚有什么了不起?谁还没结过婚?他们离过吗?很难说清楚这种建立在衰亡基础上的优越感来自哪里,但它可能也指向了某种本质:生命的进程同时也是积累经验的过程,这个经验不见得都是成功经验,也不以成功论高低。尤其是生老病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注定败下阵来的大考,早点看到别人在衰老面前是怎么踉踉跄跄,可能也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建设。
《老夫老妻》写的就是这么一对凡俗夫妻,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丈夫是退休的建筑师,爱伺弄花草,一生中有过那么一两次无伤大雅的精神出轨,妻子是图书管理员,爱好文艺却谈不上有什么才华,兢兢业业地做着读书会,觉得单位离了自己简直无法运转,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就是那种淹没在人群中、不上不下的大多数,既谈不上拥有成功的事业,也谈不上拥有美满的婚姻,一个及格线以上的人生即将迎来它的尾声,唯一的课题,就是在生理和心理上节奏并不同步的男女,如何一起变老。
有意思的是,这本小说有两位作者,一位是我很喜欢的德国女作家埃尔克·海登莱希,另一位是编剧贝恩德·施罗德,我不知道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是朋友还是工作伙伴,是恋人还是夫妻,更不知道他们如何联袂合写小说——故事是以双线结构展开的,丈夫自述一部分,妻子自述另一部分——也许这就是两位作者的分工方式,也暗合着男女之间那些天然不可调和的部分。
横亘在这对老夫老妻面前的是一桩再简单不过的家庭事务,他们唯一的女儿要结婚了,这个不务正业、总是陷入不靠谱情感关系的女儿即将跨入人生中第三段婚姻,嫁进莱比锡的豪富家庭,这个消息对中产阶级老夫妻的震撼极大,一方面,他们为一直没有正经工作的独女终于“有人养了”而大松了一口气,但另一方面又本能地感觉到,女儿恐怕压根驾驭不了未来的生活。妻子满脑子都是如何不塌台地出席豪门婚宴,如何送出得体的结婚礼物,而丈夫则痛快地宣布,他根本不会去参加这个荒谬的、要花费好几百万的狗屁婚礼。
即使在如此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依然潜伏着让人倒抽一口凉气的细节。妻子有两条珍珠项链,一条是母亲传给她的,母亲戴了半辈子,另一条是她在十四岁坚信礼上,父亲赠予她的礼物,两条项链看起来几乎一样,接头的地方也都老化了,为了焕然一新出席婚礼,妻子找人把两条珠链拆开重穿一下,结果修理珠宝的人告诉她,其中一条珍珠是假的!
她不知道究竟是父亲给了自己假项链?还是母亲戴了半辈子假项链?她的父母早已离异,也许母亲那条项链也是父亲赠予的?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真相都令人心寒。所谓老年生活,首先便是直面生命真相,在衰老来临之前,我们都需要不断预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