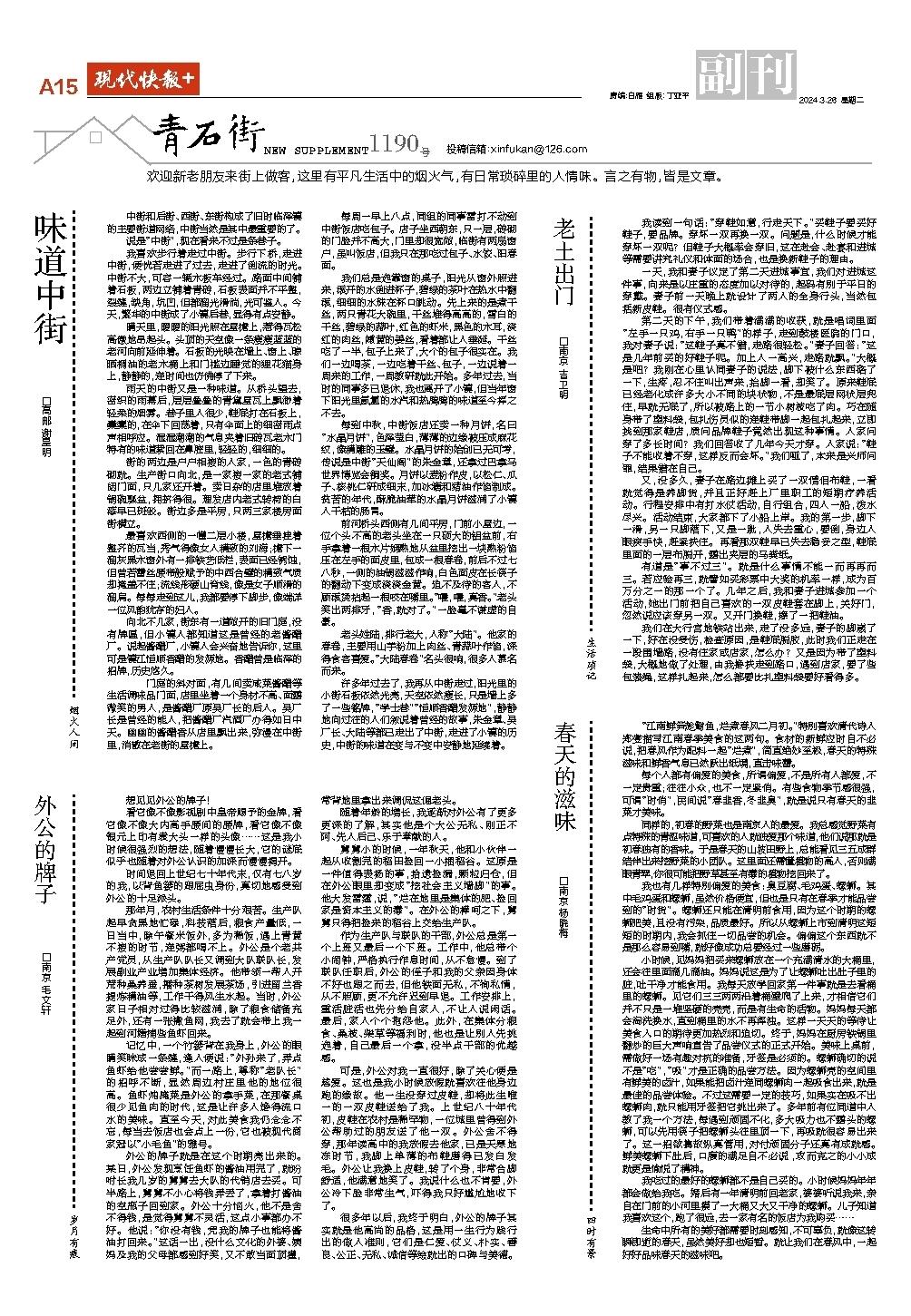□高邮 谢星明
中街和后街、西街、东街构成了旧时临泽镇的主要街道网络,中街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了。
说是“中街”,现在看来不过是条巷子。
我喜欢步行着走过中街。步行下桥,走进中街,便恍若走进了过去,走进了倒流的时光。中街不大,可容一辆木板车经过。路面中间铺着石板,两边立铺着青砖,石板表面并不平整,裂缝,缺角,坑凹,但都溜光滑淌,光可鉴人。今天,繁华的中街成了小镇后巷,显得有点安静。
晴天里,暖暖的阳光照在屋檐上,惹得瓦松高傲地昂起头。头顶的天空像一条瘦瘦蓝蓝的老河向前延伸着。石板的光映在墙上、窗上、晾晒桐油的老木桶上和门槛边睡觉的狸花猫身上,静静的,连时间也仿佛停了下来。
雨天的中街又是一种味道。从桥头望去,密织的雨幕后,层层叠叠的青黛屋瓦上飘渺着轻柔的烟雾。巷子里人很少,鞋底打在石板上,橐槖的,在伞下回荡着,只有伞面上的细密雨点声相呼应。湿湿潮潮的气息夹着旧砖瓦老木门特有的味道萦回在鼻腔里,轻轻的,细细的。
街的两边是户户相接的人家,一色的青砖砌就。生产街口向北,是一家接一家的老式铺闼门面,只几家还开着。卖日杂的店里堆放着锅碗瓢盆,拥挤得很。理发店内老式转椅的白漆早已斑驳。街边多是平房,只两三家楼房面街横立。
最喜欢西侧的一幢二层小楼,屋檐垂挂着整齐的瓦当,秀气得像女人精致的刘海;檐下一溜灰黑木窗外有一排铁艺低栏,表面已经锈蚀,但曾若蕾丝腰带般赋予的中西合璧的精致气质却掩盖不住;流线形硬山脊线,像是女子顺滑的溜肩。每每走到这儿,我都要停下脚步,像端详一位风韵犹存的妇人。
向北不几家,街东有一道敞开的旧门庭,没有牌匾,但小镇人都知道这是曾经的老酱醋厂。说起酱醋厂,小镇人会兴奋地告诉你,这里可是镇江恒顺香醋的发源地。香醋曾是临泽的招牌,历史悠久。
门庭的斜对面,有几间卖咸菜酱醋等生活调味品门面,店里坐着一个身材不高、面露微笑的男人,是酱醋厂原吴厂长的后人。吴厂长是曾经的能人,把酱醋厂汽酒厂办得如日中天。幽幽的酱醋香从店里飘出来,弥漫在中街里,消散在老街的屋檐上。
每周一早上八点,同组的同事雷打不动到中街饭店吃包子。店子坐西朝东,只一层,砖砌的门脸并不高大,门里却很宽敞,临街有两扇窗户,虽叫饭店,但我只在那吃过包子、水饺、阳春面。
我们总是选靠窗的桌子,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滚开的水倒进杯子,碧绿的茶叶在热水中翻滚,细细的水珠在杯口跳动。先上来的是煮干丝,两只青花大碗里,干丝堆得高高的,雪白的干丝,碧绿的蒜叶,红色的虾米,黑色的木耳,淡红的肉丝,嫩黄的姜丝,看着都让人垂涎。干丝吃了一半,包子上来了,大个的包子很实在。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吃着干丝、包子,一边说着一周来的工作,一周教研就此开始。多年过去,当时的同事多已退休,我也离开了小镇,但当年窗下阳光里氤氲的水汽和热腾腾的味道至今挥之不去。
每到中秋,中街饭店还卖一种月饼,名曰“水晶月饼”,色泽莹白,薄薄的边缘被压成麻花纹,像精雕的玉璧。水晶月饼的始创已无可考,传说是中街“天仙阁”的朱金章,还拿过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铜奖。月饼以麦粉作皮,以松仁、瓜子、核桃仁研成细末,加冰糖和猪油作馅制成。贫苦的年代,酥脆油荤的水晶月饼滋润了小镇人干枯的肠胃。
前河桥头西侧有几间平房,门前小屋边,一位个头不高的老头坐在一只硕大的铝盆前,右手拿着一根木片娴熟地从盆里挖出一块熟粉馅压在左手的面皮里,包成一根春卷,前后不过七八秒,一侧的油锅滋滋作响,白色面皮在长筷子的翻动下变成淡淡金黄。迫不及待的客人,不顾滚烫拈起一根咬在嘴里。“嚯,嚯,真香。”老头笑出两排牙,“香,就对了。”一脸毫不谦虚的自豪。
老头姓陆,排行老大,人称“大陆”。他家的春卷,主要用山芋粉加上肉丝、青蒜叶作馅,深得食客喜爱。“大陆春卷”名头很响,很多人慕名而来。
许多年过去了,我再从中街走过,阳光里的小街石板依然光亮,天空依然瘦长,只是墙上多了一些铭牌,“学士巷”“恒顺香醋发源地”,静静地向过往的人们叙说着曾经的故事,朱金章、吴厂长、大陆等都已走出了中街,走进了小镇的历史,中街的味道在变与不变中安静地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