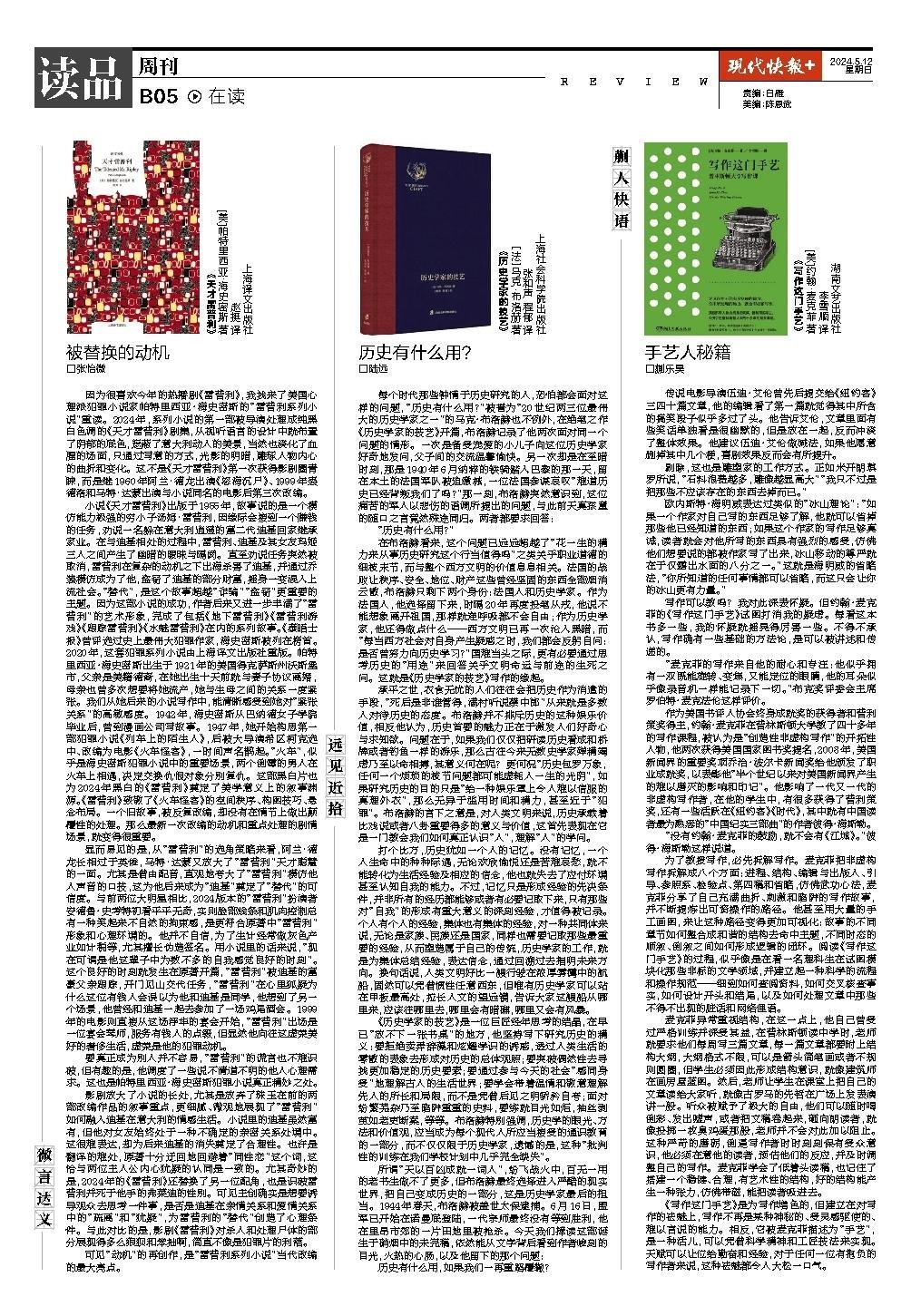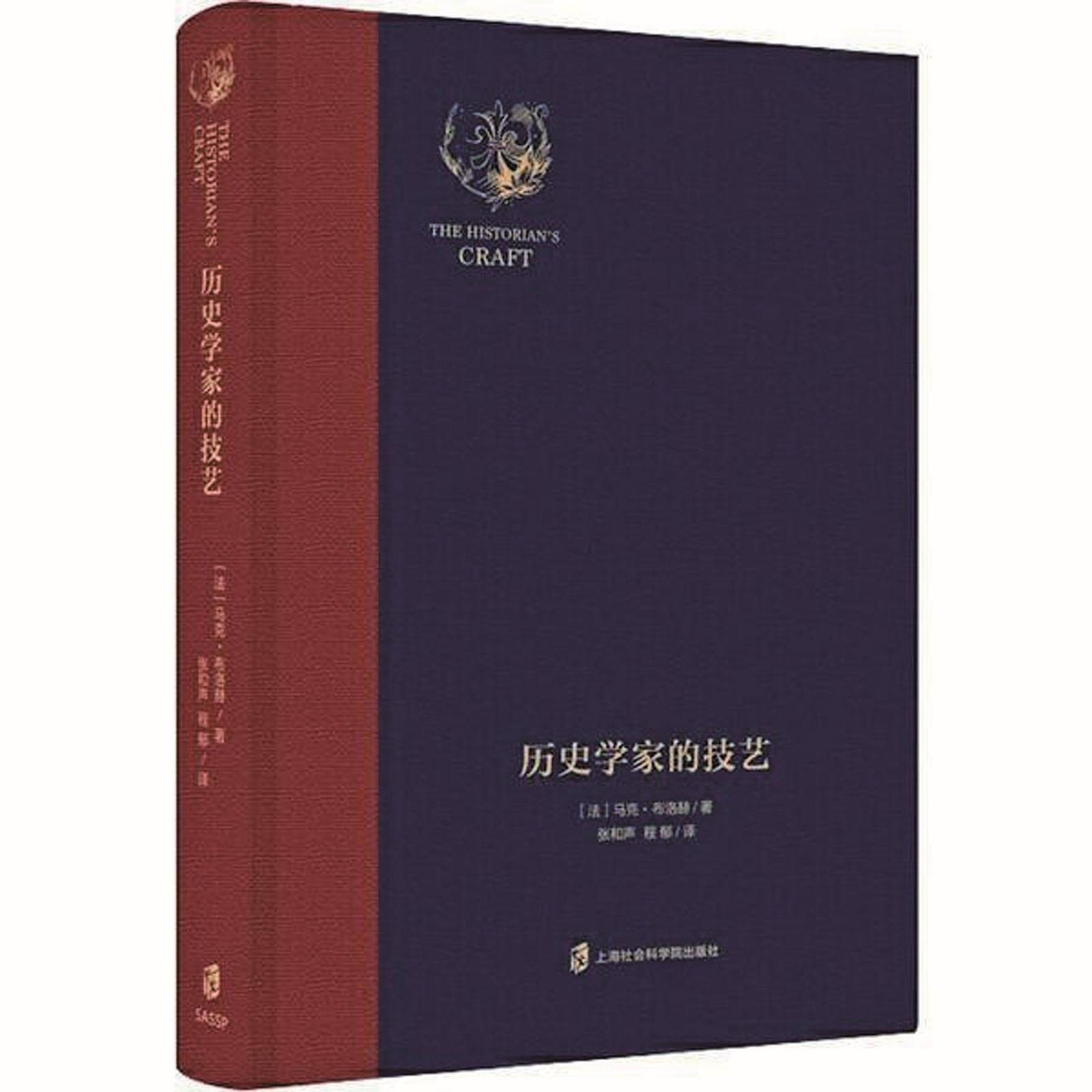□陆远
每个时代那些钟情于历史研究的人,恐怕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历史有什么用?”被誉为“20世纪两三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的马克·布洛赫也不例外,在绝笔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开篇,布洛赫记录了他两次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情形。一次是备受宠爱的小儿子向这位历史学家好奇地发问,父子间的交流温馨愉快。另一次却是在至暗时刻,那是1940年6月纳粹的铁骑踏入巴黎的那一天,留在本土的法国军队被迫缴械,一位法国参谋哀叹“难道历史已经背叛我们了吗?”那一刻,布洛赫突然意识到,这位痛苦的军人以悲伤的语调所提出的问题,与此前天真孩童的随口之言竟然殊途同归。两者都要求回答:
“历史有什么用?”
在布洛赫看来,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历史研究这个行当值得吗”之类关乎职业道德的细枝末节,而与整个西方文明的价值息息相关。法国的战败让秩序、安全、地位、财产这些曾经坚固的东西全部烟消云散,布洛赫只剩下两个身份:法国人和历史学家。作为法国人,他选择留下来,时隔20年再度投笔从戎,他说不能想象离开祖国,那样就连呼吸都不会自由;作为历史学家,他还得做点什么——西方文明已再一次沦入黑暗,而“每当西方社会对自身产生疑惑之时,我们都会反躬自问:是否曾努力向历史学习?”国难当头之际,更有必要通过思考历史的“用途”来回答关乎文明命运与前途的生死之问。这就是《历史学家的技艺》写作的缘起。
承平之世,衣食无忧的人们往往会把历史作为消遣的手段,“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从来就是多数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布洛赫并不排斥历史的这种娱乐价值,相反他认为,历史首要的魅力正在于激发人们好奇心与求知欲。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仅仅把研读历史看成和桥牌或者钓鱼一样的游乐,那么古往今来无数史学家殚精竭虑乃至以命相搏,其意义何在呢?更何况“历史包罗万象,任何一个烦琐的枝节问题都可能虚耗人一生的光阴”,如果研究历史的目的只是“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无异于滥用时间和精力,甚至近于“犯罪”。布洛赫的言下之意是,对人类文明来说,历史承载着比戏说或者八卦重要得多的意义与价值,这首先表现在它是一门教会我们如何真正认识“人”,理解“人”的学问。
打个比方,历史犹如一个人的记忆。没有记忆,一个人生命中的种种际遇,无论欢欣愉悦还是苦难哀愁,就不能转化为生活经验及相应的信念,他也就失去了应付环境甚至认知自我的能力。不过,记忆只是形成经验的先决条件,并非所有的经历都能够或者有必要记取下来,只有那些对“自我”的形成有重大意义的深刻经验,才值得被记录。个人有个人的经验,集体也有集体的经验,对一种共同体来说,无论是家族、民族还是国家,同样也需要记取那些最重要的经验,从而塑造属于自己的传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为集体总结经验,表达信念,通过回溯过去指明未来方向。换句话说,人类文明好比一艘行驶在浓厚雾霭中的航船,固然可以凭借惯性任意西东,但唯有历史学家可以站在甲板最高处,拉长人文的望远镜,告诉大家这艘船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哪里会有暗礁,哪里又会有风暴。
《历史学家的技艺》是一位巨匠经年思考的结晶,在早已“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地方,他坚持写下研究历史的精义:要拒绝卖弄辞藻和炫耀学识的诱惑,透过人类生活的零散的表象去形成对历史的总体观照;要突破偶然性去寻找更加稳定的历史要素;要通过参与今天的社会“感同身受”地理解古人的生活世界;要学会带着温情和敬意理解先人的所长和局限,而不是凭借后见之明骄矜自夸;面对纷繁芜杂乃至陷阱重重的史料,要练就目光如炬,抽丝剥茧如老吏断案,等等。布洛赫特别强调,历史学的眼光、方法和价值观,应当成为每个现代人所应当接受的通识教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限于历史学家,遗憾的是,这种“批判性的训练在我们学校计划中几乎完全缺失”。
所谓“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纷飞战火中,百无一用的老书生做不了更多,但布洛赫最终选择进入严酷的现实世界,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学家最后的担当。1944年春天,布洛赫被盖世太保逮捕。6月16日,盟军已开始在诺曼底登陆,一代宗师最终没有等到胜利,他在里昂市郊的一片田地里被枪杀。今天我们捧读这部诞生于硝烟中的未完稿,依然能从文字背后看到作者峻刻的目光,火热的心肠,以及他留下的那个问题:
历史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一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