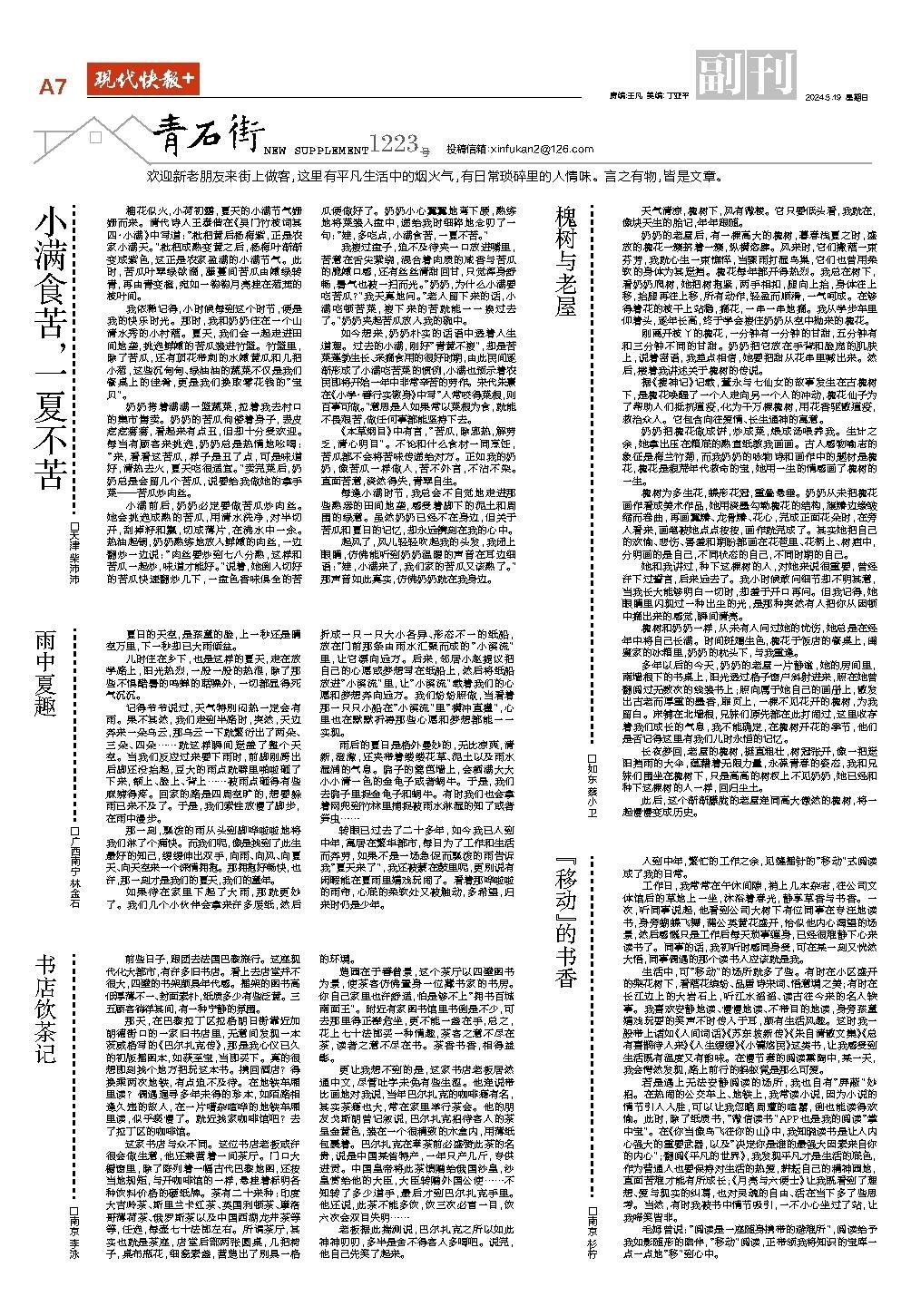□天津 柴沛沛
榴花似火,小荷初露,夏天的小满节气姗姗而来。清代诗人王泰偕在《吴门竹枝词其四·小满》中写道:“枇杷黄后杨梅紫,正是农家小满天。”枇杷成熟变黄之后,杨梅叶渐渐变成紫色,这正是农家盈满的小满节气。此时,苦瓜叶翠绿欲滴,藤蔓间苦瓜由嫩绿转青,再由青变橙,宛如一钩钩月亮挂在葱茏的枝叶间。
我依稀记得,小时候每到这个时节,便是我的快乐时光。那时,我和奶奶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落。夏天,我们会一起走进田间地垄,挑选鲜嫩的苦瓜装进竹篮。竹篮里,除了苦瓜,还有顶花带刺的水嫩黄瓜和几把小葱,这些沉甸甸、绿油油的蔬菜不仅是我们餐桌上的佳肴,更是我们换取零花钱的“宝贝”。
奶奶挎着满满一篮蔬菜,拉着我去村口的集市售卖。奶奶的苦瓜佝偻着身子,表皮疙疙瘩瘩,看起来有点丑,但却十分受欢迎。每当有顾客来挑选,奶奶总是热情地吆喝:“来,看看这苦瓜,样子是丑了点,可是味道好,清热去火,夏天吃很适宜。”卖完菜后,奶奶总是会留几个苦瓜,说要给我做她的拿手菜——苦瓜炒肉丝。
小满前后,奶奶必定要做苦瓜炒肉丝。她会挑选成熟的苦瓜,用清水洗净,对半切开,刮掉籽和瓤,切成薄片,在沸水中一汆。热油起锅,奶奶熟练地放入鲜嫩的肉丝,一边翻炒一边说:“肉丝要炒到七八分熟,这样和苦瓜一起炒,味道才能好。”说着,她倒入切好的苦瓜快速翻炒几下,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苦瓜便做好了。奶奶小心翼翼地弯下腰,熟练地将菜装入盘中,递给我时细碎地念叨了一句:“娃,多吃点,小满食苦,一夏不苦。”
我接过盘子,迫不及待夹一口放进嘴里,苦意在舌尖萦绕,混合着肉质的咸香与苦瓜的脆嫩口感,还有丝丝清甜回甘,只觉浑身舒畅,暑气也被一扫而光。“奶奶,为什么小满要吃苦瓜?”我天真地问。“老人留下来的话,小满吃顿苦菜,接下来的苦就能一一挨过去了。”奶奶夹起苦瓜放入我的碗中。
如今想来,奶奶朴实的话语中透着人生道理。过去的小满,刚好“青黄不接”,却是苦菜蓬勃生长、采摘食用的很好时期,由此民间逐渐形成了小满吃苦菜的惯例,小满也预示着农民即将开始一年中非常辛苦的劳作。宋代朱熹在《小学·善行实敬身》中写“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意思是人如果常以菜根为食,就能不畏艰苦,做任何事都能坚持下去。
《本草纲目》中有言,“苦瓜,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不论和什么食材一同烹饪,苦瓜都不会将苦味传递给对方。正如我的奶奶,像苦瓜一样做人,苦不外言,不沾不染。直面苦意,淡然得失,青翠自生。
每逢小满时节,我总会不自觉地走进那些熟悉的田间地垄,感受着脚下的泥土和周围的绿意。虽然奶奶已经不在身边,但关于苦瓜和夏日的记忆,却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起风了,风儿轻轻吹起我的头发,我闭上眼睛,仿佛能听到奶奶温暖的声音在耳边细语:“娃,小满来了,我们家的苦瓜又该熟了。”那声音如此真实,仿佛奶奶就在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