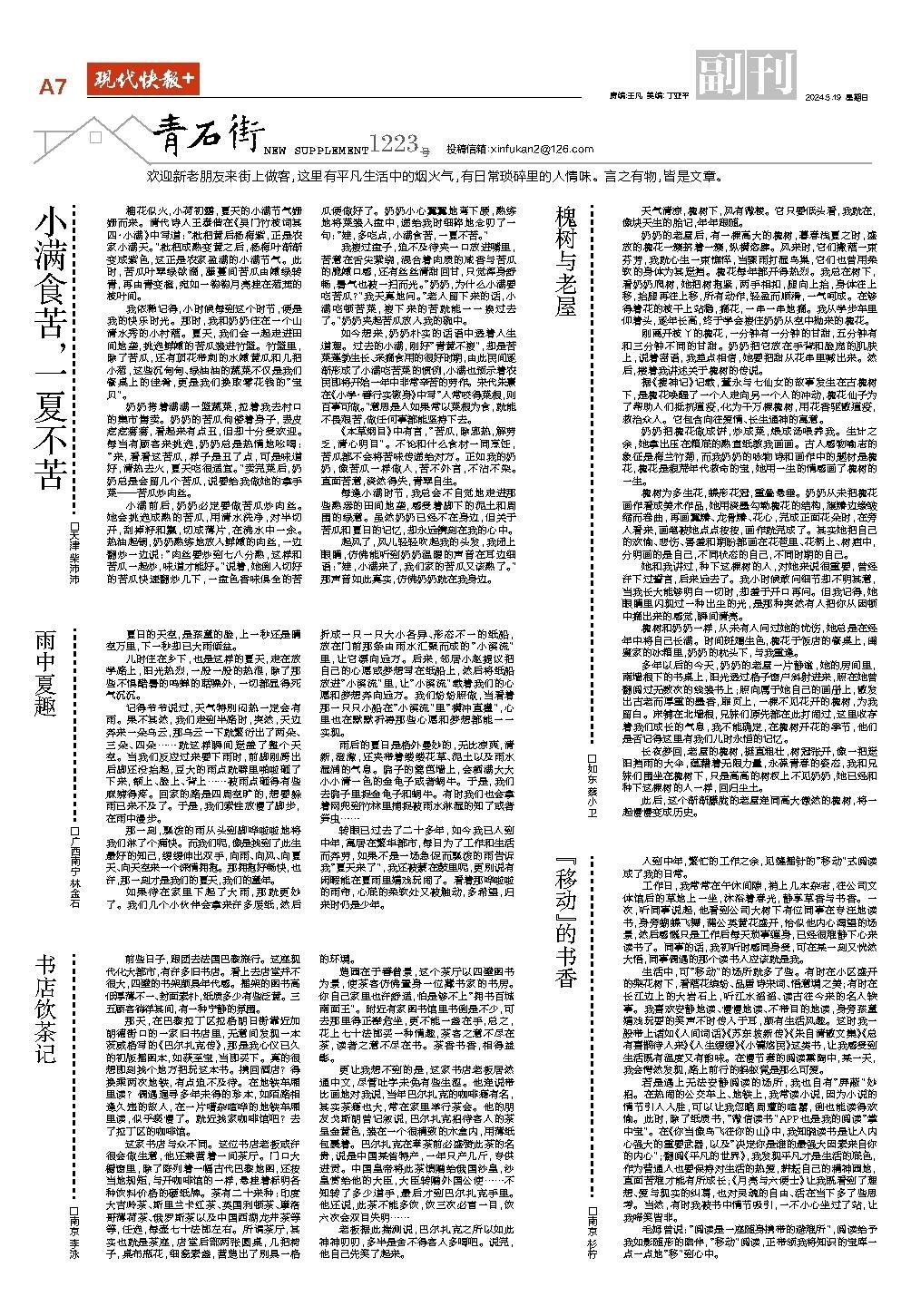□如东 蔡小卫
天气清凉,槐树下,风有微棱。它只要低头看,我就在,像块天生的胎记,年年跟随。
奶奶的老屋后,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暮春浅夏之时,盛放的槐花一簇挤着一簇,纵横恣肆。风来时,它们撒落一束芬芳,我就心生一束憔悴,当骤雨打湿鸟巢,它们也曾用柔软的身体为其遮挡。槐花每年都开得热烈。我总在树下,看奶奶爬树,她把树抱紧,两手相扣,腿向上抬,身体往上移,抬腿再往上移,所有动作,轻盈而顺滑,一气呵成。在够得着花的枝干上站稳,摘花,一串一串地摘。我从学步车里仰着头,逐年长高,终于学会接住奶奶从空中抛来的槐花。
刚离开枝丫的槐花,一分钟有一分钟的甘甜,五分钟有和三分钟不同的甘甜。奶奶把它放在手背和脸庞的肌肤上,说着密语,我差点相信,她要把甜从花串里喊出来。然后,搂着我讲述关于槐树的传说。
据《搜神记》记载,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发生在古槐树下,是槐花唤醒了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的冲动,槐花仙子为了帮助人们抵抗瘟疫,化为千万棵槐树,用花香驱散瘟疫,救治众人。它包含向往爱情、长生通神的寓意。
奶奶把槐花做成饼,炒成菜,煨成汤喂养我。生计之余,她拿出压在箱底的熟宣纸教我画画。古人感物喻志的象征是梅兰竹菊,而我奶奶的咏物诗和画作中的题材是槐花,槐花是粮荒年代救命的宝,她用一生的情感画了槐树的一生。
槐树为多生花,蝶形花冠,重叠悬垂。奶奶从未把槐花画作看成美术作品,她用淡墨勾勒槐花的结构,旗瓣边缘皱缩而卷曲,再画翼瓣、龙骨瓣、花心,完成正面花朵时,在旁人看来,画笔被她点点按按,画作就完成了。其实她把自己的欢愉、悲伤、害羞和期盼都画在花苞里、花柄上、树疤中,分明画的是自己,不同状态的自己,不同时期的自己。
她和我讲过,种下这棵树的人,对她来说很重要,曾经许下过誓言,后来远去了。我小时候敢问细节却不明其意,当我长大能够明白一切时,却羞于开口再问。但我记得,她眼睛里闪现过一种出尘的光,是那种突然有人把你从困顿中摘出来的感觉,瞬间清亮。
槐树和奶奶一样,从未有人问过她的忧伤,她总是在经年中将自己长满。时间斑斓生色,槐花于饭店的餐桌上,闺蜜家的冰箱里,奶奶的枕头下,与我重逢。
多年以后的今天,奶奶的老屋一片静谧,她的房间里,南墙根下的书桌上,阳光透过格子窗户斜射进来,照在她曾翻阅过无数次的线装书上;照向属于她自己的画册上,散发出古老而厚重的墨香,扉页上,一棵不见花开的槐树,为我留白。床铺在北墙根,兄妹们原先都在此打闹过,这里收存着我们成长的气息,我不能确定,在槐树开花的季节,他们是否记得这里有我们儿时永恒的记忆。
长夜梦回,老屋的槐树,挺直粗壮,树冠张开,像一把遮阳挡雨的大伞,蕴藉着无限力量,永葆青春的姿态,我和兄妹们围坐在槐树下,只是高高的树杈上不见奶奶,她已经和种下这棵树的人一样,回归尘土。
此后,这个渐渐朦胧的老屋连同高大傲然的槐树,将一起慢慢变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