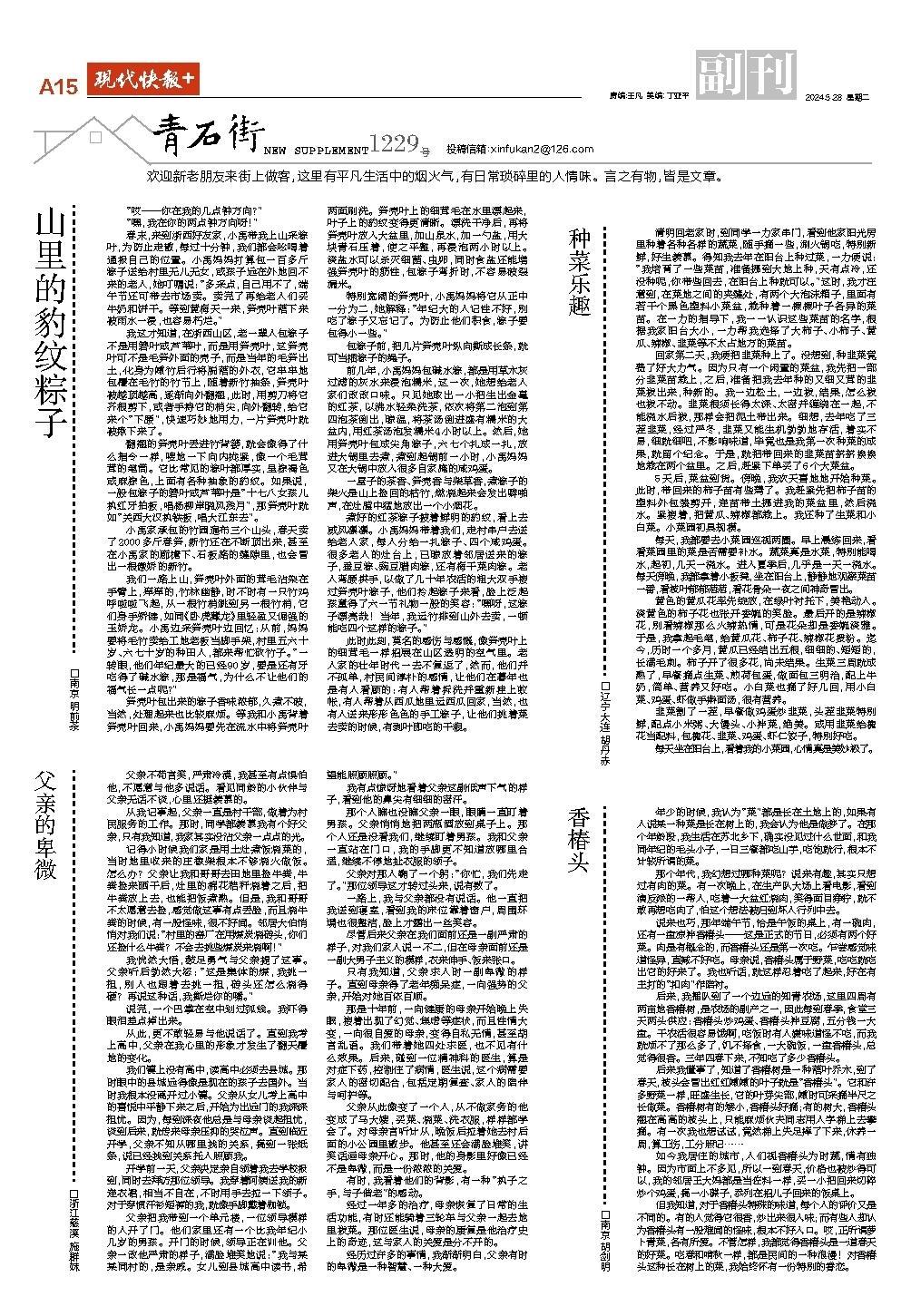□浙江慈溪 施群妹
父亲不苟言笑,严肃冷漠,我甚至有点惧怕他,不愿意与他多说话。看见同龄的小伙伴与父亲无话不谈,心里还挺羡慕的。
从我记事起,父亲一直是村干部,做着为村民服务的工作。那时,同学都羡慕我有个好父亲,只有我知道,我家其实没沾父亲一点点的光。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是用土灶煮饭烧菜的,当时地里收来的庄稼柴根本不够烧火做饭。怎么办?父亲让我和哥哥去田地里捡牛粪,牛粪捡来晒干后,灶里的棉花秸秆烧着之后,把牛粪放上去,也能把饭煮熟。但是,我和哥哥不太愿意去捡,感觉做这事有点丢脸,而且烧牛粪的时候,有一股怪味,很不好闻。邻居大伯悄悄对我们说:“村里的窑厂在用煤炭烧砖头,你们还捡什么牛粪?不会去挑些煤炭来烧啊!”
我恍然大悟,鼓足勇气与父亲提了这事。父亲听后勃然大怒:“这是集体的煤,我挑一担,别人也跟着去挑一担,砖头还怎么烧得硬?再说这种话,我撕烂你的嘴。”
说完,一个巴掌在空中划过弧线。我吓得眼泪差点掉出来。
从此,更不敢轻易与他说话了。直到我考上高中,父亲在我心里的形象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镇上没有高中,读高中必须去县城。那时眼中的县城远得像是现在的孩子去国外。当时我根本没离开过小镇。父亲从女儿考上高中的喜悦中平静下来之后,开始为出远门的我深深担忧。因为,每到深夜他总是与母亲谈起担忧,谈到后来,就传来母亲压抑的哭泣声。直到临近开学,父亲不知从哪里找的关系,搞到一张纸条,说已经找到关系托人照顾我。
开学前一天,父亲决定亲自领着我去学校报到,同时去拜访那位领导。我穿着阿姨送我的新连衣裙,相当不自在,不时用手去拉一下领子。对于穿惯汗衫短裤的我,就像手脚戴着枷锁。
父亲把我带到一个单元楼,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开了门。他们家里还有一个比我年纪小几岁的男孩。开门的时候,领导正在训他。父亲一改他严肃的样子,满脸堆笑地说:“我与某某同村的,是亲戚。女儿到县城高中读书,希望能照顾照顾。”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父亲这副低声下气的样子,看到他的鼻尖有细细的密汗。
那个人瞧也没瞧父亲一眼,眼睛一直盯着男孩。父亲悄悄地把两瓶酒放到桌子上。那个人还是没看我们,继续盯着男孩。我和父亲一直站在门口,我的手脚更不知道放哪里合适,继续不停地扯衣服的领子。
父亲对那人鞠了一个躬:“你忙,我们先走了。”那位领导这才转过头来,说有数了。
一路上,我与父亲都没有说话。他一直把我送到寝室,看到我的床位靠着窗户,周围环境也很整洁,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
尽管后来父亲在我们面前还是一副严肃的样子,对我们家人说一不二,但在母亲面前还是一副大男子主义的模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只有我知道,父亲求人时一副卑微的样子。直到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一向强势的父亲,开始对她百依百顺。
那是十年前,一向健康的母亲开始晚上失眠,接着出现了幻觉、焦虑等症状,而且性情大变,一向很自爱的母亲,变得自私无情,甚至胡言乱语。我们带着她四处求医,也不见有什么效果。后来,碰到一位精神科的医生,算是对症下药,控制住了病情,医生说,这个病需要家人的密切配合,包括定期复查、家人的陪伴与呵护等。
父亲从此像变了一个人,从不做家务的他变成了马大嫂,买菜、烧菜、洗衣服,样样都学会了。对母亲言听计从,晚饭后拉着她去村后面的小公园里散步。他甚至还会满脸堆笑,讲笑话逗母亲开心。那时,他的身影里好像已经不是卑微,而是一份浓浓的关爱。
有时,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有一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动。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母亲恢复了日常的生活功能,有时还能骑着三轮车与父亲一起去地里拔菜。那位医生说,母亲的康复是他治疗史上的奇迹,这与家人的关爱是分不开的。
经历过许多的事情,我渐渐明白,父亲有时的卑微是一种智慧、一种大爱。